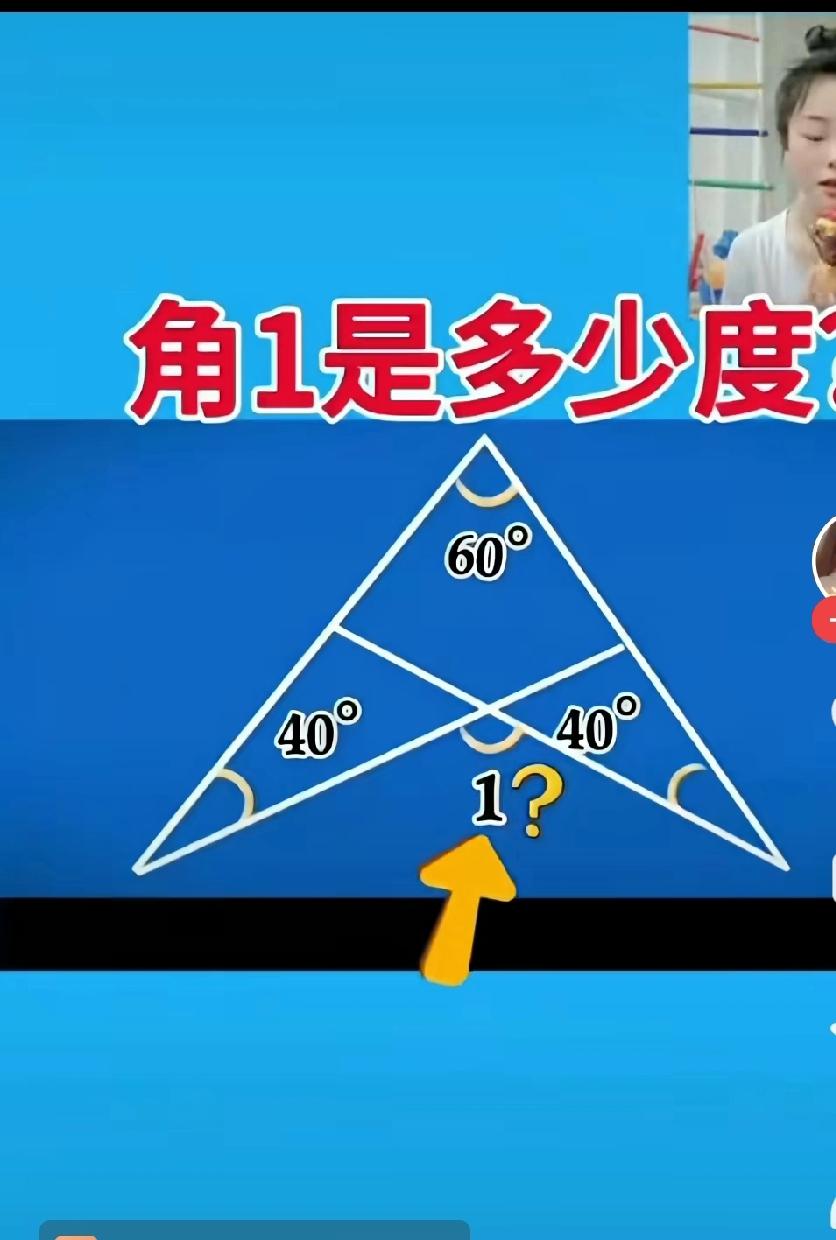老李在烟台做垃圾清运工作,今年七十二岁,老李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后两次高考都因为数学成绩不够没能考上,后来他开始扫街,这份工作一干就是四十年,最近他把一堆手稿交给同事张女士,说怕这些纸被当成废纸扔掉,希望有人帮忙留着,那些纸已经泛黄,背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公式,厚度大约八到九厘米,全部是写在捡来的废纸上头。
他住在一个九平方米的地下室,那里没有厕所和暖气,与邻居共用一扇铁门,每月租金一百五十块钱,他每天都坐在小马扎上算题,鼻血流到草稿纸上也不停下,家里人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劝他别再折腾,他便在墙上贴了写着“放下”的纸条,可实际上根本放不下这件事,他说自己这样做不是为了出名,只是觉得脑子空了不行,必须找点事情来填满。

一条网上视频热传开来,收获一百五十多万点赞和两万多条评论。博主“汤匙”毕业于北大数学系,他看过老李的论文开头,认为题目难度达到竞赛水平。“汤匙”还说,无论这份成果是否属于原创,它都代表着老李自己的数学天地。这话听着让人心头一暖,又有点不是滋味——一个人的思维世界,原来要依靠陌生人的转发才能被人看到。

有人说张女士是天才,也有人担心大家太激动,会把张女士当成悲情符号,张女士拒绝了所有私人捐款,说要走透明渠道,不想让这事变成一场围观消费,张女士觉得尊重一个人,不是给这个人钱,而是认真看这个人在写什么,老李自己也说,不要资助,只想有人看看老李的推导过程。
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里,都能看到这样一群人,退休工人、小摊贩、个体户,他们收集旧书、抄写公式、投稿信件,自己搭建出一套民间学术交流的圈子,老李的手稿中记录着一百多条定理,或许其中有些是重复的,也有些存在错误,但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很可能拼凑出一条独特的思考路线,即便得不到学院派的认可,它依然是一段真实存在过的思想印记。
他住的地方太小,连张大桌子都放不下,网友们讨论要不要帮他换个住处,张辰阳一开始就拒绝这个提议,因为张辰阳真正在意的不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是希望别人能认真看待他的演算过程,虽然张女士的团队答应给他弄一张可以写字的桌子,但那个地下室实在挤不进去。

目前的所有讨论都建立在部分公开内容的基础上,完整手稿尚未全部公布,"汤匙"只阅读了前半部分内容,这些定理是否具备原创性、逻辑是否存在漏洞、能否正式发表,目前还无法确定,学术圈既没有接手这个课题也没有明确否定,大家只是在等待更多材料公开,这个过程就像拆盲盒,人们不知道最终会收获惊喜还是遗憾,但正是拆解的过程本身,已经让许多人停下脚步开始关注。
我倒觉得这种状态很真实,不是每个努力的人都得被当成英雄,也不是每个孤独思考的人都要被体制接受,老李不需要别人鼓掌,他只想找个安静地方好好演算,就算还是那个地下室,只要没人打扰他,他就满足了,我们这些围观的人,与其急着提建议,不如先试着理解他写下的每一个符号。
他没有打算改变这个世界,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在某个角落坚持着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或许没人理解,但它确实存在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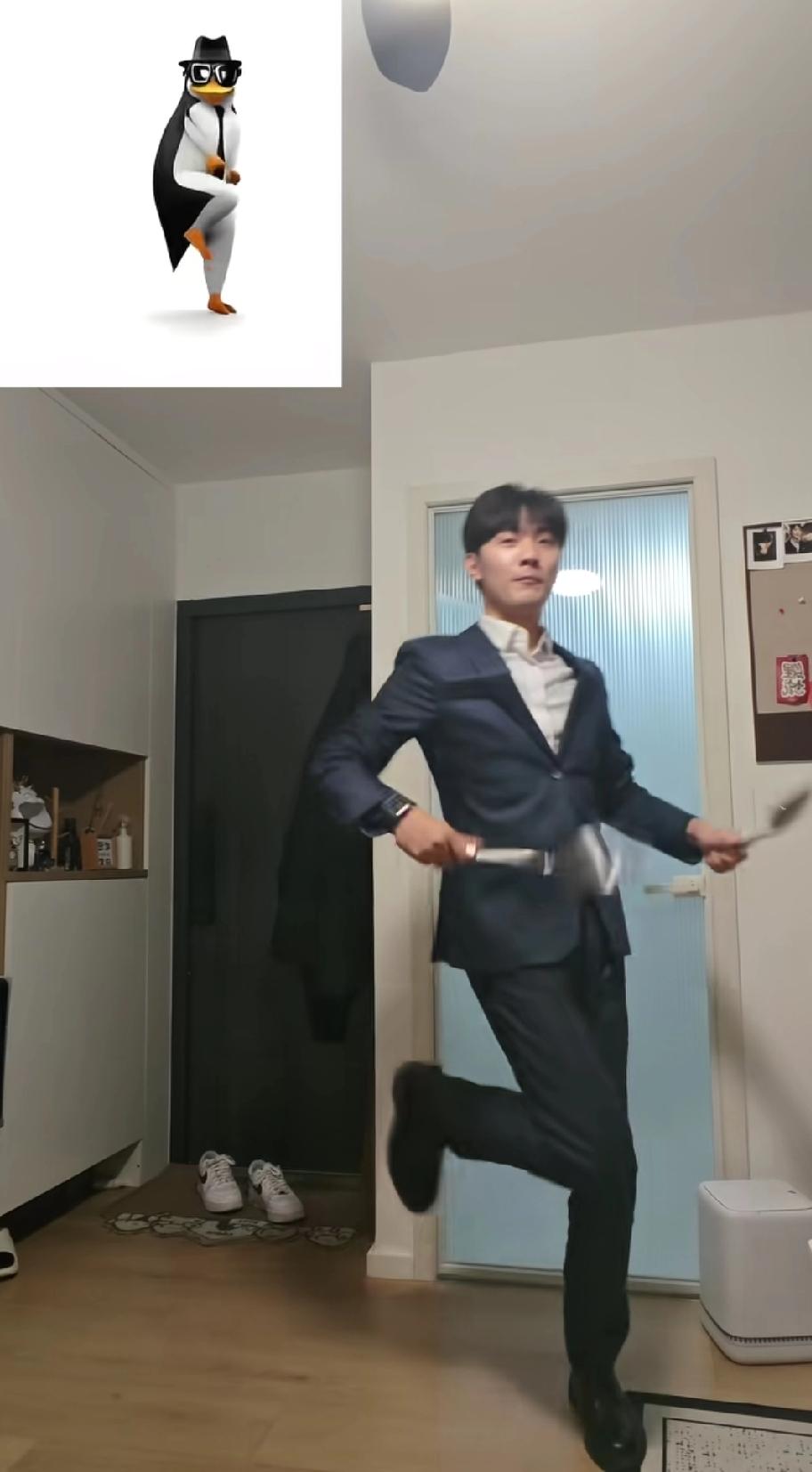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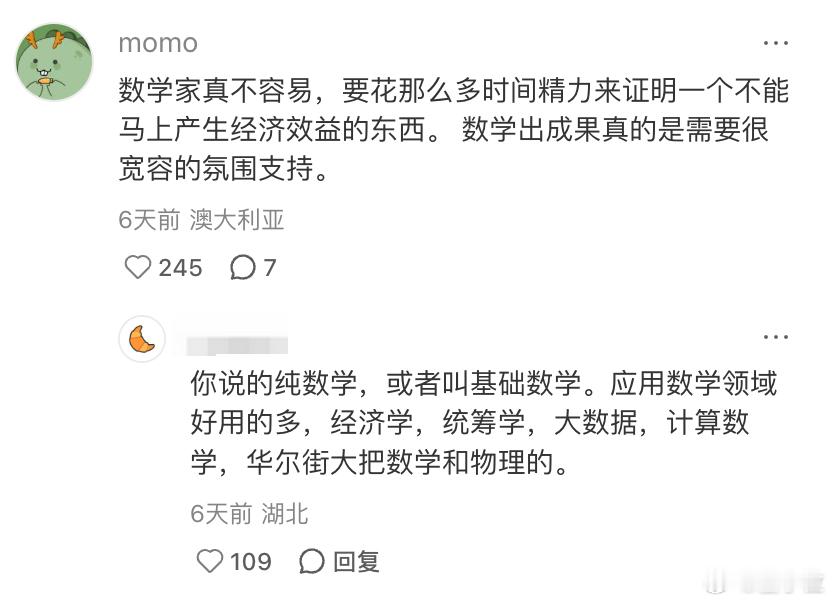
![[思考][思考][思考]](http://image.uczzd.cn/865200884053969355.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