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不到半年,妻子公然带男闺蜜回家挑衅我。
以前他们说句话我都要吃醋半天,现在任由他们在卧室里翻云覆雨闹出多大动静,我权当不知道。
她反而先急了,“谢京泽,你面对这些真的就一点也不嫉妒吗?”
我只是淡笑着说:“嫉妒什么?我看不见。”
半年前,我就为她瞎了这双眼睛,可妻子却一直认为这是我和她男闺蜜争风吃醋的手段。
1
姜幼雪回国那天,我没去接她。
因为盲人出行不太方便。
等到夜里,本来早该到家的姜幼雪终于姗姗来迟。
看着屋子里布置的浪漫鲜花,还有精心准备的礼物盒子。
一道男声噗嗤笑了起来:“看不出来京泽哥还挺有浪漫细胞,既然如此,那我就不打扰你们过二人世界。”
“雪儿,我只能陪你到这,先走了。”
熟悉的嗓音让我听出来人是黎夜。
姜幼雪从小到大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竹马兼男闺蜜。
他一口一个“京泽哥”的称呼我,态度却并无半分尊敬。
姜幼雪急忙拉住他。
“过什么二人世界呀,阿夜你又不是外人,走什么走,留下一起呗。”
黎夜故意说:“这不合适吧。”
姜幼雪温声道:“我说合适就合适,这个家我说了算!对吧老公?”
像是终于想起了我的存在。
姜幼雪转头朝我看来,神情一怔。
“老公你这是什么造型?”
我眼睛蒙着黑布,手握着盲杖,站在这里安安静静听完了他们的对话。
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可笑。
口口声声喊我老公的妻子,心中却似乎没有多少我的分量。
“幼雪,我和你发消息解释过了。”
姜幼雪这才掏出手机,似乎往下划了好一会儿才找到我的聊天框。
气氛一时间有些沉默凝固。
“谢京泽……你说你失明了?”
姜幼雪错愕地抬起头。
语气里充满了不可置信,“明明我出国之前你眼睛还是好好的,无缘无故地怎么会突然看不见……”
黎夜及时插话进来。
“京泽哥,以前你骗我们雪儿自己生病了想让她回来照顾你,发现这招不管用了,又开始换套路了是吧。”
姜幼雪一下子被他说动摇了。
“好啊谢京泽,你现在撒谎都不打草稿吗?”
“这么幼稚的把戏亏你想得出来,我都有点怀疑你是不是个成年男人了,光长年龄不长脑子。”
“阿夜明明比你小几岁,却比你成熟懂事多了,你真应该向他多学习学习……”
听出了姜幼雪话里浓浓的讥讽。
我心口弥漫出一股涩意,握着盲杖的手不自觉收紧几分。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从来没有骗过姜幼雪。
但只要黎夜一开口,无论是错是对,姜幼雪只会无条件地偏信于他。
我扯了扯唇角,“我有什么骗你的必要吗?”
“怎么没有?”
姜幼雪言之凿凿,“为了和阿夜争宠,为了博取我的同情,还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出来的!”
“我倒是挺佩服你的,戏这么多,怎么不干脆改行去当演员?”
说着,姜幼雪一把扯掉了我眼睛上蒙着的黑布,以为这样就能拆穿我的诡计。
可是当她看清我此刻的样子后,整个人都愣住了。
2
我的瞳孔黯淡无光,死气沉沉的一片。
我失明这件事一直瞒着姜幼雪,就是怕她在国外替我担心,打算等她回来以后再慢慢和她解释缘由。
“谢京泽,你……”
姜幼雪愣神过后,仍是有所怀疑地凑近了些观察我的眼睛。
我一眨不眨,眼神完全是失焦的状态。
“也没个伤口什么的,好端端的怎么会失明。”
姜幼雪皱起眉头,有种被我捉弄般的气恼。
她伸手用力推了我一把,“差不多够了谢京泽,我都已经回来了,你还要怎么样?”
这一下太过突然。
我毫无防备,身体踉跄了一下往后栽倒。

整个世界都是晦暗无光的,手里什么东西也抓不住的感觉让我慌张又绝望。
等到腰部一阵尖锐的刺痛感传来时,我知道我应该是磕到桌角上了。
手捂住伤口,好像有温热黏腻的液体流淌出来。
我听见两道讽刺笑声。
“你还演上瘾了是吧,奥斯卡真是欠你一座小金人。”
“这么喜欢装瞎,有本事就装一辈子!”
“雪儿你也别太跟京泽哥计较了,他肯定是因为太爱你了,才想出这个蠢办法试图引起你的注意。”
姜幼雪拉过黎夜的胳膊,“你就别替他说话了,走吧阿夜,我们回房间睡觉!”
“不管这个戏精了,他爱演就让他继续演,我懒得奉陪。”
她刻意把“睡觉”两字咬的很重。
当着我的面,我的妻子直言要别的男人陪她睡觉。
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腰部的伤口血越流越多,透过衣料渗透出来。
我不知道身上这件衣服是什么颜色,血迹在上面会不会很显眼。
伤口的痛不及心口的万分之一。
姜幼雪说是要走,我却迟迟没有听见他们转身离开的动静。
我期待她能发现我的异常。
但是没有。
脚步声最终还是响起了,离我越来越远。
如果换做以前,我肯定会忍不住沉声喊住他们,质问姜幼雪到底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类似的情景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可姜幼雪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
哪怕失明了,我的脑海里依然记得她理直气壮的样子。
“谢京泽你有这个功夫怀疑我,不如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的思想有问题!”
“你不仅侮辱了我和阿夜纯洁的友谊,还侮辱了我们的人品!”
“我们两家关系好,几乎是从小睡一张床长大的,早就习以为常了,这又没什么,就你大惊小怪的。”
……
所以现在我不过问了。
我摸索着找到医药箱的位置,给自己简单处理了伤势。
包扎的样子大概很难看吧,但是有用就好。
卧室里的暧昧声响我就当听不见。
偏偏姜幼雪还是不满意。
她来客房找到了我,冷冷地笑了一下。
“谢京泽你现在还挺能忍。”
我听见布料摩擦的声音,她好像把衣领解开拉低了一些,我知道她这个举动应该是在向我展露她脖颈上的痕迹。
结合她刚刚和黎夜在卧室里闹出的动静,我怎么会猜不到。
“这样呢?你还是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姜幼雪死死观察着我的反应,期待着我会像曾经那样暴跳如雷,为她吃醋到发狂。
是我对她的溺爱和纵容,让她连出轨都能如此理直气壮耀武扬威。
可我现在什么也看不见。
我目光空洞困惑,“怎么了?我应该说什么吗?”
姜幼雪似乎气狠了,掐着我的肩膀强迫我抬头和她对视。
“你还装!”
我叹了口气,“幼雪,为什么你就是不肯信我?”
姜幼雪沉默了片刻,“如果你不是装的,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瞎?”
3
“出了点意外。”我没细说,毕竟这事和她也有关系,我不希望她因此自责愧疚。
姜幼雪追问:“什么意外?在哪里?什么时间?怎么发生的?”
见我低头不语,姜幼雪松开我的肩膀,慢慢后退几步。
“编不出来了是吧。”
她嗓音冷淡,仿佛对我失望至极。
“阿夜有抑郁症,你就跟我装残疾人,你就非要什么都和人家比吗?居然还学会了无耻的卖惨。”
我只觉得喉头像堵了团棉花,没等我继续为自己辩解。
黎夜也过来了,伸手在我面前挥了挥,我毫无反应。
他嗤笑一声,“装的还真像,要不然我们试试吧,看他能忍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谢京泽,跟我出来!”
姜幼雪把我带到了楼下。
夜里风大,我只穿着单薄的居家服,找不到任何方向孤零零站在街头。
我抱着双臂,下意识瑟缩了一下。
然后就听见了姜幼雪从鼻腔里发出的一声不屑的轻哼。
“你要是真的瞎了,就证明给我看。”
“怎么证明?”我问。
“沿着这条盲道走到头。”
就这么简单,我总觉得不太对劲,但我还是点头答应了,“好。”
我没机会拿盲杖,只能凭借盲道的触感一步步小心翼翼往前。
但还是撞到了好几次路边随意停放的电动车辆。
腰部伤口传来被牵扯的痛感。
“京泽哥你怎么停下来了?继续走啊,你不是想证明给雪儿看吗?”
听到黎夜的催促,我沉了口呼吸,重新抬脚向前的那一刻。
我踩空了。
失重感瞬间袭来,整个身体都往下坠落。
砰的一声!
我重重地摔进了一个坑里,能清晰听见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四肢百骸都是密密麻麻的疼,血流不止。
好痛,痛到神经都要麻木了。

世界一片漆黑,我徒劳地睁着眼望向天空。
有种流泪的冲动。
为什么?为什么姜幼雪要联合黎夜这么设计我?
她就这么厌恶我恨我吗?
耳朵似乎也开始耳鸣了,失去意识前,我隐隐约约听见姜幼雪焦急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
“谢京泽——你没事吧?”
幻听了吧,她怎么会担心我呢。
紧接着是黎夜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讽刺声。
“为了不露出马脚,京泽哥还真是拼啊,雪儿你难道这就信了他?”
“耐心等等吧,他自己会爬上来的。”
于是就这么等了几分钟。
姜幼雪有些忍不住了,走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彻底昏死过去。
4
再醒来,我闻到了医院特有的那股消毒水的气味。
我感觉手背上插着针管,似乎在输液。
阳光照进我的眼睛,有些热,让我有种被灼烧般的不适。
虽然我已经完全不能视物了,但对光源还是很敏感。
我下意识闭上眼,用手挡住眼皮。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当动作。
旁边突然传来一道摔碗声,吓我一跳。
“谢京泽,你这招苦肉计真是厉害啊,差一丁点就把我骗过去了。”
姜幼雪的嗓音凉凉传来。
“一个瞎子,为什么还会怕光?”
我安静地不说话,手臂也垂落下来,重新睁开空茫的眼睛循声看向她的方向。
我感觉姜幼雪站起了身。
“既然你这么喜欢当盲人,行,那我成全你。”
下一秒,冰凉锋利的刀片划过我的眼角。
血珠滴答往下掉,砸在医院的被子上,这回应该会特别醒目吧。
“……你居然不躲开?”
姜幼雪声线颤抖,有压抑的愤怒和后怕,“谢京泽,你是不是笃定了我不敢真的对你动手,才会这么有恃无恐?”
我抬手摸了摸眼角,血迹在我指腹晕开。
我淡笑着反问:“敢不敢的,你不都已经对我动手了么?”
“我那是……那是……”姜幼雪丢开手里的水果刀,带着几分咬牙切齿,“给你个教训而已!”
我又淡淡地“哦”一声。
姜幼雪扑到我面前,“装瞎这种幼稚的把戏你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
“你不就是嫉妒我陪阿夜出国治疗散心,吃他的醋吗?”
“我应该早都跟你解释过了,他有抑郁症,我不放心才陪着的,而且我都回来了,你现在跟我闹这个有意思吗?”
“是挺没意思的。”这是实话。
“姜幼雪,我们之间,真的没劲透了。”
5
还记得婚礼那日,黎夜一句心情不好想跳海。
姜幼雪就当着众人的面扯掉头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现场。
让我在大庭广众下难堪。
后来我在医院找到他们,姜幼雪正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细心地放在嘴边吹了吹,然后亲手喂给黎夜吃。
姿态亲昵暧昧,仿佛他们才是一对恩爱的情侣。
看着这一幕,我只觉得心底憋着一团火。
我大步过去拽住姜幼雪的胳膊,语气隐忍:
“你跟我回去!”
姜幼雪直接甩开了我的手。
“谢京泽,现在不是你闹脾气的时候,你没看见阿夜的状态很不对劲吗?”
“有什么事我们晚点再说,你不要在这里碍眼,阿夜不想看见你。”
病床上的男人生着一副好皮囊,苍白的面容,眼底却带着对我无尽的挑衅和炫耀。
我攥紧拳头,骨头咔咔作响。
一个女人,一个病人。
我心底的那团怒火无处发泄,只能恨恨地砸了一下墙。
“哐”地一声!
姜幼雪被吓一跳,端着的粥不小心洒出来一点。
“谢京泽你发什么神经,你赶紧给我滚!滚啊!”
我在姜幼雪的怒骂中离开病房。
我等在医院,隔了两个小时,姜幼雪才不紧不慢地走出来。
“你难道就没有什么要和我解释的?”
姜幼雪注意到我眼底猩红,强压着情绪的模样。

她可能也自知理亏,态度和缓了不少。
“好啦老公,反正我们都已经领过证了,婚礼不过是走个仪式,随时都能补办的。”
“但是阿夜当时的情况真的等不了,那可是活生生的一条人命啊,老公你不会那么冷血无情的对不对?”
“你一定能够理解我的吧。”
姜幼雪几句话一下子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
让我想反驳的话都说不出口来,沉沉呼出一口气。
到底是我爱了那么多年的女人,还是不愿意就这么和她撕破脸。
于是我忍了。
我和姜幼雪商量着重新举办婚礼的时间,日子已经订好了,新的请柬也发出去了。
可是姜幼雪再一次放了我的鸽子,让我彻底沦为圈子笑柄。
……
“谢京泽你这话说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之间没劲透了?”
“怎么,你要和我离婚吗?”
离婚这句话,到底还是先从姜幼雪的口中说出来了。
我的态度算是默认。
姜幼雪急了,“我和阿夜清清白白,昨晚的事他也不是故意的,是你自己明知有坑还非要往下跳,这能怪得了谁?”
“要不是阿夜把你捞了上来,你现在应该还躺在坑里,说起来,你还欠他一句谢谢!”
我已经无心再和她争辩,干脆顺着她的话。
随口敷衍道:“嗯,那你替我好好谢谢他。”
姜幼雪却仿佛吞了苍蝇般,不敢相信这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
她还想再说点什么。
这时候有护士进了病房,来给我换空了的吊瓶。
一片静默中,姜幼雪冷不丁开口:“您好,谢京泽的病例,能给我看一下吗?”
我的心脏倏地一紧。
护士迟疑着问:“您是他什么人?”
姜幼雪语气坚定,“我是他合法妻子。”
“不要给她!”
见我这样,姜幼雪冷嗤一声:“你急什么,该不会是怕我看了你的病例,然后装瞎的谎言再也编造不下去了?”
“装瞎?”护士夹在中间不明所以,“谢先生的眼睛在半年前就确诊失明了,您是他妻子,居然不知道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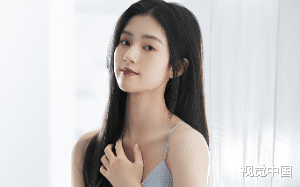







垃圾男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