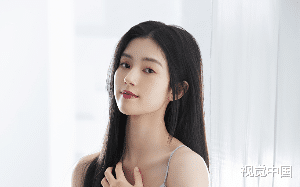我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爆火,媒体却爆出了我和男主演的绯闻。
“什么垃圾作者,敢蹭我们哥哥!经纪公司不管一管吗?”
报一丝,经纪公司是我开的,我是你们哥哥的经纪人。
男主演当天发微博艾特我,贴了我们高中时期的合照。
“年少相识,十年相伴,有如命运馈赠,我是否有这个荣幸和你共度余生?”
我淡定地转发。“乐意之至。”
我们一起从籍籍无名,走到鲜花着锦,走出困顿的年少时光,奔向旷野。
01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比人和狗之间的差距还大。
第一次见纪洲时,我脑子里闪过这句话。
这是开学第一天,我爸爸的电瓶车没电了,路上又堵,打不了车,我只好一路跑到学校。
路上我廉价的鞋开了胶,张着大口子,像在滑稽地龇牙咧嘴笑。
在校门口,我和慢悠悠下了豪车又慢悠悠往里走的纪洲撞了个正着,少爷一身富贵逼人的香水味儿扑了我一鼻子,呛得我惊天动地直咳嗽。
我被撞倒在地,一边大喘气,一边咳嗽,喉咙撕裂般生疼,发丝散乱,鞋子开着口,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纪洲衣冠楚楚,满身清贵气,居高临下地看我。
“哎不是?同学,可不是我撞的你哈!天地良心!你看,摄像头也看见了。”
哦,看我这幅尊容,他以为我是来碰瓷儿的了。
他要拉我起来,我甩甩手示意不用,拍拍手上和身上的灰:“抱歉,是我太急了不小心撞到你了,我是高一一班的言清,你哪伤了瘸了再来找我吧,要迟到了,我先走了。”
“你也是一班的?哎呀,迟到就迟到吧,你的鞋子嘴馋成这样,怎么跑?”
什么鬼东西。
我不理他,只尽力拔腿跑,纪洲追了上来,我气喘吁吁,他从容不迫,好奇又好玩儿似的看我。
“你,你干嘛?”
他忽然蹲下身,背起我就一个百米冲刺,速度很快,晃得我头晕,我像只破玩偶一样在他背上颠簸。
最后我们刹在了班级门口,上课铃声响起。
我上气不接下气,他没事人一样,把我放了下来。
班级里交头接耳,很多双发光的眼睛投来八卦的目光,老师也眼神微妙。
“迟到还带买一送一的?”
“报告老师,没有迟到,我看了表,我们在上课前五秒到的。”
老师扶着眼镜,看了眼名单。
“纪洲,言清,是吧,就差你俩了,尽快落座,你们来得晚,只有去守着垃圾桶了哈。”
“好嘞!”
纪洲生了一副好皮囊,一双桃花眼,看人时三分含笑。
老师在讲台上讲新学期的纪律,纪洲转过头笑盈盈看我。
“言清是吧?我是纪洲,哎我们的名字还怪般配的。幸会啦,同桌~”
他这跳脱的脑回路让我扶额无语。
般你大爷的配。
幸你大爷的会。
少爷这香水味儿熏得我脑仁疼,他这尊贵的“坐骑”颠得我早饭在胃里翻涌,那张皮惹来的女孩子们灼热的目光像针一般。
02
难道真像十几年前偶像剧里流行的那样,王子见惯了锦绣佳人,会觉得灰头土脸但骄傲坚韧的灰姑娘“有趣”、“新鲜”?
纪洲的新鲜劲还没过,他总念叨着我们开学第一天一起亡命狂奔的情分,对我十分殷勤照顾。
富贵乡里多浪子,我不喜欢纪洲那嬉皮笑脸样。
我讨厌纪洲。
讨厌他总是轻松自如的样子。
讨厌他莫名的松弛感,漫不经心的,满不在乎的。
搬书时,纪洲伸过手。
“我来帮你。”
“不用了,谢谢。”
搬桌子时,纪洲凑上来。
“我来帮你。”
“不用了,谢谢。”
纪洲后知后觉:“言清,你是不是讨厌我,我做错什么了吗?你怎么对别人都很好,对我这么坏?”
我面不改色地扯谎:“哪有。都是同学,哪能不一碗水端平?”
他点点头,自信道:“也是,我这么英俊潇洒,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不可能被讨厌!”
得,这少爷,要是手边有镜子,他能天天揽镜自照,课都别听了。
纪洲顿了顿,又有些哀怨地看我:“不对啊,言清,什么叫一碗水端平?我可是你同桌哎,没有点优待吗?就是什么加分啊、VIP待遇之类的?”
“同桌太聒噪,倒扣两分。”
他不说话了。
03
一中是公立的名牌中学,校风校纪很好。
为了防止攀比,学校规定学生必须统一穿校服,不得化妆,不得带电子产品。
校服一穿,众“生”平等,谁看得出你有钱没钱?
虽然有同学会在鞋子和配饰上下功夫,但总的来说,有钱人家的孩子和穷人家的孩子能比较和谐地共处同一屋檐下。
可就连朴素的校服也掩盖不住少爷温柔乡里泡出来的金贵气儿。
开学迎新晚会,纪洲被硬拉去钢琴伴奏。
音符从他的琴键上流出。
他脱去了校服,穿上了白色西装,一身清贵从容的样子,很扎眼。
他下了台,跑过来把一束花给我。
“借花献佛,孝敬我同桌。”他眼睛亮亮的。
我笑了笑。“别人送你的,我不要。”
“我送你的,你更不会要。”他垂头,小声咕哝了一句。
脱去了平等的假象,他是天上云,我是地下泥,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班长身上,好像有股奇怪的味道诶。”
“什么?哎真的,看起来白白净净一姑娘,不会不洗衣服不洗澡吧?”
“嘘,别让班长听到了!”
我抬手闻了闻衣袖,是半地下室阴暗潮湿的味道,我用肥皂使劲搓也搓不掉。
书上说,人有三件东西无法隐瞒:贫穷、咳嗽和爱情。
开学没多久开了一次家长会,纪洲的爸爸西装革履,看到我爸爸时神色一变,他倒还是个体面人,只是微妙地把椅子移远了一些。
贫穷就是我的附骨之蛆,将我腌入了味儿。身边的人闻着味儿就吓跑了,何况纪洲这么一个金尊玉贵的小少爷呢?
04
每个人都是出来卖的,只是卖的东西不同而已。
为了挣钱,白天,我是市重点高中的高冷学霸。晚上,我就成了夜店一条街的卖花女郎。
“小姑娘,新来的?怎么卖?”一个衣冠楚楚的青年带着轻浮的笑意,看的不是花,是我。
他的目光在我身上上下逡巡:“按时还是按次。”
他二十岁上下,个子很高,带着上位者慵懒从容的压迫感,俯视我,像山一样挡住了我眼前的光。
我又不适,又生起一阵惧意,支支吾吾道:“不......不是,我不是......”
“不是,不是什么?”他好整以暇地笑:“不是你来这儿做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眼前浮现了苍老的男人躺在床上面无人色的样子,我心里诡异地平静下来。
“你能给多少?”我不再害怕,抬头直视他的眼睛。
他噙了抹玩味的笑,折了朵玫瑰花插在我的丸子头上。“那要看你表现了。”
“言清!”一个声音带着急切破空而响。
纪洲拽开眼前的男人,“不好意思你谁?离她远点。”
“我谁?”男人似笑非笑。
“哦,二哥,失礼。”
“怎么,你看上她了?”
纪洲忽然吊儿郎当地揽住我的肩膀,就差把纨绔这两字写脸上了:“害,别说出来啊,多不好意思,我们还有事,就不打扰你寻欢作乐了。”
05
真纨绔“二哥”走后,我挣开纪洲的手,故作玩笑道:“少爷的夜生活还挺丰富。”
那张总是笑嘻嘻的脸上却没有表情,我才发现,纪洲面无表情时,眉目锋利又冷冽,有些吓人。
“怎么卖?”他说。
我一直在发抖,听见这三个字,又没忍住发起抖来。
“......啊,啊?”
“花,怎么卖?我全要了。”
我低头默默包花,低头不敢直视他的目光。
每次,纪洲都能撞破我最狼狈的样子,真是......讨厌啊。
他的声音里压着怒气:“你来这里做什么,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反唇相讥:“你来这里做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他不气反笑:“你以为我来这里干嘛?”
我犹豫道:“寻欢作乐?”
“言清,我在你眼里就这种形象是吧?”说话时带着幽怨和委屈。
可不是吗?一个人五人六的富家公子哥。
他把他哥戴在我头上的玫瑰花摘了下来,扔在地上,泄愤似的踩上几脚。
“言清,我们都是一样的。”
他娓娓道出一个故事。
他妈妈初中辍学进城,没有学历,只能找到夜店的工作,纪家的少爷来买醉时相中了她,和她春风一度,于是便有了纪洲。
少爷只是来买了一回春,哪里记得那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配角,他妈妈为了养活他,做了暗娼,有不认识的叔叔来时,纪洲便被打发去守门,那时一个阿姨常常关照他们,给他们送饭送菜的。
夜店街是纪洲长大的地方,他今天来这儿,就是来看望生病的阿姨。
后来女人年老色衰,身体也不好了,纪洲八岁时,她心一横,去纪家闹,要让纪洲认祖归宗,过更好的生活。
正好纪家的老太太在家,见是个孙子,做了亲子鉴定确认血缘关系后,便同意去母留子,纪洲他们养,这个不正经的女人不能进纪家家门。
女人很快就病逝了,纪洲都没见着她最后一面。
纪洲在纪家也只是表面风光,他上面有三个哥哥,他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子,谁也不拿正眼瞧他,反正纪家有钱,多一张嘴吃饭而已,当个宠物养着呗。
纪洲认真地看着我,再次重复。
“言清,我们都是一样的。”
06
我以为少爷富贵逼人,和我们这些夹缝求生的蝼蚁不同。
原来,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父母都是农村出身。
十几岁时,辍学进城打工。
二十岁上下,父母一催,媒人一撮合,就这么仓仓促促结了婚。
我对童年最多的记忆便是无止无休的争吵。
锅碗瓢盆的哐啷声、女人歇斯底里的怒吼、男人的沉默。
他们谈论工作,谈论生活,谈论房子里的老鼠,谈论这个月房租,谈论三姑六姨姐姐妹妹过得如何如何幸福。
贫贱夫妻百事哀,连吵架都是毫无逻辑的情感宣泄。
像要把一生的郁郁不得志,怪罪到这桩既没有物质基础也没有精神支柱的婚姻。
我六岁那年,他们终于离了婚。
离得鸡飞狗跳,很不太平。
妈妈跟着一个姓刘的叔叔走了。
他在隔壁市有三套房,条件是妈妈不能要我。
他说跟着他,妈妈可以安心当家庭主妇,在家带孩子,吃穿不愁,过好日子。
妈妈走的那天,给我买了公主裙,带我去了平时吃不起的肯德基。
她红着眼看我吃完,然后用她新买的诺基亚手机给爸爸打了电话。
她声色陡然冷下来,名字都不愿叫。“我要走了,来接人吧。”
我放下手中的鸡腿,将手上的油在袖子上擦了擦,拉着妈妈的衣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