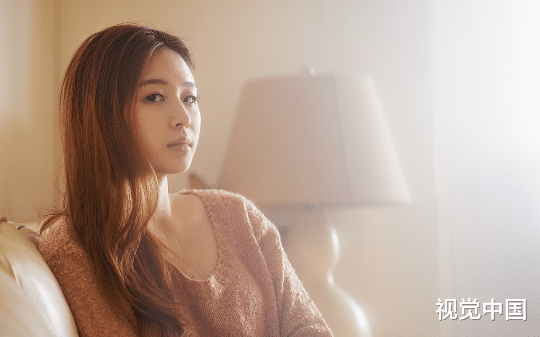和男友相恋一年。
我才知道他来自苗疆,上面还有个哥哥。
在他们那,兄弟需共侍一妻。
起初,男友的哥哥满眼冷漠的看着我们,冷声丢下句:
“要谈恋爱,滚出去谈,别扯上我。”
可后来,一向温和的男友红着眼求我只爱他一个人的时候。
哥哥正将我按在门后,
在我脖颈处占有欲极强的落下红痕,漫不经心问:
“要他?还是我?”
“或者说,你都想要?”
我流出了泪。
那是激动的。
1
这是我头一次来到苗寨,便正巧碰上了家族大会。
女性都端坐在座位上,穿着苗服,威严庄重。
部分年轻男性却跪坐在地上,身着便服。
南寻坐在我身边,勾着我的指尖,微微凑近我的耳边解释:
“在苗寨,女子为尊,有对象的男人可以坐着,但是没对象,得跪着,托你的福,这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坐着。”
说话的时候,他顺着指尖,将我的手整个握住。
从旁人角度看,就是年轻小情侣在腻歪。
但是只有我知道,他是皮肤饥渴症发作了。
我看了他一眼,轻笑:
“再忍会,乖。”
我粗略的扫了眼众人。
又发现,跪在最中间的那个,他是所有跪着的男性里,唯一穿着苗服的,还带了个面纱。
他始终低着头,眉间隐隐皱着,似乎是在忍耐什么。
手指关节和指尖都是粉的,青筋却明显。
美人在皮在骨,更在气韵。
这是个极品。
不等再看,身侧伸过来的手捂住了我眼睛。
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和:
“他好看吗?”
出于对男朋友的了解,我反勾了下他的手:
“不如你。”
南寻出乎意料的对这个答案不满意,意味不明的哼了声:
“那是我哥。”
话刚落,又是一道威严女声传来——
“在我们苗疆,兄弟需共侍一妻,望诸位谨记!”
跪着的人第一次抬起了眼,直直的朝我和南寻看过来。
漂亮的像琉璃一样的眼睛里,满是厌恶。
家族大会一结束。
南寻便迫不及待的将我抱进怀里。
扣在我腰后的手一寸寸收紧,像是要把我融入他的骨髓。
骨头勒的有点疼,但我只是愉悦的纵容他。
他声音狠戾,完全不同于平日的温柔:
“不准看我哥!只能看着我,什么兄弟共侍一妻,你只能是我的!”
我顺着他的话哄他:
“嗯,我是你的。”
可脑子里,那双漂亮的眼睛,始终挥之不去。
越想越兴奋。
被强迫的倔强美人。
那可真是,太有意思了。
门外传来敲门声。
南寻是将我抱在怀里,开的门。
门外,脑海里的美人化作了真人,站在那。
他还是穿着苗服、戴着面纱,小铃铛挂在他腰间,风一吹,就叮叮作响。
眼神比在家族大会上还要冷漠,声音也冷:
“要谈恋爱,滚出去谈,别扯上我。”
南寻嗤笑:
“正有此意。”
之后,一连在苗疆待了七日。
但我都没能再见到,这个漂亮的苗疆少年。
南寻似乎对这个哥哥很有敌意。
凡是知道他哥哥会去的场合,他都找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不带我去。
那架势跟防贼一样。
直到,苗疆举办春日宴,南寻前去帮忙准备。
临走前,他再三嘱咐我:
“不要找南青,他不是什么好人,看见他就离远点,我三天后就回。”
我面上乖巧点头。
实则心里想着,原来,他叫南青啊,莫名配他。
南寻看出了我的阳奉阴违,温柔一笑。
下一秒,恶狠狠的掐着我的下巴,咬在我脖颈上。
我疼的“嘶”了声。
看着清晰的咬痕,南寻满意离开。
可到底天不如人愿。
他走的当天下午,我就碰到了南青。
他正在路边哄一个哭闹的孩子,神情特别温和。
跟看到我和南寻的时候截然不同。
“苗疆那么多人,为什么只有你,需要每日戴面纱穿苗服?”
我自认为笑意温和的走过去。
却见南青骤然冷了脸色,将孩子抱在怀里,转身就走。
我不再说话,只不紧不慢的跟在他们身后。
南青猛得转过身,眉眼紧皱,似乎是忍耐到了极限。
“要么跟他分手,要么离开这!”
“再待上几日,我就离开,至于分手,那不可能,南寻很爱我,我也……爱他。”我还是微笑着。
他嗤笑声,神情讥讽,视线落在我手腕上的红绳——那是南寻送给我的。
“爱你?蠢货!”
说完,他再不理我。
搭上话了,我也不贪心,没跟上去。
南寻离开的第二日。
我在苗寨里发现了个湖。
湖水很神奇,岸边居然有小贝壳,在阳光的照耀下,像是在发光。
我想了想,南寻最喜欢这些漂亮的小物件。
于是,我捡了十来个,打算给他亲手串个手链。
我找隔壁阿翁借了工具。
在我道完谢、准备离开时,阿翁突然出声:
“你是南寻那孩子带回来的吧?别被他的皮囊骗了,他和他哥哥,会蛊毒,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漫不经心的应了声。
不是好东西?那有什么关系。
正好我也不是。
一个下午,我都在串手链,自然没有再见到南青。
临近傍晚,手链才串成。
我洗完澡,只披了件薄裙,就躺在床上睡去。
迷迷糊糊间,我似乎听见了铃铛声,然后有人躺在了我身边。
起初,只是握着我的手。
到后来,来人低骂了声:
“该死的共感!”
共感?谁和谁?
我的意识想醒过来。
可眼皮沉沉的,完全睁不开。
我被人以一种严丝合缝的状态,完全抱进了怀里。
没来由的想。
南寻犯皮肤饥渴症的时候,也喜欢这样抱着我睡。
可他现在不在。
所以,这人是谁?
2
第二日睁眼时,床上只有我一个人。
身侧是冰凉凉的,没有温度。
我起床吃了个早餐。
门便被推开了。
是南寻回来了。
几天不见,皮肤饥渴症应该已经发作到他的极限了。
我笑着等他冲过来抱住我。
可出乎意料的。

南寻只是走到我跟前,就不动了。
哪怕是嘴角勾着笑,也挡不住他眼底的阴鸷:
“南青碰你了?”
“宝贝,我跟你说的话,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还没等我弄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我就被他扔到了床上。
他面色已经彻底冷了下来,桌上放着的给他做好的贝壳手链,被他拿来绑住了我的双手。
他一向脾气好,或者说他一向把自己的脾气伪装的很好。
可这次,是为什么生气?
我刚想张嘴询问,就被他的手用力捂住。
“有些事情,既然说不明白,那就别说了。”
“用做的。”
我开始慌了。
把狼驯服的太好了。
以至于,我差点忘了,再温顺,也是狼,不是狗。
我和南寻是在一次学生会活动上相识。
彼时,我刚上大二,而他是我的学长。
南寻模样好,性格又温和,谁都喜欢他。
我也不例外。
于是,我果断甩了当时的男朋友。
前男友以一种释然的神情,对我笑了下:
“谢迦,你又看上新的猎物了是吗?”
“你早晚会遭到报应的。”
我不以为然。
遭报应?
呵,笑话。
第二天,我开始追求南寻。
三个月后,拿下。
在一起的那天,南寻掐着我的下巴说:
“那就和那些阿猫阿狗都断干净,以后,你只能是我的。”
他又想了想,软了神情:“我也只是你的。”
阿猫阿狗?是指我的那些前任吗?
我笑着应好。
可是,或许真是应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
不出一个月,我腻了,转身勾搭上了个小学弟。
我永远都记得,被南寻发现的那天。
我还在不知死活的挑衅他:
“你也看到了,我喜欢上别人了,分手吧,拖下去对你我都没好处。”
南寻背着光站着,对我特别温柔一笑。
我被美色蛊惑了一瞬间。
等回过神的时候,我被他关进了一个房子里。
他看着我,笑得残忍:
“不听话的人,要什么自由?”
之后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没下来床。
每次往床下跑,就会被他掐着腰拖回来,任由我哭喊,都无济于事。
最后,我的身体害怕的下意识发抖,但还是紧紧的抱着南寻。
他温柔的摸了摸我的脑袋:
“你爱谁?”
我抱得更紧了:“南,南寻。”
南寻满意了,在我手上带了个红绳,放了我。
从那以后,无论我在哪里,南寻总能第一时间知道我的行踪。
我以为我会恨他。
可实际却是,我的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

这是我自从八岁被双亲抛弃、整日流离失所后,最踏实的时候。
这是病态的,但我没办法抵抗。
我冷眼看着自己的堕落,清醒看着自己的沉沦。
再没动过其他心思。
直到,来到苗寨,看见了南青……
我意识恍惚的过了三天,流干了眼泪,落了一身的痕迹。
最后,缩在南寻的怀里,哭着说只爱他。
他气消了大半,戴上沾了我气息的贝壳手链,又恢复了温柔的模样。
“南青和我自幼共感,我们其中一人的一切感受,另外一人全都能感受到,我有皮肤饥渴症,他也有。”
“从三天没碰到你,但是皮肤饥渴症却没有发作开始,我就知道,他碰你了。”
他像是神话故事里,诱哄路过船夫的漂亮人鱼。
“所以,告诉我,他碰你哪了?”
我哆嗦了下。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南寻似乎是笑了下,双唇贴在我的耳边:
“我相信你,你可别骗我啊。”
双脚落在地上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不真切的实感。
南寻被隔壁阿嬷叫走了。
我下意识的拉住他的衣角,这是我的戒断反应。
他笑了笑:
“乖,我很快就回来。”
一个小时后,戒断反应消失,我恢复正常。
但我还没等回来南寻。
反而等来了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