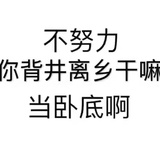摘
智永的《千字文》以楷书和草书体书写,有多种版本。启功的研究展示了法书文献的复制方式及流传轨迹,还强调《千字文》具有启发童蒙、流传广远的实用价值。这有助于人们了解古代法书文献的版本知识、认识“王羲之这个角色”、拓展法书文献出版物及书法教学“启发童蒙”的功用,同时也为研究中国特色的阅读史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案例。
关
启功;智永;千字文;法书文献;童蒙读物;阅读史
作
于翠玲,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1期。
中国古代的书法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许多著名的法书文本,通过临摹、碑帖、刊印、辑录等方式得以流传后世,形成了积淀深厚的法书文献。启功先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书法家,在书画文献的鉴定和考证方面造诣高深,著述颇多。其中对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版本的考证历时多年,有《说〈千字文〉》及题跋,还有两首《论书绝句》,展示了法书文献的复制方式及流传轨迹,为探讨《千字文》的文化价值和实际功用提供了思路,也为研究中国特色的阅读史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案例。

01
考证智永《真草千字文》的流传轨迹
01
早年研习影印本
启功先生对《千字文》的研究是从学习书法开始的,他自述“六岁入家塾,字课皆先祖自临九成宫碑以为仿影”;20多岁后“杂临碑帖与夫历代名家墨迹,以习智永千文墨迹为最久,功亦最勤”;“接触《千字文》,实从习字临帖开始。既是一字字地临写,就发现了许多异文……不免发生哪个对、为什么不同诸多疑问。后来逐渐留心有关《千字文》问题的资料”;23岁时根据所见从日本传回的《千字文》版本,写了《论书绝句(七)》:“砚臼磨穿笔作堆,千文真面海东回。分明流水空山境,无数林花烂漫开。”此诗附有说明文字,列举了智永《千字文》的五个版本,并将群玉堂本与墨迹本比较,认定智永的墨迹本是真面目,而且指出对研究书法史有重要价值:智永写《千字文》八百本,分施浙东诸寺,事见唐何延之《兰亭记》。千数百年,传本已如星凤。世传号为智永书者并石刻本合计之,约有五本:大观中长安薛氏摹刻本,一也;南宋群玉堂帖刻残本四十二行,自“囊箱”起至“乎也”止,二也;清代顾氏过云楼帖刻残本,自“龙师”起至“乎也”止,此卷为明董其昌旧藏,戏鸿堂帖曾刻其局部。近获见原卷,黄竹纸上所书,笔法稚弱,殆元人所临,三也;宝墨轩刻本,亦殊稚弱,四也;日本所藏墨迹本,五也。此五本中,以一、二、五为有据,长安本摹刻不精,累拓更为失真。群玉本与墨迹本体态笔意无不吻合,惜其残失既多,且究属摹刻。惟墨迹本焕然神明,一尘不隔。非独智永面目于斯可睹,即以研求六朝隋唐书艺递嬗之迹,眼目不受枣石遮障者,舍此又将奚求乎?启功先生当时所临写和参考的是罗振玉的跋文及影印本。据他后来记述:“1912年日本小川为次郎氏把所得到的一个墨迹本交圣华房(出版社名)影印行世,后有日本内藤虎次郎氏跋尾,从此许多人才见到一个可靠的墨迹本……此后几年,上虞罗氏重印此本,后有罗叔蕴先生跋尾,便理直气壮地说它多力丰筋,实是智永八百本之一的真迹。从此时以至今日,智永的书写权愈来愈被确认了。”还有一个佐证,启功先生曾将这个影印本呈送书法家、金石鉴赏家张伯英观赏,张伯英“见而大惊,曰:‘此六朝人之墨迹也’”。罗振玉1918年所作《智永千文跋》附在《智永真草千文真迹》影印本后,说明:“后于东友小川简斋许得见此本,则多力丰筋,神采焕发,非唐以后人所得仿佛,出永师手无疑。昔贤评右军书势雄强,永师传其家法,固应尔尔。此不但可压倒关中本及顾氏所藏,且可证宋以来官私法帖右军诸书传摹之失。亟写影精印,以贻好古之士,即此以求山阴真面,庶几其不远乎?”罗振玉在日本见到了《千字文》墨迹本,参照关中本和顾氏藏本,鉴定墨迹本为智永所书真迹,并以日本影印本为底本在中国重印。启功先生所谓“真面”“多力丰筋”等评语就出自罗振玉的题跋,可见他最初见到的就是罗振玉重印的影印本。这个影印本在当时被不少学者看到,马叙伦就说:“余谓智永《真草千文》真迹今尚传世,余见日本影印本,风韵自不待言。”启功先生列举了五个版本,并对罗振玉提到的“顾氏所藏”本,根据“近获见原卷”加以考辨,详细说明“清代顾氏过云楼帖刻残本”的流传情况和版本特征,认为其“笔法稚弱,殆元人所临”,这就是相对墨迹本“多力丰筋”而言的。启功先生《说〈千字文〉》提到法国人伯希和1932年发表的《千字文考》。伯希和1908年到达敦煌,带走了藏经洞中的大量文献。其《千字文考》开篇就说“千字文是中国从前儿童初学的一种字书,外国人的译本很多”,有根据汉文、高丽文、日本文版本而译成英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的,还有一种蒙古文本;还提到“在敦煌石室发现了几本周兴嗣的千字文”,其中有一本附有西藏文的音释,由此可见《千字文》在海内外广泛流传的信息。此文的重点是引证中国古籍中相关资料,逐一辨析有关《千字文》的传说或故事。启功先生认为:“伯氏着力在周兴嗣这篇《千字文》撰写过程,并讨论流传各种本子的真伪,对所谓‘王羲之书钟繇千字文’进行辨伪。”而新发现的日本墨迹本提供了有力证据,“近数年原卷出现,有影印本”,足以证明“其为凭空捏造,望而可见”;伯希和对“其他有关《千字文》的问题,由于着力点不同,反倒未暇谈及”。02
晚年鉴定墨迹本
启功先生1974年作《日本影印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跋》,这时所见是日本影印的墨迹本,肯定“乃唐时传去者,其笔锋墨彩,纤毫可见。证以陕刻及群玉堂刻四十二行,益见墨迹之胜。此直是永师手迹,无容置疑。多见六朝隋唐遗墨,自知其真实不虚”;“余既定之为当日浙东诸寺中八百本之一”,并作诗赞之:“永师真迹八百本,海东一卷逃劫灰。儿童相见不相识,少小离乡老大回。”此诗收入《论书绝句(三十六)》,并附注简单说明用于对校的版本:“智永千文墨迹本,唐代传入日本,持较北宋长安刻本及南宋群玉堂帖刻残本四十二行,再证以六朝墨迹,知其当为永师真迹。”这里只提到两个用于比较的《千字文》版本。1988年7月发表的《说〈千字文〉》,全面梳理和考订有关《千字文》的版本问题。其中依次列举“智永《真草千字文》写本、临本和刻本”,共有五种:智永墨迹本、敦煌发现的唐初人临本残卷、宋薛嗣昌摹刻本(碑石在陕西西安碑林)、南宋《群玉堂帖》刻残本、宝墨轩刻本。与1974年的跋相比,去掉了“清代顾氏过云楼帖刻残本”,增加了敦煌发现的临本残卷,而最有价值的是日本藏“智永墨迹本”,被置于第一位。《说〈千字文〉》“附记”特别说明:“余于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九至日本京都小川氏家,获观原本,装册褾手不精,每半页四边镶以绫条,其风格似清末褾工,殆即明治末年所装,计其改卷为册,当亦即在此时。硬黄纸本,黄上微泛淡褐色,盖敦煌一种薄质硬黄纸经装褾见水时即呈此色。其字每逢下笔墨痕浓重处时有墨聚如黍粒,斜映窗光,犹有内亮之色,更可知绝非钩描之迹也。”2001年启功先生回忆张伯英时也称:“功年八十,始于小川为次郎氏家见其遗物,《千字文》墨迹赫然寓目,证以敦煌所出隋唐硬黄写本落笔处墨痕如漆,足知为永师散施浙东之本,而为使者携归之物,毫无可疑。回忆勺翁见影印本而惊叹之,弥足征信。”03
考证墨迹与文词
法书文献与其他古籍文献的不同是,为了保存书体的整体面目(“真面”)而不失真,采用了特殊的复制方式,形成了特殊的版本形态,“法书这个称呼,是前代对于有名的好字迹而言。墨迹是统指直接书写(包括双钩、临、摹等)的笔迹”,“碑帖是指石刻和它们的拓本,这两种,在我们的文化史上都具有悠久传统和丰富的数量”。启功先生自言“半生师笔不师刀”、“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这不仅是学习书法的路径,也是鉴定法书的方法,因为“墨迹之笔锋使转,墨华绚烂处,俱碑版中所绝不可见者。乃知古人之书托石刻以传者,皆形在神亡,迥非真面矣”。对日本所藏智永《真草千字文》,启功先生正是根据观察“其字每逢下笔墨痕浓重处时有墨聚如黍粒,斜映窗光,犹有内亮之色,更可知绝非钩描之迹矣”,还有“多见六朝隋唐遗墨”的经验,得出结论:“智永写本的周兴嗣《千字文》应是这篇文今存的最早的本子,是毫无疑义的。”这个《千字文》墨迹本实物是使“眼目不受枣石遮障者”,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启功先生对其他书画的鉴定也是如此,“必审笔墨之精粗,神气之雅俗”。例如《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与宋刻本》指出:“后来用墨迹本和石刻本并列临摹,发现墨迹本确实比石刻精采,这原是法书传本的通例。”他对智永书《真草千字文》墨迹本的考证,对校了多种版本(敦煌临写本、碑刻本、影印本),也呈现了这一《真草千字文》递藏和流传的历史轨迹:日本藏墨迹本—日本影印本—罗振玉影印本;而他获取这一版本的过程是:罗振玉影印本—日本影印本—日本藏墨迹本(原件)。他通过数十年的临摹、追踪和探讨,终于根据所见墨迹本原件,特别是“惟墨迹本焕然神明,一尘不隔”,或者说“多力丰筋,神采焕发”的神韵,进一步确定这是智永所书《千字文》八百本之一。研究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除了鉴定书体墨迹,还要考证“文词内容”,涉及字义、避讳、音韵、辨伪等方面的文献学知识。启功先生早年临写《千字文》“就发现了许多异文”。《说〈千字文〉》通过辨析文字的含义和写法,说明是先有真书,后有草书;针对不同版本中的异文现象,说明“‘律召’作‘律吕’的写本,最早见于怀素小草书写本”;辨析“薛氏刻本”中的宋讳字,如“玄(缺末笔)”。而敦煌发现的唐初人临本残卷“草书‘煒’字真书作‘瑋’字,与日本藏本完全一样,使我真要喊出‘一字千金’了”。1993年所作《南朝诗中的次韵问题》一文说明《千字文》“题目称‘文’,而全篇四言为句,隔句押韵,又换韵转押,分明是一首四言长诗”;接着考证“周兴嗣次韵”问题,认为“从文章上看,是周氏次韵所撰;从书法上看,是一卷王羲之的字”,并进行辨伪:“宋人造出那卷‘钟繇千字文王羲之书’一卷伪物,使人觉得周兴嗣次韵的就是这卷《千字文》。其实这卷钟文王书的《千字文》完全不成语句,更无韵脚可次,真可以说作伪心劳日拙了!”02
《千字文》流传轨迹的启示意义
启功先生《说〈千字文〉》是对自己从临写到考证《千字文》的一个总结。其开篇的概述尤其值得关注:“以‘天地玄黄’为起句的《千字文》,名头之大,应用之广,在成千累万的古文、古书中,能够胜过它的,大约是很少很少的。只看它四字成句,平仄流畅,有韵易诵,没有重字(没有重复写法的字),全篇仅仅一千字,比《道德》五千言这本著名的‘少字派’书还少着五分之四。它便利群众,启发童蒙。其功效明显,流传广远,难道不是理所应得的吗?”有关《千字文》“便利群众、启发童蒙”的作用,正是《千字文》不同于其他法书文献的特点,因而涵盖了更为广泛的文化普及意义和实际利用功能。01
了解古代法书文献的版本知识
启功先生考证《千字文》,列举了“智永《真草千字文》写本、临本和刻本”。目前尚存的可靠实物版本或者说文献证据,一是墨迹本(原件之一流传到日本,现有影印本);二是敦煌发现的唐初人蒋善进临本残卷(图1);还有宋代薛嗣昌摹刻本(碑刻现在西安碑林)。参照启功先生《关于法书墨迹和碑帖》一文,可以窥探法书文献为了保真而采用的复制方式及其所形成的流传轨迹。
02
认识“王羲之这个角色”
为什么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能够流传下来,成为历代书家临写、品评的对象?启功先生指出“千字文故事中有王羲之这个角色”。智永是陈隋间的僧人、王羲之的七世孙,曾收藏王羲之所书《兰亭序》等真迹。他专心临摹王羲之的字,曾经书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赠多处佛寺,致力于传承王羲之的“家法”,如启功先生所说:“智永所临,当然是王羲之的字,那么智永所临《千字文》中的字样,即是王羲之的字样了。”王羲之在书法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自晋以下,南朝书风的衔接延续,在王氏门中,更可看出承传的紧密”,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北宋时御制的《宣和书谱》梳理了一条线索:“释智永,会稽人也,晋右将军王羲之之裔。学书以羲之为师法,笔力纵横,真草兼备,绰有祖风……又作真、草书《千文》传于世,学者率模仿焉。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三。”假如是一个普通僧人所书写的一篇千字诗文,是不可能被后人不断临摹而蔚成风气的。更为重要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引导作用,他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他也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先是释智永善羲之书,而虞世南师之,颇得其体,太宗乃以书师世南”。其他文臣也以智永为师法对象,例如,“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柳公权曾“一纸行书十一字曰: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纸草书八字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帝尤奇惜之”。实际上书法已经成为朝廷“润饰太平”的一种媒介,也是用于“宣赐”的文化仪式活动。历代皇帝及其文臣竞相书写的《千字文》数量颇多:有的传承智永的真草“家法”,临写逼真;有的变化出新,不拘一格,例如宋徽宗的瘦金体《千字文》、文征明的《四体千字文》、赵孟頫的《六体千字文》,等等。《四库全书》在子部“艺术类”有“书画之属”,或者说书法被归入“艺术类”。其中收录清代倪涛《六艺之一录》,在“法帖论述”中列有“千字文”类,专门收录历代有关《千字文》的资料。民国时期,伴随着石印、影印技术的发展,名家书体的《千字文》成为书局推广的商品,报刊可见“赵文敏公真草千字文帖,一册八分”(1915年《申报》)、“元鲜于枢赵孟頫合笔草书千字文卷(宋纸本)”(1920年《益世报》)、“周兴嗣千字文帖一角五分”(1921年《申报》)、《智永真草千字文》碑帖本(商务印书馆1933年)等广告。由此可见,以《千字文》为线索,可以追溯王羲之书体的深远影响及其历史背景。而历代名家以《千字文》为文本而衍生的各种法书文献及其出版物,也是窥探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书法文献阅读史的一个窗口。03
拓展“启发童蒙”的功用
智永《真草千字文》作为法书文献在上层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古代书法家对周兴嗣《千字文》的内容并不重视,古代朝廷设置的“书学”不以《千字文》为教材。《千字文》由于“名头之大”,被私塾先生当作童蒙教材,反而在民间广泛传播。《千字文》作为童蒙教材,具有包括识字(不重复的千字)、写字、读文、道德教化以及编排序号等功用。例如,敦煌遗存的《千字文》写本中就有“学童初学识字所写”的残片,由老师在纸上写出《千字文》中若干字的楷体,让儿童在下面反复临写练习。元代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规定:“小学习写字,必于四日内,以一日令影写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写者,先以子昂所展千字文大字为格,影写一遍过,却用智永如钱真字影写。每字本一纸,影写十纸……其所以用千文、用智永楷字,皆有深意。”直至晚清民初,以书写本(手抄本)、小册子流传的《千字文》课本,在民间私塾仍然不计其数。民国初期,伴随着社会文化及教育体制的变革,主管部门开始“停闭不合程序私塾”,因为“取阅课本大都《千字文》《百家姓》,询其讲解茫无以对”。新式小学开始采用新编的语文教科书,《千字文》用于识字、习字的功能被取而代之。1929年发表的《小学初级写字教学法》一文说明:儿童刚入学时年龄小、能力弱,“采用毛笔太嫌费事费力;而且铅笔字在将来生活上应用很广博的”;到第二、三学年再安排写毛笔字(大楷、小楷),临摹字帖;建议根据儿童已认识的字,将所选字帖中艰深的字去掉,加上九宫格,编成一种适合儿童临摹的字帖。从实用角度来看,书写工具已经发生变化,硬笔写字逐渐普及。1931年《申报》有关《国语科教学》的消息说:“在从前社会上所需要的是软笔字(就是毛笔字)。可是现在社会上所需要的是,软笔字变为钢笔字了。如果在现在时候,学习写字,仍和从前一样,只用软笔不用硬笔,实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千字文》押韵成文,便于诵读,但内容繁杂,难以理解。古代私塾老师让儿童背诵,并不讲解,所谓“牧童三五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古代也有多种注释本,例如明代娄芳撰、娄国安校梓《千字文释义》,注释颇为详细,但不适用于童蒙教学。民国时期,《千字文》这本家喻户晓的童蒙读物,在民间私塾依然有广泛需求,民营书局纷纷印行各种小册子。为了适应新式学校的教育内容,书局开始对《千字文》的文本进行改编,特别标明其新特点而加以推广:有的附加了绘图、注音、标点、言文对照等内容;有的选择楷书字体,有的采用印刷铅字。例如,书名标称《新式标点千字文白话注解》(1927年,图2),用楷书体,配有插图;蔡元培题签的“注音注解、言文对照千字文”(1937年,图3),用印刷铅字排版,四句一页,附加了注音字母,用白话文简明注释每句的内容。各家书局采用的封面也竞相出新,早期的封面有的是旧式私塾的师生图,类似明代仇英的《村童闹学图》;而新式书局的《千字文》,彩色封面上已经出现衣着时尚的小学生快乐游戏的画面。绘图本的内容也有新意,一本《蒙学千字文》配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两句,第一张插图是半个“地球”。这种《千字文》新印本考虑到儿童喜欢图画的心理,补充了教育部门新制定的文字语言规范,已经被改编为儿童识字读本。各家书局出版的小学生读本《千字文》,其版本略有差异。有的仍存在启功先生所提到的避讳改字现象,如“玄”改作“元”、“律召”改为“律吕”。这正如启功先生所言“《千字文》是以蒙书的身分被传习的,教蒙书的人,自以普通文化程度的为多”,因此这些字就都流行起来。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成立的中华书局印行《初等小学中华国文教科书》,其版权页附有广告语:“千字文,刚读完,父母心喜欢。明日起,读国文,中华书局出版最有名。语句好,记得清,有图画,更鲜明。我们快快读,莫负好光阴。”这则广告的内容很有趣,是对小学生的召唤,可以看作是从在私塾读《千字文》过渡到在小学读新式国文教科书的一个标志。


03
结 语
综上所述,启功先生对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的研究,从临摹其字体、考证其文字,到目验其墨迹、辨析其版本,历时多年,反复揣摩,心领神会,见解独到。其中记录和呈现了书法大家对法书文献所特有的阅读方式和体验过程,包括“真要喊出‘一字千金’”的发现、请名家观赏“见而大惊”和“大喜”的情景,为从阅读史角度研究中国书法文献提供了具体生动的个案。《千字文》作为一种被阅读的出版物,其绵延不绝的流传轨迹包括两个层面:上至宫廷层面,衍生出多种名家书体的法书作品,被多次辑录刊刻;下至民间层面,演化为乡村私塾的童蒙教材,被不断改编出版。这二者既有关联,也有错位,由此形成了“名头之大,应用之广”的阅读效应。《千字文》的历时性阅读和传播,受到政治环境、书法功能、文化变革、媒介更新(包括复制技术、换笔)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千字文》通过儿童在私塾诵读和临写的方式,逐渐成为乡村百姓耳熟能详、触手可及的读物。顾炎武曾记述识字书籍的变化:“盖小学之书,自古有之。李斯以下,号为《三苍》,而《急就篇》最行于世。”但《千字文》出现后,“不独以文传,而又以其巧传。后之读者苦《三苍》之难,而便千文之易,于是至今为小学家恒用之书”。中国古代的地方志中也有不少关于《千字文》流传的记载。此外,《千字文》还有许多流播海外的版本(中文本、翻译本、刊印本、新编本等),尤其对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如古代日本、朝鲜)有广泛影响,这是研究中国阅读史应该关注的内容。我们有必要了解《千字文》的流播轨迹及其所积淀的文化传统,拓展知新温故、中外交流的学术视野,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附记:此文作于2022年,谨以此文纪念启功先生诞辰110周年。转载自公众号“中国出版史研究”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汉语研究与社会应用实验室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