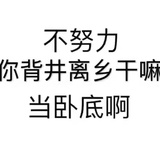无独必有对:朱熹《大学》《中庸》阐释的文本结构与经义生成
文丨白如
摘 要
文本结构的理据重构是经学典籍义理生成的重要方式,典籍的结构化程度与义理思想的致密程度具有正相关的联系。朱熹的《大学》《中庸》(简称《学》《庸》)阐释充分发挥章句体“离章辨句”的功能,通过文本结构的多维调试,完成理学化重塑。朱熹的哲学思想与注经实践内外贯通,“无独必有对”既是其理学思想层面的认识论,也是指导其经典阐释的方法论。尤其在《学》《庸》阐释中呈现出鲜明的对称化追求:对于经文中的对称表达,多通过“添加一致性概念”“嵌入成对式概念”的方式实现文本结构的重新分析;对于单句、句群、章节之中的非对称结构,则通过“二元切分”“并蒂架构”“对称排布”等方式实现文本结构的重新组构。在“无独必有对”理念的作用下,《学》《庸》阐释建构起围绕关键理学概念展开的义理体系,文本结构的系统性和精密化程度大大提升。其中就单句、句群文本脉络展开的结构化阐说,使得章句体具有了文章学的特征,义理阐释也更为邃密通贯。
朱熹采用章句体作为《大学》《中庸》(简称《学》《庸》)的注释体式,意在充分运用章句“离章辨句”的阐释功能实现文本结构的重新组织,服务于理学思想的阐发。除了“经”“传”二分、次第调整、重分章节这些较为显性的结构调整之外,朱熹对于《学》《庸》文本结构还有一些更为细密而精微的阐释理念,无论在表层形式还是在内在关系中,均呈现出非常鲜明的对称化追求,使得其《学》《庸》阐释呈现更为突出的“几何学般精美均衡的形态”。
学界对于朱熹理学思想的对称性特征已有诸多关注,钱穆感叹:“朱子之学,重在内外本末精粗两面俱尽。”又言:“一体两分,两体合一,此正朱子思想大体系所在,亦是其最著精神处。”陈荣捷称朱熹理学为“两轮哲学”,其他学者亦对此有“一而二,二而一”思维或“有对”思维等不同表述。哲学思想的研究是从典籍材料中提炼、概括思想家的核心观点,属于“是什么”层面的问题。而阐释学的关注要点则是思想家的思想观念“怎么样”落实的内在路径:认识论层面的思想如何渗透在具体的经典阐释之中,如何与经典文本字句段落的自身结构相适应,又体现怎样的规律性特征与个性化特质?本文关注朱熹《学》《庸》阐释的“无独必有对”理念,正是希望打通哲学思想与经典阐释,通过阐释方法论层面“潜理论”的提取和归纳,来挖掘朱熹在“就经为注”的有限空间内,生发经义、重构义理的内在机制。

朱熹
一、经义生成的方式之一:文本结构的理据重构
经义生成本质上是经典文本在不同文化语境影响下重新理解、重新分析的结果,可视为一种文本意义的“理据重构”。多数古代学者致力于透过经典文本推求圣贤之原意,带有一定的排他性与唯一性。朱熹的经典阐释要更为圆通包容,其言:“大抵圣贤之言,多是略发个萌芽,更在后人推究,演而伸,触而长,然亦须得圣贤本意。”经义在其初生阶段,只是存于未发将萌之态,还需后人推究申发、理解阐释,这也就给经典阐释的不同侧重、不同方向留有合法性的解释空间。张江选取“衍生”一词作为中国阐释传统的关键词,认为其“更能确当表达文本阐释在合理性约束下的扩张与流溢”,与朱熹之说相合。
(一)经义生成的两种机制
经典文献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通过重新阐释不断地获得生命力与影响力,但“思想”与“文本”之间并不具有天然关联,必须借助一定的内在机制予以转换,才能实现基于经典文本的义理重构。经义生成的内在机制可分为两种:其一是语词义位的重新选取,其二是句段关联的重新组合。如果将经典文本视为一个意义系统的话,那么“语词义位的重新选取”关注的是系统中各要素自身的意义,而“句段关联的重新组合”则着眼于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意义系统的迭代变迁,势必牵引着“要素”与“结构”的双重变化。在经典阐释实践中,经义生成的这两种机制往往彼此影响、相互配合。
“语词义位的重新选取”是历代训诂学家关注的重点。汉语语词的多义特征为不同的经典阐释者留下了充足的选择空间。一字之义有别,整句乃至整篇的意义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关乎思想体系的整体转向。如《论语·颜渊》中的“克己复礼”,何晏引马融之说训“克”为“约”:“马曰:克己约身。”宋儒则将“克”解为“胜”,程颐言:“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于仁。”朱熹也称:“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一个强调自我约束,一个强调战胜私欲,背后关涉的是汉宋体系下不同取向的修身法则。如此之例,不胜枚举。
“句段关联的重新组合”面向语言单位更大的句群、段落及篇章之间的关联关系,属于针对文本结构层面的理据重构。文本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意义之间脉络相联,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说“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又言“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就是在讲意义的完整表达与章节次第的排布之间有着内外相应的关联关系。反向来看,文本结构的重组也可以助力文本意义的转换与重构。经典文献文本结构的关联属性、组合方式不同,也会带来文本表意功能的差异,进而为不同的经义思想服务。
经学化程度越高的典籍,其文本结构也越为紧密。结构紧密体现在文本内容的关联性强、层次丰富。与此相对的则是文本要素的散点化分布,关联松散、层次单一。多数经学典籍的原生形态其实较为朴素,其经学化的特质多由后人的重新分析才得以突显。《春秋》属于编年体史书,其文本表层结构是按照时间次序单线排列的叙事路径。《春秋》三传为了突显其经学指向,皆从不同角度运用“以例说经”的方式来阐发经义:通过参照“例”之正变,来推度《春秋》微言之褒贬。“以例说经”使得经义的获取必须超越经文的线性顺序,同类比并、互相参照,大义方得体现,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大大增强。《诗经》在仪式乐歌向政教文本转换的过程中,文本结构的系统性也逐渐强化:汉代《诗经》学普遍有“以史说《诗》”的倾向,但三家《诗》多单篇散点地就《诗》论《诗》;《毛传》《毛诗笺》《毛诗谱》所共同构筑《毛诗》阐释体系则更注重篇际之间的前后关联,诗篇次第与帝王世系的联系更为紧密,且分“正”“变”,层次性更加突显,文本结构也更为致密。在诗篇内部的文本结构中,亦有通过调整章节划分传达不同经义思想的做法。《仪礼》《礼记》皆由单篇文献集解而成,篇目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强。郑玄编纂《三礼目录》,采用“吉凶宾军嘉”五礼之说整合《仪礼》,沿用刘向《别录》中制度、通论、丧服、祭祀等分类方法整合《礼记》。在具体的礼学阐释中,又以《周礼》为核心贯通三《礼》,建构起“三礼体系”,完成礼学典籍的结构化统整。马楠综合《春秋》三传及郑玄《三礼注》,提出“比经推例”之说,正是看到不同经注在方法论层面掘发文本结构关联的共通之处。
(二)无独必有对:
《学》《庸》文本结构的“前理解”
宋代理学体系下,《大学》《中庸》由《礼记》中的篇章升格为“经”,也面临着文本结构的升级任务。二程就曾在《明道先生改正大学》《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中分别对《大学》文本结构予以调整,为《大学》今本的设立导夫先路。除章次划分、文本顺序等较为显性的文本结构外,朱熹对于章节之内的句群、小节等微型文本结构的意义关系也有诸多阐发,其中文本结构的敏锐程度和重塑意识渗透在《学》《庸》的字里行间,广大与精微之处皆彰显着朱熹的理学思考。朱熹对于《学》《庸》文本结构评价极高:“近看《中庸》,于章句文义间窥见圣贤述作传授之意,极有条理,如绳贯棋局之不可乱。因出己意,去取诸家,定为一书,与向来《大学章句》相似。”他又称《大学》“前后相因,互相发明”“首尾具备,易以推寻”,赞《中庸》“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齐整”。其实,这些特征既是朱子对于《学》《庸》文本结构的“前理解”,也是其经典阐释的目标指向与突出特征。
阐释体系所建构的文本结构多随文化语境的变迁而变化。反向来看,对于文本结构的认识也受到特定历史语境的影响。“枝枝相对,叶叶相当”正是经典文本在“无独必有对”这一思想映射下所彰显的结构特征。在宋代哲学思辨思潮的催化下,宋儒赋予了“对”普遍化、本体化的特质。张载言:“天地变化,二端而已。”“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二程将对立统一视为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成为“理”的重要品格。“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他们又将“对”与其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理”紧密结合:“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熹亦充分认可“对”的普遍性,多次援引程子“无独必有对”之说。有学生不解程子为何思及此理会手舞足蹈,朱子叹曰:“真个是未有无对者。看得破时,真个是差异好笑。”又言:“天下事物之理亭当均平,无无对者。惟道为无对,然以形而上下论之,则亦未尝不有对也。……反覆推之,天地之间真无一物兀然孤立者。”“无独必有对”的认识论亦深刻体现在理学思想的概念体系中。叶适言:“古之言道者必以两。”其实这揭示的是宋代学术的时代特征。张岱年就曾将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概括为48对“对偶范畴”。其中“本末”“道器”“理气”“体用”“动静”“形上形下”“理欲”“知行”“格物致知”等范畴,皆为宋代理学家关注的重点。
认识论层面的思想观念对于经典阐释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杨立华就指出,朱子的《太极图说解》有着很强的对称均衡特征。《朱子语类》中还记载有朱熹所撰的《大学图》与《仁说图》,对称形态亦非常突出。朱熹《学》《庸》阐释的特殊之处在于使用就经为注的传统解经模式,既贴合经文字句,又富有自主意识,在经书文本所携带的规定性和有限性中注入理学思想、申发自主思考,将“无独必有对”的理学认识转化落实在经文字句篇章的点滴之处。下面就分别从“对称句式”和“非对称结构”这两种文本结构类型出发,予以详细探讨。
二、对称句式中文本结构的重新分析
经典文献中的对称式表达渊源甚早,即便是先秦时期的非韵文类文献,对称表达亦很常见。针对这类表达的注释则有不同取向:传注类训诂多着眼于疑难字词的训解,训释语言并不会有意呼应被释文句的结构特征;以串讲句意为主的章句体,虽偶有对称式表述,但也不会刻意求“对”;而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中,朱熹则有意识、成规模地运用对称句式进行阐释。这类说解并不单纯是修辞层面的追求,而更有其服务于阐发理学思想、建构经学体系的宏大旨归。
(一)添加一致性概念
具有相对关系的两个主体之间存在对立、对当、内外、主次等多重可能,同时在某一层面存在一致性要素。张载《正蒙·太和》言:“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此中之“一”也就是双方的一致性。陈来指出:“理学讨论的问题是通过概念范畴来表达的。”朱熹的阐说就往往将对称式表达背后的“一”予以挖掘、提炼、加工,且多指向理学思想的核心概念。
“气”是宋儒普遍关注的重要理学范畴,《中庸》的一些经文中虽并无此字,但朱熹将“气”的概念嵌入阐释语言,成为对称表达中的一致性成分,在长句、短句或双音词等大小不同的对称表达中皆有体现。如《中庸》第十章的“子路问强”:“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两句分别描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朱子的阐说从“风气”出发,总结两地之“强”的相对特点:“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君子之道也。”“北方风气刚劲,故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强者之事也。”一南一北,但均是外在“风气”影响下生于形气之私的“胜人为强”,与下文所推崇的“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等“自胜其人欲之私”的自强品质形成鲜明对照。又如《中庸》第十七章:“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这一段表述本未涉及“气”,但在理学视域下,万物之生与“气”密切相关,故朱熹将“栽者培之”与“倾者覆之”的原因归结为“气至”与“气反”:“气至而滋息为培,气反而游散则覆。”由此,表面上相反相对的两个单句,具有了以“气”为中心的一致性特征。经文中有一些同义连用的双音词,本侧重于二者的同义联系,朱熹则在提取一致性要素的基础上又突显二者相反相对的关系。如《中庸》第十六章“鬼神之为德”中的“鬼神”一词,朱熹阐释道:“愚谓以二气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以一气言,则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其实一物而已。”其从一致性成分“气”出发,详细探讨了“鬼”与“神”在“二气”与“一气”框架下的不同关系,深化了文本的理学内涵。
使用对称式说解进行义理阐发并非朱熹独创,但在义理阐释的深度与密度方面,朱子则更为精进。以“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为例,吕大临以疏通文义为主,添加了“植之固/不固”“本”“末”等概念:“植之固者,如雨露之养,则其末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风凌雨,则其本先拔。至于人事,则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张九成则将“本根”一词作为一致性成分:“栽者,本根深固,自取培益;倾者,本根摇荡,自取颠覆。”侯仲良关联“舜”和“桀”,突显文句言外之意:“舜自匹夫而有天下,‘栽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为匹夫,‘倾者覆之’也。”对比诸家的对称式说解即可发现,朱熹更有意识地关联理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虽然表层文本结构并未改变,但文本结构的内在意义实现重新组织,文本字句段落超越了典籍原文结构的框架束缚,紧密集结在核心概念为枢纽的义理体系之中。这正是朱熹的对称式说解胜于前儒之处。
(二)嵌入成对式概念
除关注一致性特征之外,朱熹对于对称表达中的相对关系也有不少深入阐说。这类说解通常不会限于被释文句的自身结构,而是拈出其中成对的关键词语,通过概念的重新阐释来嵌入成对的理学范畴。
宋代理学可谓“明体达用之学”,朱子体系中的“体-用”概念有诸多侧面,兼具整体与部分、内涵与形式、抽象与具象等多层意义,也与理学体系中其他成对概念有着广泛联系。在对称句式的说解中,朱熹充分运用“体-用”作为思维框架,拓展了对称双方深层次的义理内涵。如《中庸》第一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章句》:“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这段阐释朱熹采用短句组合的对称表达,使得文句的义理内涵实现扩容增量。其一,通过界定“大本”与“达道”,确立“道”为“中”与“和”的一致性成分,并将二者纳入“体用”范畴之中。其二,通过“天命之性”及“循性之谓”的对应表述,又将“性”确立为一致性成分:“中”为其本体内核,“和”为其遵循运用,实现与“体-用”关系的隐形照应。对于“中”与“和”的阐发,程颐之说可作参照:“‘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同样使用对称式表达,程子从“寂然不动”与“感而遂通”两方面来突出“中-和”的相对关系,朱子则更清晰地与“体-用”相关联,且挖掘出相对关系之中的一致性成分“道”“性”等。两相对比,朱熹抉发义理透彻利落的阐释品格更为突显,充分体现了朱子“一杖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历历落落,分明开去”的论理之道。
“知-行”关系也是朱熹理学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在《学》《庸》阐释中有诸多对称表述被嵌入“知-行”概念。如《中庸》第四章:“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中提到“知”“愚”“贤”“不肖”四种类型的人,皆存在“过”与“不及”之蔽,但具体指向哪一方面经文则未提及,也给后人阐释留下空间。朱熹之前,吕大临论及此处也提到了“知-行”关系,但与经文的贴合尚不紧密:“知之过,无证而不适用,不及则卑陋不足为,是取不行之道也;行之过,不与众共,不及则无以异于众。”朱熹将四者分别纳入“知-行”框架:“知者知之过,既以道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贤者行之过,既以道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其将“知者”和“愚者”统归为认知层面未达中道,前者为“知之过”,后者为“不及知”;“贤者”和“不肖者”则属于行为层面的过与不及,前者是“行之过”,后者是“不及行”。在具体论述中,认知与行为两个层面又互相影响交织,体现了“道”之体悟、发扬与“知-行”的密切联系。
朱熹对于对称句式的重新分析,巧妙地嵌入单个或成对的理学思想,不同章节的文本之间成对概念彼此关联、互相参照,从不同角度突显了概念的多层意义,阐释文辞更为精练,思想体系架构也愈加精密,较之前辈学者呈现出更强的指向理学核心概念的向心力。对称句式解说中的概念辨析,充当了将经文字句引向理学思想的桥梁。这类概念辨析并不针对被释对象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全面阐说,而是着眼于某个特征,将其与理学思想中成对的概念范畴相关联,极大拓展了经典阐释的意义空间。同时,就经为注的章句模式也给予义理阐释一种有效牵制,避免论说堕入游谈无垠之弊。

福州西湖朱熹像
三、非对称表达中文本结构的重新组构
对于一些表层语言表达并不对称的经文,朱熹同样在“无独必有对”理念的驱使下予以对称化处理。这类说解将被释文本的结构关系予以重新组构,并在此基础上予以重新分析,建构性特征更为显著。这也是《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相较《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以及其他宋儒著述更具特色的一面。下面就分别从单句、句群、章节三类大小不同的语言单位出发予以详细说解。
(一)句内关系的二元切分
《学》《庸》经文中有不少多项平列式或前后顺接式的语言表达。朱子会有意识地将其一分为二、划归两类,从而与一些理学体系中的成对概念相对接。
《大学》首句为此篇之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对于《大学》之三纲,孔疏理解为“此其一也”“此其二也”“此其三也”的平列关系。朱熹则处理为“2+1”式的结构,认为“明明德”与“新民”有着“己-人”“向内-向外”的对应关系:“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而“止于至善”则为表程度的修饰成分:“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受此影响,《大学》八目的内在关联也被朱子重新组织:“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也就是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皆属于“明己明德”,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与“新民”挂钩,使民皆明己之明德之事属于推己及人。如此解释,“顶针续麻”式的《大学》八目就被纳入“明明德”与“新民”的统摄之下,成为贯彻三纲的具体行为。对于八目的主次关系,《大学》经文强调的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朱子据此以“修身”为界将八目一分为二:“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而措之耳。”也就是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皆属于修身的具体方法,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运用举措,此二元切分也含有“体-用”思想的用意。
《中庸》第二十章的“诚之”之目,文本结构亦属于平列关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章句》:“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朱子不仅将其一分为二,且嵌套有“择善-固执”“学知-利行”“知-仁”等成对表达,从多角度指向“知-行”体系的阐说。“学知-利行”源于《中庸》第二十章,本身就由“知-行”关系衍生而出:“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择善-固执”亦来源于《中庸》第二十章:“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章句》:“择善,学知以下之事。固执,利行以下之事也。”此处朱熹的说解又与“学知-利行”相照应。
与二程的“诚之”之目的解说相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朱熹在前人基础上的调适与精进:“知至则当至之,知终则当遂终之,须以知为本。……知至是致知,博学、明辨、审问、慎思四者,皆知至之事,笃行便是终之。”程子同样是将“诚之”之目二分,分别关联“知至”与“终之”,强调彻底的认知是实践层面坚持到底的基础,内在蕴含有“知-行”关系。而朱熹的阐说则更为显豁,直指核心概念,且有意识地关联“择善-固执”“学知-利行”等旁及的诸多概念,形成围绕“知-行”关系的次级概念群。相关说解穿过文本表层的结构秩序,组构成了彼此联系的概念网络,更大程度增强了义理思想的体系化特征。
(二)句群关系的并蒂架构
句群是指单句组成的小型关联组合,其结构单位小于一章。朱熹特重语势、文脉的把握,《学》《庸》阐释中屡见“此结上两节之意”之类的表述(此“节”即为“句”),就是针对章节内部句群关系的思考。朱熹将“无独必有对”理念注入其中,使得句群关系形成“二分—总结”或“总—二分—总”的结构模式,形似一主枝两支脉的并蒂之花。
《大学》首句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其后紧接的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和“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两句。按照孔疏理解,“物有本末”一句紧接“能得”而发,当为“知止-能得”一句的总结:“若于事得宜,而天下万物有本有末,经营百事有始有终。”朱熹则认为“物有本末”一句是对“三纲”及“知止-能得”的总结:“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此结上文两节之意。”将“三纲”对应“本末”,“知止-能得”对应“终始”,使得此句有了“结上文两节之意”的总结性功能。这样一来,《大学》开篇三句就具有了“二分—总结”的结构特征,文本结构更具层次性。
《中庸》还有一些规模更大的句群,朱熹同样予以并蒂式架构,呈现出“总—二分—总”的形态,如第二十七章:
“大哉圣人之道。”《章句》:包下文两节而言。
“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章句》:此言道之极于至大而无外也。
“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章句》:此言道之入于至小而无闲也。
“待其人然后行。”《章句》:总结上两节。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章句》:至德,谓其人。至道,指上两节而言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章句》:“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
此段以“大哉”发端,无论是“洋洋乎”还是“优优大哉”都统言其“大”。而朱熹则为了与“费-隐”关系挂钩,将“洋洋乎”与“优优大哉”分别与“道之大”“道之小”相对应。“优优大哉”一句与“道之小”的关联略显牵强,朱熹就主要从“威仪三千”入手,强调礼为细碎之曲礼。此两句之外,“大哉圣人之道”“待其人然后行”皆被认定为针对中间两小节的总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的说解则拈出“至德”和“至道”两个关键词,分别与前三句对应,属于对以上句群的总结。“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这一长句由数个短句比并而成,孔颖达将此句与以上数句截为两章,朱熹则予以合并,目的是将“小-大”概念沿用,内置到这一长句的义理阐释之中,从“极乎道体之大”“尽乎道体之细”以及“大小相资”等说解中可见此用意。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的论述可参互照应:“大抵此五句,承首章道体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内,皆具小大二意,如德性也、广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问学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礼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尽之、极之、道之、温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于道之大小无所不体,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乱,无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一章之内层次分明、结构井然、脉络贯通,令人叹服。朱熹曾评价《中庸》“义理大小精粗纵横贯穿,无空阙处”,就此章内在脉络的说解来看,其实正是朱熹义理阐释所呈现的突出特色。

《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之前,游酢等宋儒也对此节予以对称式说解:“‘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至道之功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至道之具也。”虽具对称形态,但两者之间的相对关系并不清晰。朱熹就曾对前辈之论表示遗憾:“游氏分别至道、至德为得之,惟‘优优大哉’之说为未善,而以‘无方无体’‘离形去智’为极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为德性广大高明之分,则其失愈远矣。”文本结构形式上实现对称并非难事,但义理阐释中各类概念能够定位清晰、逻辑自洽则更为难得。朱熹对于文本结构的重新组构,不仅胜在形式层面一以贯之,更胜在义理辨析的精熟邃密。
朱熹对于句群之间文本脉络的细致挖掘与建构阐说,是其较之汉代章句及其他宋儒经注更具特色的一面。吴承学等指出,朱子章句是对章句之学与文章之学的综合运用,这一观点敏锐地关注到朱熹在阐释微观文本结构方面的着力功夫。例如,朱子对于句群关系“二分—总结”或“总—二分—总”关系的建构,就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传统典籍语言表达的一些内在规律。启功曾言诗歌、骈文句子排列组合的基本规律,最常见的形式是“单行句—偶句上句+偶句下句—单行句”,且此类结构在先秦散文亦有用例。可见,朱熹对于文本结构的建构性阐释有着暗合行文规律的一面。
(三)章节关系的对称排布
在语言单位更大的章节层面,朱熹同样贯彻了鲜明的“无独必有对”理念。通观《学》《庸》的章节划分与章旨设定,可以看到清晰的对称形态。
《大学》经文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结构特征,先提出三纲八目,后分别对照辅证,只不过文本次序未做到严丝合缝,朱子参考二程观点予以调整,形成《大学》今本。分章层面,朱子首先将“经”“传”二分,“经”的部分也即三纲八目,“传”则设十章,分别与“经”依次照应。在末章的章旨阐述中,朱子又将“传”予以二分:“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传”之前三章分别与“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对应,另有一句朱子设置为第四章:“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其章旨为“释本末”,与“经”中的“物有本末”一句对应。此句亦涉及文本次序的调换,目的是使得经传之间呈现合如符契的对称形态。
《中庸》经文规模更大,朱子共分为三十三章,章句的切分也更为细密。《中庸》分章据朱子之说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十一章围绕首章展开,第十二~二十章围绕“费-隐”展开,第二十一~三十三章围绕“诚”展开。其中第二、第三部分的对称式布局尤为鲜明。在第二部分中,第十二章围绕“君子之道费而隐”展开,可视为总说,此下八章(第十三~二十章)为其申说之辞。第十六章“兼费隐、包小大”,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其前三章(第十三~十五章)为“费之小”,其后三章(第十七~十九章)为“费之大”,皆由朱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可谓费矣”之说派分而来。第二十章同样有“包费隐、兼小大”的总结之言。统观第二部分的章节划分与章旨设定,不仅首尾呼应、中有转承,而且“费之小”“费之大”的相关章节数皆为三章,章节排布的对称特征十分显著。
《中庸》第三部分在分章上也有类似特征。第二十章内容非常丰富,包含“五达德”“三达道”“九经”以及“诚”等关键概念。第二十一章其实与第二十章中的“诚”联系十分紧密:“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章旨中的“天道-人道”之分,照应的是第二十章中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一语。此一句独设一章,有着开启下文之用。其后数章皆“天道”与“人道”互相交替。第二十七章为小型枢纽,统领第二十八、二十九章的章旨,皆言“人道”。与此相对,第三十~三十二章言天道,章旨表述亦与“人道”呈现相对称形态。最后第三十三章总结全文。值得注意的是,朱子的分章中不乏以单句为一章的处理,这种划分显然是为章旨结构的对称形态服务。
上述单句、句群、章节文本结构的重构阐释虽然具体观点指向各异,但内在理路则高度一致——“无独必有对”为一以贯之的核心追求。求对的阐释理念虽然并非朱熹独有,但其在义理的完备自洽及方法的纵横贯彻方面则更具代表性与典型性。阐释方法论层面的“理”与思想体系中的“理”高度一致、互相呼应,又能彼此促进、相得益彰:理学思想体系中的成熟思考促使阐释方法的运用更为彻底,阐释方法的系统贯彻协助理学思辨更为透辟。这也是其修身功夫与注经方法内外贯通的具体表现。

中山大学校训
余论
“无独必有对”的阐释理念在《学》《庸》中体现得尤为显著,也在一定程度上旁及《论》《孟》,成为朱子进行跨文本阐释、构建四书义理系统的重要方法。依托对称句式进行文本结构重新分析的做法,在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亦有运用,如《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集注》:“礼贵得中,奢易则过于文,俭戚泽不及而质,而者皆未合礼。”这段阐释重新组合“奢”“俭”“易”“戚”的文本结构,将之纳入“文-质”和“过-不及”这两对概念框架之中,与中庸思想相关联。虽未改易表层文本结构,但理学向度的经义内涵得到了充分阐述。而文本结构重新组构的做法则在《论》《孟》阐释中较少体现,这也与二者作为语录体较为短小、各自独立的文本体式相关。
《学》《庸》阐释的诸多“对称化”说解具有建构性阐释的特点,但这种建构性阐释与中国古典阐释传统中的“阐释确定性”并不矛盾。阐释的确定性是一种关系网络中的确定。在多维度、多层次的关系网络中实现通达、融贯,正是“阐释确定性”的一种体现。从朱熹“无独必有对”理念所引导下的诸多阐释实践来看,其既符合理学思想的宏观文化语境,也符合语言文字的微观规律,即便是对文本结构予以重组的例证,也是在文本语境有限的内在张力范围内予以调适。这也正是朱熹理学阐释能够从个体阐释上升为公共阐释,为人所接受认同,甚至在学术史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内在原因。朱熹从四书文本中提取出了这些核心理念,又将这些理念散布、渗透到其他文本的义理阐释以及文本结构的重解与重组之中,形成一种类似“回响共振”的阐释效果,在多重文本网络的合力作用下,实现了通贯浃洽的体系建构,极大地深化了这些核心概念的理论深度,也完成了《学》《庸》的理学化重塑及其在经学体系中的“升格”。
朱熹经典阐释内在机制层面的“理”与其思想体系中的“理”高度一致、彼此呼应,“无独必有对”式的普遍性认识,使得“对称关联”成为朱熹的思想钢印,渗透到经典阐释字句篇章的点滴之处,成为指引经典阐释的方法论。朱子不仅对于《学》《庸》之中的对称式文本有诸多对称式阐说,使得经书文本与理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紧密关联,大大增强了两部典籍的理学化特质。对于单句之内、句群之间、章节划分等非对称表达,朱子亦从对称化的视角予以重组建构,呈现出二元切分、总分架构、对称布局等不同形态,促使《学》《庸》文本实现高度的系统化和结构化。传统章句就经为注的方式不仅没有限制朱熹的理学思考,其离章别句、敷衍发明的功能反而成为经义生成的重要路径,充分展现了经典阐释的巨大张力,以及承载不同义理思想的巨大潜力。
本文发表于《东南学术》2024年第1期,
转载自公众号“东南学术”。
作者简介

白如,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董京尘 谢琰
责任编辑:高洁
我知道你 在看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