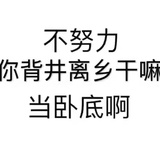论《文始》“初文”的价值与局限
文丨陈晓强
摘要:《文始》以《说文解字》中的独体字为“初文”、以省变独体字或介于独体与合体之间的字为“准初文”。字不同于词,《文始》以“初文”为出发点系联汉语词族存在很多问题。另一方面,《文始》“初文”兼有字根和语根双重功能,汉字字根和汉语语根关系密切,《文始》以“初文”为基点、以“字根”通“语根”、以“语根”统词族的方法又有其合理性。
关键词:文始 初文 字根 语根
对汉语词族进行全面系联,始自章太炎《文始》。章太炎先生利用汉语和汉字的密切关系,巧妙地设计出以“字根”通“语根”,以“语根”统词族的方法。《文始》对术语“初文” [1]的运用,基本原理即以“字根”通“语根”。字不等于词,语根与字根本质不同,《文始》以“初文”为出发点系联汉语词族的方法,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如王力先生认为《文始》“初文”犯了章太炎先生自己所定的不要“拘牵形体”的原则。[2]然而,《文始》以“初文”为根系联大量词族的成功案例,又值得我们深思《文始》“初文”的合理性。
一、《文始》对“初文”界定存在的问题
《文始·叙例》:
《叙》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以讫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然则独体者,仓颉之文;合体者,后王之字。古文、大篆虽残缺,仓颉初文固悉在许氏书也。……于是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省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复重者,谓之“准初文”;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五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雠,谓之“变易”(即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者);义自音衍,谓之“孳乳”。坒而次之,得五六千名。
(一)初文
章太炎先生以《说文解字·叙》所论为基础,从《说文解字》(后文简称《说文》)中提取独体字,名之为“初文”。《文始》设置“初文”的学术史意义及从《说文》中提取“初文”的问题,后文将详论,此处仅通过原始文字与表词文字的不同谈《文始》对“初文”界定存在的问题。
1.“初文”不是原始文字
传说中,仓颉是汉字的创造者。《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文始·叙例》:“独体者,仓颉之文。”“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章太炎先生认为“初文”始于仓颉,反映汉字起源阶段的状态。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值得深入研究。汉字起源于什么时代?目前难有定论。尽管文献中有“仓颉造字”的记载,可远古黄帝时期的传说太过模糊,而现实的考古又很难看到五、六千年前有汉字的踪迹。再说,历史上是否有“仓颉”其人,“仓颉”是一个人还是一批人,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当然,如果不把“仓颉”局限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时代,则“仓颉之文”可宽泛地理解为起源阶段的汉字。那么,起源阶段的原始汉字,是否为独体之文,又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从文字产生、发展的共性规律看,古老的原始文字大多由图画演变而来。俄国学者B.A.伊斯特林认为:原始图画文字曾经是句意文字,字形上不是一个个单独的孤立的图形,而是叙事性的组合图画,不可分解为单个的词。[3]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器物上,发现了一些性质接近句意文字或语篇文字的图画,例如,河南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缸上,画着一个白鹳口衔一鱼,旁边画一把石斧(见图1)。

图1
对图1的解释,或认为:石斧是氏族图腾,鹳衔着大鱼,虔诚地面对石斧,意味着向石斧奉献供品,该图是原始氏族图腾崇拜礼仪场面的一个特写镜头。[4]或认为:石斧表示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征伐,鹳与鱼表示两个不同的部落;意即鹳部落通过斧头(武力战争)征服了鱼部落。[5]两种解释都在具象的鹳鱼石斧图中看到了抽象的语篇意义,这种具有抽象意义的图画,已有一定的文字性质,有些学者称之为“文字画”。[6]周有光先生认为:“文字画一般都是单幅的,它们的特点是:符号是图形,语段是篇章。”[7]如把类似于上图的合体“文字画”视为原始语篇文字,则独体字形的产生不见得先于合体字形。“独体者,仓颉之文”,可能与事实不符。因此,不应从原始文字角度理解或界定“初文”。
2.“初文”反映表词文字初级阶段的状态
很多学者认为,萌芽阶段的汉字与成熟时期的汉字有很大区别。文字要精确记录语言,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成熟过程;在成熟的表词文字产生之前,古汉字应该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从这个角度看,沈兼士、周有光等先生所论“文字画”现象,可能符合汉字萌芽阶段的实际。因此,对“初文”的性质及“文”与“字”关系的讨论,应注意到原始图画文字与成熟表词文字的不同。
原始图画文字在与语言逐渐结合的过程中,出于精确记录语言的需要,组合物象图画中的单一物象可能会逐渐从图画中离析出来而成为表词文字。例如,离析鹳鱼石斧图,可得出鹳、鱼、钺三个图案,这三个图案似乎和古汉字“ (雚)”“
(雚)”“ (鱼)”“
(鱼)”“ (戊)”有一定的形体关联。金文族徽中有原始图画文字的遗存,根据金文族徽,鹳鱼石斧图中的鹳和鱼很可能表示不同部落,例如,商代铜器铭文“鱼父乙”(见图2)、“雚母”(见图3)中的“鱼”“雚”即为族徽。[8]金文族徽的相关信息,为鹳鱼石斧图中的“鹳”“鱼”与古汉字“”“”的关联提供了一定线索。当然,笔者并不就此认为古汉字“雚”“鱼”与鹳鱼石斧图有必然联系,本文以鹳鱼石斧图为例,只是为了说明原始文字与表词文字的关联及不同。当原始汉字逐渐演变为表词文字后,独体之“文”便成为最早的一批能独立记词的文字。此后,随着独体之“文”与语言之“词”地不断互动,在“文”的基础上便孳生出大量“字”。“独体者,仓颉之文;合体者,后王之字。”章太炎先生根据《说文解字·叙》,认为“文”产生于仓颉时代,可能与事实不符;但认为“文”早于“字”,“字”在“文”的基础上孳乳派生而出,是符合表词阶段汉字发展实际的。
(戊)”有一定的形体关联。金文族徽中有原始图画文字的遗存,根据金文族徽,鹳鱼石斧图中的鹳和鱼很可能表示不同部落,例如,商代铜器铭文“鱼父乙”(见图2)、“雚母”(见图3)中的“鱼”“雚”即为族徽。[8]金文族徽的相关信息,为鹳鱼石斧图中的“鹳”“鱼”与古汉字“”“”的关联提供了一定线索。当然,笔者并不就此认为古汉字“雚”“鱼”与鹳鱼石斧图有必然联系,本文以鹳鱼石斧图为例,只是为了说明原始文字与表词文字的关联及不同。当原始汉字逐渐演变为表词文字后,独体之“文”便成为最早的一批能独立记词的文字。此后,随着独体之“文”与语言之“词”地不断互动,在“文”的基础上便孳生出大量“字”。“独体者,仓颉之文;合体者,后王之字。”章太炎先生根据《说文解字·叙》,认为“文”产生于仓颉时代,可能与事实不符;但认为“文”早于“字”,“字”在“文”的基础上孳乳派生而出,是符合表词阶段汉字发展实际的。

图2

图3
(二)准初文
由“文”到“字”,是表词阶段汉字发展的总规律。那么,“文”与“字”之间,是否存在过渡现象?《文始·叙例》:“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省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复重者,谓之‘准初文’。”《文始》所谓“准初文”,即是介于“文”与“字”之间的过渡现象。就此,黄侃先生有详论。黄侃《说文略说·论文字制造之先后》指出:汉字由“文”向“字”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半字”的情况,包括合体象形、合体指事、省变、兼声、复重等。[9]章太炎、黄侃先生所论“准初文”或“半字”,基本上涵盖了汉字的独体与合体之间有可能出现的各种现象:①特殊象形(独体象形的省或变、合体象形);②特殊指事(合体);③特殊会意(同体重复);④特殊形声(声具而形残)。从整体看,《文始》对“准初文”的设计和运用是合理的:只有合体和独体的概念,不足以说明汉字发展演变中纷繁复杂的现象;而且,“准初文”与“初文”的性质接近,往往兼有字根与语根的双重功能,这对上古汉语词族的系联有重要意义。
二、《文始》设计和使用“初文”的合理性
在汉字萌芽时期,汉语中的词汇已经有漫长的发展演变历史。“初文”“准初文”只是表词阶段汉字字形的源头,《文始》以“文”为根系联上古汉语词族,在理论上存在缺陷。但是,要追寻原始汉语的蛛丝马迹,很难找到比三千多年前的汉字更有效的线索。这就好比对汉语词语本义的探求,理论上应追寻到词语最早出现时的意义,但现实中却只能从记录该词最早的字形中探寻词语的本义。《文始》以“初文”“准初文”为出发点系联汉语词族,尽管影响了理论的纯洁性,但在方法上实现了现实的可行性。
《文始》以“文”为起点,利用由“文”到“字”的字形孳乳线索系联汉语词族,在理论上存在字、词混淆的问题。要理解这一问题的深层合理性,需要对语言与文字的一般关系及汉语与汉字的特殊关系有深入认识。《文始·叙例》:“文字者,词言之符。”字、词混淆是困扰传统训诂学的难题,章太炎先生受西学影响,对字、词关系有了科学地认识。“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10]因此,章太炎先生反对汉语、汉字研究“偏理《说文》,拘牵形体”,主张“依隐声义”。(详《文始·叙例》)另一方面,章太炎先生对汉语与汉字的特殊关系有深刻认识,他高度重视汉字由“文”到“字”的字形孳乳线索在汉语词源研究中的价值。[11]有了“文”的基础,经“变易”“孳乳”不同途径,便产生大量“字”;而“文字”是“词言之符”,梳理出字的繁衍系统,则词的演变之迹、词族系统都可从中考察。这就构成了《文始》由字到词,由字源到词族的研究思路,即《文始·叙例》所谓由“五百十字”得“五六千名”。
黄侃《略论推求语根之法》:“治《说文》欲推其语根,宜于文字、说解及其所以说解三者细加推阐。凡文字解之至无可解,乃字形之根。纯象形、指事字是所谓文。一面为文字之根,一面又为声音之根、训诂之根;形声义三者实合而为一,不可分离,故文为形、声、义之根。”[12]黄侃先生的汉语词源学思想,深受章太炎先生影响。从黄侃先生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文始》“初文”在形式上是字根(即“字形之根”),在实质上却起到语根的作用(即“声音之根”“训诂之根”);统而言之,“初文”为“形、声、义之根”。章太炎先生以“初文”为词族的起点,实质上是以“初文”为语根。字根能否起到语根的作用?如能,字根如何起到语根的作用?要论证《文始》设计和使用“初文”的合理性,这些问题是必须要回答的。
语言在不断发展,表义含混的旧词需要分化,新词也在不断产生。独体的象形之文,显然无法满足全面记录语言的需求;指事、会意字的出现,也难以彻底解决问题。因此,在汉语词汇不断孳生的过程中,形声造字逐渐成为汉字形体繁衍的主流。于是,曾经的独体之文很多随着汉字构形方式的演进而具有了新的身份和功能,即成为具有示源功能的形声字声符。由此,以形声字声符为字根,一个个蔚为壮观的汉字字族开始形成。例如,以“今”为字根而孳乳出的一大批形声字具有蕴含、闭藏意象:“含”为口中含物、“䶃”为含物之鼠、“侌”为云中含日、“念”为心中含人、“贪”为心中含财、“肣”为口中含舌、“妗、欦”为闭口之笑、“吟”为低沉之吟、“ ”为噤不成声、“棽”为枝条覆地、“䰼”为腌制之鱼、“紟、靲”为束系之带。[13]“今”的形体是这组字的字根,“今”的音义是这组字所记录词的语根。字根起到了语根的作用,由此即可看出《文始》以“文”为“根”(字根、语根),由“根”到“族”(词族)的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
”为噤不成声、“棽”为枝条覆地、“䰼”为腌制之鱼、“紟、靲”为束系之带。[13]“今”的形体是这组字的字根,“今”的音义是这组字所记录词的语根。字根起到了语根的作用,由此即可看出《文始》以“文”为“根”(字根、语根),由“根”到“族”(词族)的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
文字与语言毕竟不同,与“今”语音相近且具有蕴含、闭藏意象的形声字声符有很多,如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讨论“复式音符分化式”所举“今、甘、兼、甲、音、猒、奄、弇、咸、、臽、合”十二个声符所孳乳之字多有蕴含、闭藏意象,“其韵皆属侵覃部收m之音”,声纽“见匣两纽交流,见纽又入于影”。[14]如果拘泥于“初文”的字形线索,势必无法对词族进行全面系联。《文始·叙例》明确指出:汉语词族的研究不能“拘牵形体”,而要“依隐声义”。在具体词族的系联中,《文始》一方面重视对形声字声符线索的利用,另一方面又能摆脱字形束缚,将同声符的形声字系联在不同“初文”下,如“含”“䶃”“肣”在《文始》“圅”族[15]、“贪”在《文始》“㐁”族。“含”与“嘾”音义相近,《文始》“圅”族:“含又变易作嘾,含深也。”但“覃”“醰”却在“甘”族:“(甘)旁转侵变易为覃,长味也。为醰,甛长味也。”[16]同声符的形声字,系联在不同“初文”下,反映了章太炎先生对语根与“初文”关系的洞见卓识:一个语根,或对应一个“初文”,或对应一组“初文”。一个语根与一组“初文”对应,则出现《文始》中同声符形声字在不同“初文”下交叉互通的现象。就“今”声、“覃”声、“兼”声等形声字出现在不同“初文”下的现象,《文始》指出:“圅虽象形兼声,其义实因,声义又与㐁通。初文或但作,作㐁。圅者,准初文也。”[17]“凡圅、㐁、甘三文所孳乳者率皆可转。”[18]《文始》关联一组音义互通的“初文”,说明章太炎先生所设计的“初文”,不仅要承担字根的任务,更要承担语根的任务。《文始》以“初文”为词族系联的起点,反映章太炎先生对汉字字形线索的重视;但《文始》在具体词族的系联中,又不拘泥于字形线索。重视汉字形体线索,又能摆脱汉字形体的束缚,反映了章太炎先生对汉语与汉字辩证关系的深入思考,这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始》对“初文”的合理使用。
《文始》经常以“初文”的字形造意为出发点探求语根的词源意义及派生分化,这在理论上存在明显错误。令人奇怪的是,即便《文始》对“初文”字形分析有误的情况下,《文始》以“初文”为根所系联的词族却大多是合理的。错误的出发点,却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例如《文始》初文“”下以《说文》训释“壬,象物出地挺生也”为据,认为“挺生”为“壬”的本义,其字形“上象其题,下象土,声义与端、屮皆相近”,所以,“(壬)变易为莛,茎也。又为茎,枝柱也。”又,“挺生则直,故诸壬声字义多近直。”《文始》又以形声字声符“、廷、巠”为线索,在直义下系联“廷、梃、筳、珽、庭、颋、侹、呈、桯、桱、胫、颈、经、径、娙、劲”等词。由此,形成一个以“壬”为语根,词源意义为直的词族。[19]从“初文”字形看,“”甲骨文作“ ”“
”“ ”等,象人挺立地上之形。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徐铉曰:‘人在土上,然而立也。’……舜徽按:即挺之初文。……象人挺立地上形。盖造字之初,人挺立地上与物挺生出地,本为二字,音同而形有异。及变为篆体,乃以形近混而为一。”[20]《文始》对“”的字形造意尽管理解有误,但以“”为出发点系联起来的词族却是正确的。由此可见,“初文”的形式表现为字根,但其承载的却是语根。所以,即便对“初文”形义理解不正确,但“初文”内在的语根属性也能保证系联结果的相对正确。这进一步说明《文始》以“初文”为出发点系联汉语词族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其实质是由“初文”兼有字根和语根的双重功能决定,由此也反映出汉语语根与汉字字根的密切关系。
”等,象人挺立地上之形。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徐铉曰:‘人在土上,然而立也。’……舜徽按:即挺之初文。……象人挺立地上形。盖造字之初,人挺立地上与物挺生出地,本为二字,音同而形有异。及变为篆体,乃以形近混而为一。”[20]《文始》对“”的字形造意尽管理解有误,但以“”为出发点系联起来的词族却是正确的。由此可见,“初文”的形式表现为字根,但其承载的却是语根。所以,即便对“初文”形义理解不正确,但“初文”内在的语根属性也能保证系联结果的相对正确。这进一步说明《文始》以“初文”为出发点系联汉语词族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其实质是由“初文”兼有字根和语根的双重功能决定,由此也反映出汉语语根与汉字字根的密切关系。
在明确《文始》“初文”所存在问题的前提下,如果能对《文始》“初文”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可从中提取出很多合理的汉语词源研究法:①从平面系源的观点看,系源的起点仅是处理材料的一个操作依据,它相当于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坐标点,而不是标志着历史起源的根词。汉语词汇的派生与汉字的孳乳相伴而行,章太炎先生所定的“初文”的产生先于会意、形声,在根词难以确定的前提下,以“初文”为系联的起点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办法。[21] ②“初文”为上古汉语词族的系联提供了比较合理的形的出发点。如果能进一步摆脱字形的束缚,便可发现“初文”更重要的价值是为汉语词源全面、系统的系联提供了音的基本点。汉字不是表音文字,但词源的全面研究却需要有一批基本音节作为系联的基础。如何在表意的汉字中挑选出一批数量不大但又覆盖面很高的基础音节,“初文”自然成了最佳的选择。[22]③由于受共同的认知规律和文化心理的支配,部分“初文”的造字取象有可能与词语的造词理据暗合,因此对“初文”构形理据的分析,有利于在起点上揭示一个词族的源义。相对词汇意义而言,词源意义的重要特征在于稳定性,因此,通过对“初文”构形分析所得到的在词族起点上的词源意义,经常对整个词族词源意义的探求起很大的提示作用。
三、《文始》使用“初文”存在的问题
文字不同于词语,形源不同于词源。《文始》以“初文”为根探求语源,在理论上存在字词混淆的问题。上文已指出《文始》“初文”这方面的问题,此处不再赘述。本部分主要讨论《文始》使用“初文”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一)对“初文”“准初文”的错误判断
汉字演变发展至小篆,很多字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说文》收字以小篆为主,而《文始》判断“初文”“准初文”的依据是《说文》,这就导致《文始》对一些“初文”“准初文”的错误判断。相对而言,“初文”是独体字,容易判断;而“准初文”已具有合体字的性质,《文始》对“准初文”的判断则有很多错误。例如《文始·叙例》:“声具而形残,如氏从乀声,禸从九声,乀、九已自成文, 、
、 犹无其字。此类甚少,盖初有形声时所作,与后来形声皆成字者殊科。”按,“氏”甲金文作“
犹无其字。此类甚少,盖初有形声时所作,与后来形声皆成字者殊科。”按,“氏”甲金文作“ ”“
”“ ”“
”“ ”,构意不明,《说文》从小篆“
”,构意不明,《说文》从小篆“ ”中解析出“乀”声,析形有误。《说文》设“
”中解析出“乀”声,析形有误。《说文》设“ ”部,统摄“禽”“万(萬)”“禹”等字,“禽”“萬”“禹”甲金文作“
”部,统摄“禽”“万(萬)”“禹”等字,“禽”“萬”“禹”甲金文作“ ”“
”“ ” “
” “ ”,可见,所谓的“”部只是“”“” “”等字在发展演变中经字形类化而形成的同形构件。文献中不见“禸”单独使用的情况,也说明“禸”只是以构件形式存在。《说文》从不成字的“禸”中解析出“九”声,析形有误;《文始》根据《说文》,以“禸”为“准初文”,自然是错上加错。
”,可见,所谓的“”部只是“”“” “”等字在发展演变中经字形类化而形成的同形构件。文献中不见“禸”单独使用的情况,也说明“禸”只是以构件形式存在。《说文》从不成字的“禸”中解析出“九”声,析形有误;《文始》根据《说文》,以“禸”为“准初文”,自然是错上加错。
(二)拘泥于“初文”的字形造意
部分“初文”的字形造意,可以为语根意象的探求提供一定线索。但是,“初文”的字形造意与词语的语根意象并无必然联系。《文始》根据“初文”的字形造意来探求词语的语根意象,其结论有很多错误。例如:
说文》:“匕,相与比叙也。从反人。”“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古文作 。”案,“匕”“比”当为一字。反人而为比叙者,“人”象臂胫,度寻以臂,度步以胫,皆以身为法。“鸟”足似“匕”,“鹿”“能”“㲋”足似“比”,“虎”足似“人”,“兕”足似“儿”,皆谓臂及胫也。然则人有二臂二胫,但作一臂一胫者,侧视之形,“匕”亦如“人”,全则为“比”矣。由匕旁转支则为臂,手上也。由匕次对转真则为髌(犹比之为濒),膝端也。旁转支则为髀,股也。《周髀算经》曰:“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周髀长八尺。”[23]
。”案,“匕”“比”当为一字。反人而为比叙者,“人”象臂胫,度寻以臂,度步以胫,皆以身为法。“鸟”足似“匕”,“鹿”“能”“㲋”足似“比”,“虎”足似“人”,“兕”足似“儿”,皆谓臂及胫也。然则人有二臂二胫,但作一臂一胫者,侧视之形,“匕”亦如“人”,全则为“比”矣。由匕旁转支则为臂,手上也。由匕次对转真则为髌(犹比之为濒),膝端也。旁转支则为髀,股也。《周髀算经》曰:“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周髀长八尺。”[23]
“匕”之字形造意是否“从反人”,学界有不同看法。《文始》认为“匕、比当为一字”,又将“匕、比”“人”的字形与“鸟、鹿、能、㲋、虎、兕”等字形中的足部形象对应,认为“匕”的字形造意和“人”相同,取象于人之臂、胫。姑且不论以上字形系联思路的牵强迂曲,《文始》在论证“匕”字形取象于人的臂、胫之后,又根据“匕”字形中的臂、胫,认为“匕”孳乳出“臂、髌、髀”等词。这种根据字形局部形象来考察词语孳乳派生的思路,实在是太过牵强,其结论自然是错误的。
《文始》对“初文”字形的分析和利用,主要依托于《说文》。《说文》小篆字形与甲金文字形相较,有些已发生很大变化。《文始》根据后起的小篆字形,探寻远古的语根意象并系联同源词,导致很多研究结论的错误。例如:
《说文》:“丙,万物成炳炳然。从一入冂。丙承乙,象人肩。”案,“㔷”字说解曰:“侧逃也。从匸丙。”然则“丙”有侧义。“丙”象人肩,《大一经》说独为合义,此纯象形字。对转鱼变易为髆,肩甲也。《说文》“牛”字说解曰:“象角头三、封尾之形。”“封”亦“丙”之声转,今俗犹云肩䋽矣。阳部有“膀”字,胁也;《士丧礼》作“胉”,虽与肩髆异物,亦以在侧,声义相转。《山海经》东望恒山“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搏”即“髆”字。“丙”有侧义,亦可见矣。孳乳为彷,附行也。为傍,附也。与方属之“迫”相转,即今旁侧字。又孳乳为房,室在旁也。为防,堤也。对转鱼孳乳为浦,水濒也。[24]
《文始》以“丙”之字形“象人肩”进行同源词系联,与上条以“匕”之字形象人之臂胫进行同源词系联的思路接近。甲金文中“丙”作“ ”“
”“ ”等形,丝毫不象人肩,《说文》释“丙”字形“象人肩”,有误。“丙”字在甲骨卜辞中就已被假借作天干第三位之名,其字形造意很难明确。即便“丙”之字形取象人肩,《文始》根据字形造意认为“丙”有肩义,混淆了字形造意与词汇意义。接下来,《文始》又以“丙”之肩义为语根意义,系联“髆”“封”“膀”等词,混淆了词汇意义与词源意义。
”等形,丝毫不象人肩,《说文》释“丙”字形“象人肩”,有误。“丙”字在甲骨卜辞中就已被假借作天干第三位之名,其字形造意很难明确。即便“丙”之字形取象人肩,《文始》根据字形造意认为“丙”有肩义,混淆了字形造意与词汇意义。接下来,《文始》又以“丙”之肩义为语根意义,系联“髆”“封”“膀”等词,混淆了词汇意义与词源意义。
(三)将语根局限于“初文”
汉字字根与汉语语根既有密切关系,又有本质不同。沈兼士先生基本同意《文始》以“文”为根系联汉语词族的方法,但沈兼士先生也明确意识到《文始》“初文”是“是字原而非语根”[]的问题。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语语根既会在独体之“文”中有反映,也会在合体之“字”中有反映。如果简单地将字根(即“文”)与语根对应,则“字”的语根功能在汉语词源研究中容易被遗漏或忽视。就此,张舜徽先生指出:“如必考求语根,自不可局限于象形、指事独体之文。即会意合体之字,音读与形体俱来,无假于外,与形声字之从某某声者,截然不同。故欲推寻声始,则会意字之音与象形、指事之音,宜可并重,不应弃此取彼也。”[26]“故今日推求语原,必博征会意之字(合体)与象形、指事之文(独体),综合治之,庶乎取径较广,所得为多也。”[27]张舜徽先生的观点,不是将字根与语根简单对应,而是从声音角度沟通语根与汉字的关系,这是对《文始》“初文”以字根代语根问题的纠正。如果从声音角度沟通语根与汉字,则一个语根很可能表现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多个字形中,故张舜徽先生指出:“探求语原,首必从人情物理乃至方言俚语及谣谚习俗中取得依据,由一声而推衍至数字或数十字,而皆可贯通其义。始得立一为端,以确定其孰为语根,孰为由此而孳乳之字群以论定之,固不必繁征博引经传群书而后可以取证也。”[28]
语言与文字不同,张舜徽先生从多个汉字中探寻语根的方法,无疑比《文始》简单地将字根与语根对应的方法科学。但是,如果不利用字根线索,那么在多个汉字中如何确定语根?如何利用汉字形体的孳乳线索以研究汉语语根的派生分化?以张舜徽先生的方法来研究汉语词族、系联汉语同源词,又会遇到很多困难。由此也可看出,《文始》“初文”尽管在理论上存在缺陷,但在方法上有合理性。这提醒我们在利用字根线索探求汉语语根及系联汉语词族时,既要充分利用方法合理的一面,又要注意避开这种方法不合理的一面。
(四)忽视汉字形声孳乳线索,
混淆词汇意义与词源意义
章太炎先生在重视汉字字形线索的同时,也注意到语言与文字的不同,强调汉语词族研究要“依隐声义”而不应“拘牵形体”。(《文始·叙例》)既要利用汉字形体,又不能“拘牵形体”,这在理论上容易说清楚,但在实践中却会遇到很多困难。《文始》经常将同声符形声字置于不同“初文”下,这反映了章太炎先生进行同源词系联“依隐声义”的思想,也反映了语根与字根的复杂对应关系,其中合理性上文已有讨论。另一方面,《文始》忽视形声字声符线索的做法,也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例如沈兼士先生认为:“今《文始》全书取本声者,才及十一,将谓二十三部之通转,胜于声母与形声字自然分化之为可信耶?”[29]
形声字占汉字的绝大多数,由汉语词汇孳生与汉字形声孳乳相伴而行的事实决定,先秦产生的很多形声字的声符具有示源功能。《文始》摆脱形声字声符的束缚,经常根据形声字所记录词义的不同,将同声符形声字置于语根相通的不同“初文”下,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例如,《文始》以词义为据,将“嘾”归“圅”族,将“覃”“醰”归“甘”族。“覃”声字多有深厚、蕴含、闭藏意象,如王力《同源字典》认为“深、覃、潭”同源。[30]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瞫”下:“㫗部:‘覃,长味也。’长与深义近,故覃声之字多有深义。深视谓之瞫,犹之含深谓之嘾,水深谓之潭,酒味长谓之醰耳。”[31]很明显,张舜徽先生根据形声字声符线索所得出的结论优于《文始》将“嘾”与“覃”“醰”分置两族的观点。词族的系联,应以词源意义为纽带,《文始》根据形声字所记录词义的关联,如“嘾”之“含深”义与“含”关联、“覃”“醰”之“长味”义与“甘”关联,将本来应属于同一字根、语根下的形声字分置于不同“初文”下,这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是存在问题的。
四、《文始》“初文”的学术史意义
(一)以“文”为根,
将语根、词族、历时观念引入汉语词源学
语言的产生远远早于文字,而且汉字的表意性容易遮掩语音交替的规律,因此,当不同时代产生的字、词累积到同一平面之后,很难判断这些字、词产生的历时层次。例如,对《说文》中以“句”为声的“笱、钩、 、斪、跔、
、斪、跔、 、軥、朐、䅓、枸、痀、佝、耇、姁、驹、狗、鼩、蚼、䵶、苟”等字进行系联后,很容易发现“句”声所蕴含的词源意义有弯曲的意象[32]。以上“句”声字及其所记录的词,不在同一个时期产生,这就决定了我们无法用共时的方法观察以上形声字及其所记录的词;同时,以上不同时代产生的“句”声字累积到《说文》这样一个平台上之后,我们很难判断这些“句”声字产生的历时先后顺序,更难判断这些“句”声字所记录词产生的历时先后顺序,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很难用历时的方法观察以上形声字及其记录的词。面对现实,汉语词源研究打破了共时与历时的严格界限,走出了一条适应自身特色的泛时研究道路。泛时的汉语词源研究法,强调从同源词的平面系联中归纳词源理据,而不强调同源词之间的历时演变层次。清代学者以“音近义通”为基础理论系联大量同源词,这种系联大多是平面的、泛时的。
、軥、朐、䅓、枸、痀、佝、耇、姁、驹、狗、鼩、蚼、䵶、苟”等字进行系联后,很容易发现“句”声所蕴含的词源意义有弯曲的意象[32]。以上“句”声字及其所记录的词,不在同一个时期产生,这就决定了我们无法用共时的方法观察以上形声字及其所记录的词;同时,以上不同时代产生的“句”声字累积到《说文》这样一个平台上之后,我们很难判断这些“句”声字产生的历时先后顺序,更难判断这些“句”声字所记录词产生的历时先后顺序,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很难用历时的方法观察以上形声字及其记录的词。面对现实,汉语词源研究打破了共时与历时的严格界限,走出了一条适应自身特色的泛时研究道路。泛时的汉语词源研究法,强调从同源词的平面系联中归纳词源理据,而不强调同源词之间的历时演变层次。清代学者以“音近义通”为基础理论系联大量同源词,这种系联大多是平面的、泛时的。
词源是一个历时现象,只有泛时系源而无历时推源的词源学是不健全的。进行历时推源,就需要有“语根”观念。清代学者尚未提出“语根”概念,与之相关的词族系联零星而不成系统。章太炎先生则有了明确的“语根”观念,他认为“诸语言皆有根”。[33]语言的产生远远早于文字,如果不依托文字线索,“语根”只能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抽象概念。《文始》以“初文”为起点,以“字根”通“语根”,通过“变易”“孳乳”两大条例系联汉语词族,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将历时观念引入汉语词源学,这在汉语词源学史上有重大意义。就此,沈兼士先生评价:“自来训诂家鲜注意及语根者,章氏首先标举语根以为研究之出发点,由此而得中国语言分化之形式,可谓独具只眼。”[34]陆宗达、王宁先生指出:“章太炎初创的《文始》,是一部把《说文》学由平面形义关系的研究发展为纵向历史研究的首始工作,由此而奠定了汉语字源学[35]的基础。”[36]
(二)以“文”寻“根”,
高度彰显了“文”在汉语词源研究中的价值
《文始》之前,汉语词源研究中关乎汉字形体的学说主要是“右文说”。《文始》“初文”的设计和运用,开启了对独体之“文”的系统利用。形声字占汉字的绝大多数,利用形声字声符进行汉语词源研究无疑抓住了汉字形体线索的关键。然而,在汉字发生与发展的初期,占汉字数量绝大多数的并不是形声字,而是图像性的形意字[37]。词源研究关注的是词语发生时的理据,其对汉字的利用当然是字形越早越好。部分形意字的造字取象对探求词源理据有一定帮助,例如甲骨文“麋”字作 或
或 ,其头部作
,其头部作 或
或 ,和眉目之“眉”同形。《急就篇》:“狸兔飞鼯狼麋麆。”颜师古注:“麋似鹿而大,冬至则角解。目上有眉,因以为名也。”《荀子·非相》:“伊尹之状,面无须麋。”杨倞注:“麋,与眉同。”综合字形线索和文献证据,可知“麋”之名源为“眉”。由此可以看出:汉字早期阶段形意字的造字取象对探求上古汉语词源理据有帮助,汉语词源研究对汉字形体线索的利用,不应局限于“右文说”。上古汉语词汇派生与汉字形声孳乳相伴而行,很多形声字的声符具有揭示词源的功能,而形声字声符的形式主要是以独体之“文”为基础的形意字,因此,“右文说”的深入发展,也需要加强对形意字的研究和利用。
,和眉目之“眉”同形。《急就篇》:“狸兔飞鼯狼麋麆。”颜师古注:“麋似鹿而大,冬至则角解。目上有眉,因以为名也。”《荀子·非相》:“伊尹之状,面无须麋。”杨倞注:“麋,与眉同。”综合字形线索和文献证据,可知“麋”之名源为“眉”。由此可以看出:汉字早期阶段形意字的造字取象对探求上古汉语词源理据有帮助,汉语词源研究对汉字形体线索的利用,不应局限于“右文说”。上古汉语词汇派生与汉字形声孳乳相伴而行,很多形声字的声符具有揭示词源的功能,而形声字声符的形式主要是以独体之“文”为基础的形意字,因此,“右文说”的深入发展,也需要加强对形意字的研究和利用。
《文始》“初文”使独体字在汉语词源研究中的价值得到彰显。《文始》通过对“初文”构形理据的分析来探求词源意义,也为汉语词源研究利用汉字形体线索开拓了新方法。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始》对“初文”的设计和使用已非常合理。“初文”作为独体字,其尽管在会意字中作为基础构件而存在,但独体字和会意字之间并没有字形孳乳关系。《文始》以“初文”为系联起点,以“孳乳”“变易”为系联条例,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就容易忽视会意字。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与“初文”相关的很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 本文除第一部分外,其他部分所论“初文”包含“准初文”.
[2] 王力《同源字典》,第4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3] 详《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第50—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4] 百度百科“彩陶缸绘鹳鱼石斧纹”。
[5] 王晖《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12页。
[6] 学者对“文字画”的认识不完全一致。沈兼士先生认为:“在文字还没有发明以前,用一种粗笨的图画来表现事物的状态、行动,和数量的观念,就叫做文字画(picturewriting)。”(《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载《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21—22页,中华书局,1986年)唐兰先生则对“文字画”持否定意见。(《中国文字学》,第67—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7]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第10—12页,语文出版社,1998年。
[8] 张亚初《商周金文姓氏通考》(第179页,中华书局,2016年)认为“雚母”之“雚”为姓氏。古姓、图腾、族徽,三者关系密切。又,商代铜器铭文常见“族徽+人称”,如“鱼父乙”即族徽“鱼”+人称“父乙”,“玄鸟妇”即族徽“玄鸟” + 人称“妇”;据此,“雚母”即族徽“雚” + 人称“母”。或释“雚母”之“雚”为地名、方国名;“雚母”或释为人名“雚女”。这些观点,缺乏有力的证据。
[9] 黄侃《黄侃论学杂著》,第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0] 章太炎《转注假借说》,载《国故论衡》(陈平原导读),第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11] 从《文始》所系联词族中,既能感受到章太炎先生对汉字字形线索的高度重视,也能感受到章太炎先生对汉字字形线索的有意回避。这反映了章太炎先生进行汉语词族系联的两难选择:割裂汉语与汉字,忽视汉字字形线索的汉语研究注定会迷失方向;混淆汉语与汉字,过度依赖汉字字形线索又会将汉语研究带进另一歧途。汉语与汉字关系的研究,是目前学界十分重视但仍未能深入解决的问题之一。章太炎先生进行汉语词族系联,难免会对汉字字形线索的认识、利用出现矛盾。这种矛盾,也导致本文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存在矛盾,例如后文所论《文始》问题之一即“忽视汉字形声孳乳线索,混淆词汇意义与词源意义”。此处所论“重视”,更多是学理层面的重视;后文所论“忽视”,更多是材料层面的忽视。
[12]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3] 具体论证详陈晓强《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考释篇之“今”声,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14]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52页,中华书局,1986年。
[15] 为了便于指称,本文以《文始》“初文”为相关词族的名称。
[16]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文始》,第455—4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7]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文始》,第4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8]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文始》,第4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9]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文始》,第300—3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20] 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第2010—201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1] 陆宗达、王宁《论字源学与同源字》,载《训诂与训诂学》,第382—384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22] “初文”为汉语词源的全面系联提供了音的基本点。王宁先生在2006年讲授《文始》时和同学们讨论得出此观点,该观点与黄侃先生所论“文”为“声音之根”有相通之处。(详黄侃《略论推求语根之法》)
[23]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文始》,第2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24]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文始》,第3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25]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70页,中华书局,1986年。
[26] 张舜徽《张舜徽集·霜红轩杂著·汉语语原声系》,第6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7] 张舜徽《张舜徽集·霜红轩杂著·汉语语原声系》,第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8] 张舜徽《张舜徽集·霜红轩杂著·汉语语原声系》,第25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9]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12页,中华书局,1986年。
[30] 王力《同源字典》,第613—61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31] 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第815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2] 论证详陈晓强《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考释篇之“句”声,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33] 章太炎《语言缘起说》,载《国故论衡》,第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34]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11页,中华书局,1986年。
[35] 陆宗达、王宁先生所论“汉字字源学”,实即“汉语词源学”。
[36] 陆宗达、王宁《论章太炎、黄季刚的说文学》,载《训诂与训诂学》,第348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37] 根据传统“六书”分析,形意字可分为象形、指事、会意三大类别。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查看)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王晖《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年。
张亚初《商周金文姓氏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张舜徽《张舜徽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陈晓强《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俄]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作者简介

陈晓强,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兰州大学古文字学强基计划专业负责人,中国文字学会理事。
本文发表于《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三十辑,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汉语研究与社会应用实验室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董京尘 谢琰
责任编辑:李向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