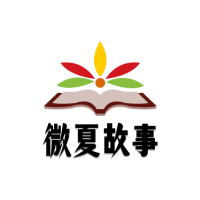与我结婚三年,甚至我提出离婚,梁靳白也笃定我离不开他。
可是后来等在大雪里求我的原谅的那个人也是他。
1.
找到梁靳白时,透过门缝一字一字蹦了出来。
「靳白,今天梁叔大寿你真的不回去看看吗?」
「不回去。有程昭在一天我就绝不踏进梁家。」
我静默了一秒直接推开门。
包厢内的空气有一瞬间的停滞。
他在看见我后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你来做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陈述着事实:「今天爸生日,全家人都在等你。」
「跟我回去。」
众人大气不敢出。
可我只是冷静地重复那句话:「你该跟我回去。」
2.
在人生的前二十多年里,围绕我的只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被梁家收养的孤女,一个是梁家的儿媳。
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是梁家朝我递来了救赎的橄榄枝。
他们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梁家儿媳。
可是从一开始,梁靳白就不喜欢我。
他顽劣,时常换着法子折磨我。
他会在冬日里将昂贵的手链丢进泳池,逼我跳水去捡。
也会在夏日里故意打碎古董花瓶栽赃到我身上,害我在烈日炎炎的正午里罚跪晕倒。
转机发生在十六岁那年的暑假,因为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梁靳白对我的态度缓和了许多。
他开始替我在学校里撑腰,甚至送出了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份礼物。
那时我满心欢喜,以为是苦尽甘来。
却没想到噩梦会来得这么快。
我的成人礼,在梁宅大办了一场。
席间有好事者在本属于我的酒杯里加了一些料,我因为私事晚到了些,那杯酒竟阴差阳错被文禾喝下。
等被众人发觉时,文禾的嗓子眼已经开始往外冒血,再也发不出一个音节。
那时梁靳白抱着文禾跪在地板上,看向我的眼神却尽是冷冽。
他说:「程昭,你是灾星吧?」
灾星。
想到这,我盯着面前那杯酒红的液体,竟不自觉笑出了声。
如果真的有一报还一报。
那这个困扰了我很久的噩梦,或许今日就能终结。
于是我不顾众人的阻拦,垂眸接过酒杯就要往喉咙里灌。
一双大手却兀然出现在眼前。
想象中的辛辣刺痛感并没有发生。
梁靳白快手抢过酒杯,他冷着脸哼了一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解脱没这么容易。」
说完,他骨节分明的指节已经捏着酒杯倒扣过来。
血红的液体顺着发丝流下,在我的白裙上洇出一朵朵红色的花。
一如文禾那晚吐出的血。
梁靳白眯起狭长的眼眸,他居高临下地看向我。
「你欠文禾的,就算用你这条命来抵都不够。」
3.
我独自回了梁家。
回程的路上,理所当然地接到了梁夫人的电话。
「靳白呢,没跟你一起?」
我紧握着手机,组织了很久的语言最终也只是低低地应了一声。
尖酸刻薄的话语顺着听筒就传了过来,「无能!我梁家培养你这么多年,你竟然连丈夫的心都拢不住。」
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雨点砸在车窗上,留下若有似无的痕迹。
我盯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死咬着嘴唇,等尝到血腥味才发觉电话里对我的审判已经接近尾声。
梁夫人的情绪平复了许多,她冷漠地吩咐:
「你今晚不用回梁家了。在车库前跪一晚上,想想自己到底错哪了。」
……
罚跪。
永无止境的罚跪。
雨势越来越大,豆大的雨点砸下来,我跪在水磨砖上,全身酸痛几乎要散架。
雨幕中蓦然亮起一道刺眼的车前灯,我低垂着眉眼,头也没抬。
伴随着皮鞋接触地面的清脆响声,雨好似小了些。
一双沾染着雨水泥污的皮鞋赫然出现在眼前,清朗的嗓音在雨中回荡。
我听见他说:
「挺能跪的,继续。」
「这才有点梁家儿媳的模样。」
我努力抬起头,扯起嘴角乖顺地朝他笑了笑,「谢谢夸奖。」
然后精疲力尽,眼前一黑,彻底晕了过去。
4.
再次醒来时,已是三天后。
刺鼻的消毒水味呛得我直咳嗽。
我捂着口鼻缓了好一会,才发觉整间病房里除了我空无一人。
好似这么多年我在梁家的处境。
我挣扎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
房门又被猛地踹开。
微小的颗粒在空中飞舞,我看见文禾走了进来,气势正盛。
她双手交叉端坐在木椅上,好整以暇地看向我。虽不能说话,眼角眉梢却尽是得意。
我的视线却被她腰间挎着的提包吸引。
那是一个皮草包,一些黑白相间的花纹延续到左提手处停止。
我看着却莫名觉得眼熟。
我疑惑望向她,正欲开口,手机又响了起来。
来电显示是好友思思。
刚一接通,她就焦急地喊道:「昭昭,米酒不见了。」
我心里一惊,还未来得及开口,又听见她说:「米酒就是你晕倒那天晚上走丢的,本来我顾忌着你生病住院想瞒着你,可是我查了监控发现米酒是被人偷走的,这都第三天了没有一点头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听筒里抽泣的声音断断续续,我听着却觉得大脑一片空白,几次想开口张嘴却发不了声。
我死死攥着手机,眼泪也不知不觉流下来。
泪眼模糊间,我好像看见一旁的文禾扬了扬手中的提包。
她举起了手机,上面有几个大字——
「米酒在这啊。」
5.
米酒是我十七岁那年养的小猫。
它是一只小狸花。
虽然流浪却异常亲人,从我第一次见到它开始便会主动蹭着我的裤腿要吃的。
梁靳白并不喜欢小动物,那段时间我与他的关系刚缓和,我便有意将米酒藏了起来。
直到一周后我给米酒喂粮时被发现,他并没有如我预想中生气。
只是颇为嫌弃地摆了摆手:「你要是实在喜欢,就养在我二环的那套平层。妈对猫毛过敏,别让她发现。」
就连米酒这个名字,也是梁靳白起的。
因为他第一次品尝米酒这种新奇的食物,也是在我的撺掇下。
他只尝了一口,便捏着鼻子倒掉了剩下的。
他总嘴硬说小猫跟米酒一样讨厌,却又会耐着性子给它换粮换水。
透过米酒,我好像看见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梁靳白。
甚至米酒突发肠胃炎住院的晚上,我曾无意中瞧见梁靳白独自躲在角落抹眼泪。
梁家最矜贵的小少爷,竟然也有如此柔情的一面。
可这些深埋我心底的记忆也在十八岁暑假乍然终止。
梁靳白厌恶我的同时,也不再踏进二环的平层。
米酒时常会呆呆地望着门口的方向,像是饥渴顿踣又渴求一个答案的旅人。
我该怎么告诉它呢。
在它剩下的生命周期里,梁靳白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出现。
它还没有等到想要的答案。
生命便已在三天前戛然而止。
所以并不是眼熟。
那个皮草包,就是完整剥下米酒的皮做的。
提手处突然顿住的花纹,是米酒流浪时被轧掉的左腿。
6.
米酒是被活活溺死的。
它被捆在麻袋里,然后压在几块巨石下沉入池底。
不过几分钟,池面便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可整整一小时后,麻袋才被拉出来。
再用磨得发亮的小刀一点点剥下米酒身上整块毛皮。
……
每听一步,我的心脏就好像被人用大手狠狠揪起一般的窒息感。
我得让文禾也尝尝米酒临死前的濒死感。
望着一旁笑得近乎癫狂的文禾,我几乎下意识扯着她的领口往卫生间走。
任凭她怎样挣扎,我都死死钳住她的脖子。
然后将她的头摁进盛满水的水缸。
这些年我委身梁家只求一丝生机,从未有过如此畅快的时候。
水面不断漾开一圈圈波纹,我强硬地拽起她的头发迫使她与我对视。
一双大手却近乎执拗地将我们分开。
梁靳白像是急匆匆赶来,汗水润湿了他额前的碎发,却还是警惕地将文禾护在身后。
他陡然拔高了音调,「程昭你疯了?」
惯性使然,我被狠狠甩在一旁的门框上。手臂处传来结结实实的痛,我却顾不上,只是固执地抬起头与他对视,然后歇斯底里地喊:「我疯了?梁靳白,你搞清楚,文禾她活生生溺死了米酒,还剥了米酒的皮做包。你怎么偏爱她我都没意见,这种时候你还要装聋作哑吗?你有没有一点良心!」
闻言,梁靳白也只是极轻地皱了皱眉,然后禁锢住我的肩膀,嗓音带了些怜惜,「一只畜生而已。你要是喜欢,我就赔十只甚至一百只狸花猫给你,只要你能消气。」
多讽刺啊,十八岁后梁靳白第一次向我低头求和竟然也是为了文禾。
于是我用力挣开他,顺势倚靠在身后的门框上。
眼神在两人身上兜转了一圈,我伸手抹掉了脸上的眼泪,反倒很轻地笑了出来。
「你俩,都一样的让我恶心。」
「梁靳白,跟你结婚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耻辱。我们离婚吧。」
此话一出,空气都静默了一瞬。
梁靳白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事情,他伸手轻揩了嘴角的水渍,才慢条斯理地回复:「离婚,我当然乐意至极。」
「只是梁家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养你这么多年,你总得先把费用结清。」
我点了点头,并未反驳。
「那就麻烦你拉个表格出来,将明细发送到我的邮箱,我会尽快结清。明天我就回梁家收拾行李,离婚协议会放在卧室的桌子上,你抽空仔细看看。」
「其他的,如果你有什么诉求,也可以提出来。」
然后,用力推开愣在原地的男人,头也没回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