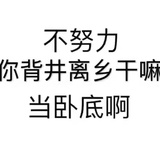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徐淵
《儀禮》《禮記》《周禮》三部典籍在中國歷史上被合稱爲《三禮》,《三禮》研究是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由於《三禮》所涉名物、制度、稱謂繁多,所涉史事、文獻、義理龐雜,故《三禮》研究常常要求研究者對傳世禮學文獻有較高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不能深入理解傳世禮學文本的具體內涵,往往無法對禮學文獻具體涉及的儀節及其義理得出正確的判斷。正由於禮學研究的這種特性,歷代禮學家對禮學文獻本身的重視,要遠遠超過對其他非禮類文獻的關注,這種研究風氣即使到了二十世紀仍然没有發生太大的改觀。
二十世紀以降,中國大地上出土文物及包涵文字信息的出土文獻不斷涌現,從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先秦秦漢研究的基本面貌。出土文獻的不斷面世,使得今人有了第一手材料,從而可以擺脱傳世文獻的束縛,對上古時代進行更爲直接的探究。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甲骨文第一次爲世人所知,甲骨文上所刻的文字被認定爲古文字。通過對甲骨文的初步釋讀,1917年王國維撰寫了《殷周制度論》這一名篇。這是首次通過對出土文獻的釋讀來解決先秦重大禮制問題的嘗試。無論《殷周制度論》的結論是否可靠,依據出土文獻解決先秦禮制問題的思路和方法爲後來的學術研究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王國維先生甲骨文書法

沈文倬在《略論禮典的實行與〈儀禮〉書本的撰作》(以下簡稱《撰作》)中引其師、晚清民國禮學家曹元弼之説,“二戴《記》之説禮,大類有三,曰禮、曰學、曰政。《曲禮》、《檀弓》、《遷廟》、《釁廟》、《冠義》、《昏義》、《朝事義》等篇,禮類也;《學記》、《中庸》、《儒行》、《大學》、《曾子》十篇,學類也;《王制》、《月令》、《夏小正》、《文王官人》之等,政類也。[1]”沈文倬同意乃師之説,認爲“按三大類來區分大戴輯《禮記》三十九篇、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就能使各篇何者當屬禮類,何者當屬政、學類,性質明確,界限清楚[2]”。
曹元弼這種分類對於先秦禮類文獻的分類具有重大的意義,是禮學家從傳世禮學文獻内部區分文獻性質的重要發現。這種對先秦禮學文獻的區分方式同樣貫穿於沈文倬的禮學研究,沈文倬在《漢簡〈服傳〉考》中也提到“《禮記》内容龐雜,要而言之,可分論學、論政、論禮三類,就論禮諸篇來説,實是《禮經》的傳記[3]”。由於二十世紀中期以來傳統禮學没有受到足夠重視,這種對先秦禮類文獻按性質進行分類的方式雖然極富洞見,但至今尚没有被廣泛應用到禮學文獻的研究之中。
按照曹元弼的分類方法,不但二戴《記》的篇章可以按屬性分類,對先秦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也可以做以上三類法的劃分。
學類文獻曹元弼臚列了《學記》《中庸》《儒行》《大學》《曾子》等篇目,這些篇目多爲孔子與七十子對話的記錄,多數篇章爲語錄問答形式,與《論語》體例十分類似。以《中庸》爲例,雖然宋代理學家將其獨立出來成爲《四書》之一種,但以先秦文獻的角度來看,它無疑與所謂子思四篇中另三篇《坊記》《表記》《緇衣》同屬一類文體。這類文獻所記錄的也多是孔子與弟子論心性、學習、爲人、爲政的内容,是孔子教育弟子的生動記錄。《學記》《儒行》《大學》等篇章有大段的散體論述,有些論述作爲整體出現在孔子的回答中,孔子所談的論題與《論語》所論述的主題類似,這類文獻也被歸入學類文獻。依據同樣的標準,郭店簡中的儒家文獻《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都可以劃分在學類文獻之中,郭店竹書基本没有一篇可以算作政類或禮類的禮學文獻。
政類文獻曹元弼臚列了《王制》《月令》《夏小正》《文王官人》等篇目,所謂政類則是指集中論述禮制,尤其是政治制度方面的文獻,包括先秦曆法、職官、等級、政令等内容,與後世記錄政體、官制的文獻相類似。這類文獻與《三禮》中《周官》的關係密切,是研究先秦政體制度的重要材料。這類文獻與學類及禮類文獻有明顯的區别。出土文獻中金文職官研究、曆法研究等與這類文獻密切相關。
禮類文獻曹元弼臚列了《曲禮》《檀弓》《遷廟》《釁廟》《冠義》《昏義》《朝事義》等篇,這類文獻即沈文倬在《撰作》一文中所指的禮典文獻,沈文倬説:“‘禮以體政’,適應於政治需要的各種禮典是具體的。”又舉《尚書·堯典》“三禮”説、《禮記·祭統》“五禮”説(吉、凶、軍、兵、嘉)、《禮記·昏義》“八禮”説(冠、昏、喪、祭、朝、聘、射、鄉)、《大戴禮記·本命》“九禮”説(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禮)、《禮記·仲尼燕居》“十禮”説(郊、社、嘗、禘、饋、奠、射、鄉、食、饗)來説明禮典在先秦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4]。沈文倬認爲《儀禮》是先秦記錄禮典的核心文本。“用文字記錄下來的各種禮典,我們稱之爲‘禮書’,是記錄‘禮物’、‘禮儀’和它所表達的禮意的文字書本,現存的《儀禮》十七篇就是它的殘存部分。”[5]沈文倬後來提出的禮典文獻(沈文倬稱爲“禮書”文獻)顯然與曹元弼在説明二戴《禮記》文獻的性質時,對禮類文獻的劃分内涵完全一致,包含了二戴《禮記》中與禮典相關的所有篇目。沈文倬對於《禮記》中禮典相關篇目的界定更爲細緻:
説《禮記》是《禮經》的傳記,突出地表現於下列諸篇,如《冠義》之於《士冠禮》,《昏義》之於《士昏禮》,《鄉飲酒義》之於《鄉飲酒禮》,《射義》之於《鄉射禮》、《大射儀》,《燕義》之於《燕禮》,《聘義》之於《聘禮》,《喪大記》、《奔喪》之於《士喪禮》、《既夕》,《喪服小記》、《雜記》、《間傳》、《大傳》、《三年問》以及《檀弓》、《喪服四制》等之於《喪服經》。這些篇章所題的記、傳、義是一個意思,即十七篇經義,它是爲解經所未明,補經所未備而撰作的。[6]
沈文倬認爲“《儀禮》十七篇僅屬殘存,一部分禮典書本已在秦火中亡佚,因此不應該以現存的十七篇的範圍來看待殷、周禮典”[7]。沈文倬在《撰作》一文中通過甲骨卜辭、青銅器銘文、《禮記》、《毛詩》、《左傳》、《國語》、《周官》及諸子典籍中涉及禮典的文獻來補《儀禮》所記禮典的闕漏。雖然沈文倬没有對出土文獻的邊界做嚴格的界定(其中包含了不少考古資料),但是第一次大致劃分了與禮典有關的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的範圍,並示範性地使用這些材料研究了殷、周禮典,爲以出土文獻研究兩周禮典做出了初步的嘗試。
由曹元弼、沈文倬做出的禮典文獻的界定(曹元弼稱爲“禮類”文獻、沈文倬稱爲“禮書”,本文認爲稱爲“禮典文獻”最爲恰當),爲涉禮文獻的分類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説明了以《儀禮》爲核心的禮典類文獻的獨特性,使得研究者可以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繼續推進各類禮學文獻的研究。

沈文倬先生舊照(攝於書房)

要界定與禮典有關的出土文獻範圍,首先要對研究先秦禮制所能利用的出土文獻做出界定。對在這個範圍内的文獻加以窮盡性地搜羅探討,對於這個範圍之外的材料則不再加以關注。一般認爲,出土文獻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出土器物上所書寫銘刻的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簡帛文字、璽印文字、陶文等呈現在不同材質載體上的文字資料。出土器物上所包含的文飾、花樣、圖案等内容往往遭到忽視,這是由於在整個先秦研究的文獻材料中,圖畫、紋飾所佔的比例很小,而能與傳世文獻相印證的圖畫、紋飾更少。在西方古典研究中,有大量雕塑、繪畫、圖案描繪了特定的重大歷史主題,對這些文物上的圖畫、紋飾的研究構成了西方古典研究重要的組成部分。之所以要將這些圖畫、紋飾内容作爲出土文獻的研究對象,是因爲文字與圖案作爲文獻所提供的信息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有時圖案、紋飾提供信息的豐富性還要勝於文字。現代社會仍然習慣於使用圖書來指稱書籍的總體,就是因爲書籍本身所包含的,除了文字内容以外,還有大量的圖像資料。如果將這些材料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就缺乏對出土文獻的完整認識,會大大縮小出土文獻的利用範圍,從而減少出土文獻帶來的有價值信息。
除了以上將出土器物本身所含有的文飾、花樣、圖案補充進出土文獻,作爲出土文獻重要的組成部分,還需要對出土文獻的外延做出明確界定——即作爲出土器物本身的考古資料,以及這些器物之間的相互位置關係、年代關係、等級關係等,不能被視爲出土文獻。比如,在先秦遺址和墓葬中常常能發現可與傳世文獻相對應的器物,即使這些器物本身能説明傳世文獻的一些情況,或者被認爲即是傳世文獻中所稱的某種器物,這些器物也不因此被認定爲可供研究的出土文獻,而是仍要被視爲考古學資料。只有出土器物上出現的可以説明傳世文獻中的某些特定器物、場景、儀節的文字、圖案,才是可供研究的出土文獻。
之所以要突出出土器物本身與出土文獻(主要指出土器物上的文字、圖案)之間的差别,在於根據這一劃分可將近年來考古學的禮學研究與出土文獻的禮學研究做一個明晰的劃分。在根據新的考古資料做禮學研究的全部成果中,將這些成果劃分爲兩個大類,一類是通過出土器物及出土器物的相互關係來與禮書中的相關内容做對比研究,這類研究是以考古學與文博學爲研究基礎的;另一類是通過出土文獻(文字與紋飾)來與禮書中的相關内容做對比研究,這類研究是以出土文獻與古文字學爲研究基礎的。前一類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吴十洲《兩周禮器制度研究》、姬秀珠《儀禮沃盥禮器研究》、高崇文《古禮足徵——禮制文化的考古學研究》等,代表性文章有陳公柔《士喪禮、既夕禮中所記載的喪葬制度》、張光裕《從新見材料談〈儀禮·飲酒禮〉中之醴柶及所用酒器問題》等,這類研究主要是依靠考古學的成果與先秦禮制相印證,從而達到對先秦禮制加深認識的目標。後一類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楊華《古禮新研》、賈海生《周代禮樂文明實證》等,代表性的文章有沈文倬《漢簡〈服傳〉考》等,這類研究主要是依靠出土文獻的内容與先秦禮書相比較,進一步探究先秦禮書與禮典的内涵。
以出土文獻研究兩周禮典應當將考古發掘所得的出土器物及包括喪葬用具、墓葬設施、隨葬用品等在內的墓葬、遺址相關信息排除在考察範圍之外。要嚴格區分作爲出土文獻的文字及文飾與作爲考古資料的實證器物及相關信息。從某種意義上說,由於出土器物本身並不具有文獻性質,對出土器物的討論應該限定在考古學的範疇之内,而對出土器物上文字及文飾的討論應當納入文獻學研究的範疇。
作了以上區分之後,就可以對本書所涉及出土文獻的基本邊界做出清晰的界定,凡是屬於出土文獻範圍的材料,在做兩周禮典研究時應加以深入的考察;凡是不屬於出土文獻範疇的考古資料,就不再對這些資料進行分析討論。嚴格區别出土器物本身與出土器物所包含的出土文獻是本書的研究起點,也是對之前以考古資料研究先秦禮制、禮書成果的釐清。往後所有依托考古資料來對先秦禮制進行的研究,都應該自覺地先以此標準清晰地界定兩種不同的研究路徑,這兩種研究路徑所需要的知識儲備和基礎訓練是大不一樣的。
需要特别説明的是,出土文獻中有一類特别的文獻——遣册。雖然遣册本身毫無疑問是出土文獻的一部分,但由於遣册所記載的内容往往與出土墓葬中的陪葬器物具有嚴格的對應關係,對這類文獻研究的基本方法處於出土文獻學與考古學交叉的位置上。由於遣册内容與墓葬器物往往具有嚴格的對應關係,使得對遣册的研究更偏向於考古學的範疇。遣册文獻不具有書類文獻所包含的敘事内涵,僅僅在墓主下葬時作爲記錄器物的簿册使用,故内容較爲瑣細,一般不體現禮典的重大儀節。要將遣册所記錄的内容與禮書進行比較研究,就繞不開考古學對器物本身及器物間相互關係的研究。遣册研究與考古學研究的緊密聯繫使得研究者無法以典型的出土文獻研究範式來看待遣册文獻。因此,可以將遣册及相關的墓葬出土器物視爲一類特殊的禮典研究資料,與通過出土文獻對禮典進行研究的方法區别開來。

散氏盤銘文

由於殷墟甲骨文[8]所反映的皆爲商代禮制及禮典的内容,故本書不對甲骨文做直接的禮典研究,只有甲骨文與西周金文所反映的禮典内容有關聯性的時候,才附帶地對甲骨文進行禮典分析。
第一,由於兩周金文中所反映的禮制内容非常豐富,是禮典研究的重要出土文獻,故本書首先利用兩周金文(含少量周代甲骨文)對西周至春秋戰國的禮典進行研究。對兩周金文的準確釋讀是認識金文所述禮典的基礎,界定兩周金文所涉及的禮類是認識銘文文獻性質的關鍵。
其次,利用出土文獻研究兩周禮典,應當重視與《儀禮》經記文、《禮記》諸篇成書時代接近的出土文獻材料,或者時代略晚於兩周禮典時代、可以印證兩周禮典具體儀節的出土文獻。這些文獻可以被視作重新探討《儀禮》等文獻所記述禮典更直接的文獻資料。由於《儀禮》是書類文獻,故出土文獻書類文獻中述及禮典的内容是居於核心地位的。這類文獻包括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等中涉及禮典的相關篇章。
第三,兩周器物上爲了美觀所鑄造刻畫的圖畫和繪製的紋飾也具有文獻性質,應該對其中涉及禮典的文獻加以討論。由於圖案所包含的信息量較大,反映的内容也較爲直觀,這類文獻無論是否含有題記,都對討論兩周禮典具有重要的意義。這類文獻的代表有包山二號墓漆奩上的“昏禮親迎儀節圖”、戰國嵌錯刻紋銅壺的紋飾等。
第四,春秋戰國時代出土簡帛文獻中的卜筮祭禱類文獻。卜筮祭禱類文獻不具備與書類文獻同等的經典性質,更多地以地方性禮俗文獻或書記文獻的面貌出現。這類文獻與禮典的比較研究頗類似於當代人類學對早期古典的闡釋研究。卜筮祭禱簡所記內容,雖然無法直接與禮典的相關儀節掛鉤,但卻可以看作先秦禮典所規定制度的禮俗遺存與地方變型。這類文獻的代表有包山楚簡中的祭禱簡,與兩周禮典中的祭禮有直接的相關性,但其反映的是楚地獨有的祭祀禮俗。
第五,成書時代較晚的出土秦漢文獻,其中有一些與《儀禮》中的部分篇目直接相關,它們是漢代人學習兩周禮典類文獻的文本。原則上,如果對秦漢出土文獻進行細分的話,也可以分爲上述銅器銘文文獻、簡帛書類文獻、器物圖案文獻及日用文書禮俗文獻四種類型。由於出土秦漢器物上的文字、紋飾所反映的禮制基本限於秦漢時代本身,無法有效反映先秦春秋戰國時代的情況,故漢代銅器銘文文獻、器物圖案文獻及日用文書禮俗文獻這三類可以不作爲研究兩周禮典所需考察的出土文獻。只有與解釋先秦禮書及禮典有關的書類出土文獻,才納入以出土文獻研究兩周禮典的範疇。這類文獻的代表有西漢馬王堆漢墓帛書《喪服圖》、以及武威漢簡《儀禮》《服傳》等。
第六,古代發現的出土文獻,其中與禮典有關的資料也應作爲兩周禮典研究的重要材料。古代出土的先秦文獻主要有孔壁出書與汲冢竹書。由於孔壁所出的古書在漢代已經被隸寫,並且很多成爲今天傳世文獻的一部分,所以不作爲出土文獻加以討論。汲冢竹書相傳出於戰國魏襄王之墓,如果史書記載不誤,則汲冢竹書現在所存篇目的屬性確屬戰國書類文獻。汲冢竹書中《竹書紀年》現僅存輯佚而得的《古本竹書紀年》。由於《古本竹書紀年》中涉禮的文句很少,故無法找出足夠與禮典相關内容來作爲兩周禮典研究的素材,因此本書没有對其做深入考察。汲冢竹書中的《穆天子傳》曾被不少研究者認爲偽書。以現在掌握的出土文獻知識看,其書的不少特徵確實符合先秦出土文獻的特點,當屬面貌較爲存真的出土文獻整理本。《穆天子傳》記述周穆王周遊天下的事跡,其中多數事跡均以禮典的形式反映出來。卷六《周穆王盛姬死事》中記述了盛姬喪禮的全過程,是目前所有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唯一一篇完整記載王級喪禮的文獻,禮典研究價值巨大,前人卻鮮有涉及。

長沙馬王堆帛書·《喪服圖》

沈文倬在《撰作》一文中,對《禮記》中哪些篇目屬於禮典文獻有清晰的界定:
學、政諸篇及《樂記》可置勿論,秦漢人之作應予剔除,列入禮類的,小戴輯所有:《曲禮》上下、《檀弓》上下、《曾子問》、《禮器》、《郊特牲》、《玉藻》、《喪服小記》、《大傳》、《少儀》、《雜記》上下、《喪大記》、《祭法》、《祭義》、《祭統》、《仲尼燕居》、《奔喪》、《問喪》、《間傳》、《三年問》、《深衣》、《投壺》、《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大戴所輯有:《禮三本》、《虞帝德》[9]、《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朝事》、《投壺》、《公冠》[10]、《本命》等,凡三十九篇。[11]
根據沈文倬對二戴《禮記》篇目的分類,合《儀禮》篇目述及的禮典,對先秦禮書所涉及的禮典類型可以做以下文獻歸類(見下表):

先秦禮書涉及禮典類型表
上表是對傳世禮書中所涉禮典的大致分類,由於《禮記》諸篇中單篇涉及多種禮典的情況非常普遍,故不少篇目無法完全確定其禮典類型的歸屬,只能就其主要内容做大致的分類。出土文獻所涉禮典類型的情況將以此作爲一個起點。在後面的研究中,會發現出土文獻所論述的禮典大致不超出本表所歸納的類型(金文多兩個主要禮類:軍禮(獻俘禮)、冊封禮),只有西周早中期金文所涉祭祀禮典要多於上表所述涉禮類,具體原因會在相關章節中作出説明。
————
以上論述對於兩周禮典研究相關的出土文獻做了界定,對於近幾十年來利用出土文獻與考古資料研究兩周禮典的兩種路徑做了區分。特定的出土文獻資料規定了利用其研究兩周禮典時所應當採取的態度和所受到的局限,對出土文獻的材料性質進行分組分類是研究兩周禮典的前提。在這樣的前提下,對出土文獻的内涵進行最大限度的挖掘,才能充分發揮出土文獻的效用。
錯誤地理解和利用先秦秦漢出土文獻與兩周禮典的對應關係,將直接導致錯誤的研究結論。過分地誇大非經典性質的出土文獻的價值,或者忽略具有經典屬性出土文獻的價值,都將嚴重妨礙使用出土文獻研究兩周禮典以及利用兩周禮典的知識校正出土文獻文本的準確性。在之前幾十年的研究中,這類誤用的情況屢見不鮮。本書希望通過嚴格的區分和限定,爲未來利用出土文獻研究兩周禮典製定比較合理的框架。在這個框架内,不同性質的出土文獻材料都能找到合理使用尺度和研究方式。
注釋
[1] 沈文倬:《略論禮典的實行與〈儀禮〉書本的撰作》(下),《文史》第十六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11月,第8頁。沈文引自曹元弼:《禮經學》卷四《會通》。
[2] 同上引。
[3] 沈文倬:《漢簡〈服傳〉考》(下),《文史》第二十五輯,第4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0月。
[4] 沈文倬:《略論禮典的實行與〈儀禮〉書本的撰作》(上),《文史》第十五輯,第2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9月。
[5] 同上揭,第30頁。
[6] 沈文倬:《漢簡〈服傳〉考》(下),《文史》第二十五輯,第40頁。
[7] 沈文倬:《略論禮典的實行與〈儀禮〉書本的撰作》(上),《文史》第十五輯,第21頁。
[8] 由於出土甲骨文多爲殷墟甲骨文,少量爲周原甲骨文,故爲了行文方便,本文稱甲骨文者一般都是指殷墟甲骨文,凡用到周原甲骨文者皆標注“周原甲骨”。
[9] 所引原文爲《虞帝德》,各本作《虞戴德》,爲沈文倬所改。
[10] 沈文倬據戴震校本,改“公符”爲“公冠”。戴震曰:“冠”各本訛作“符”,今訂正。
[11] 沈文倬:《略論禮典的實行與〈儀禮〉書本的撰作》(下),《文史》第十六輯,第8頁。沈文倬既然將《曲禮》《少儀》《深衣》納入禮典文獻,《内則》實際也可以納入這個範圍,專講侍奉長輩之禮儀,可以歸入表中“禮容、禮辭、禮服”一欄。
[12] 大戴記《虞戴德》篇中述禮内容不多,沈文倬將其歸入禮類文獻不知何故。沈文倬的三十九篇之數大於曹元弼所列篇目,其中某些篇目述禮的内容並不多,列入禮類文獻,似可斟酌。
新書推介 圖書信息叢書:“禮學新論”叢書書名:兩周秦漢禮典相關出土文獻考疑出版社:武漢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3年10月 字數:32萬 版次:一版1印 ISBN:978-7-307-23522-9定價:79元作者簡介
圖書信息叢書:“禮學新論”叢書書名:兩周秦漢禮典相關出土文獻考疑出版社:武漢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3年10月 字數:32萬 版次:一版1印 ISBN:978-7-307-23522-9定價:79元作者簡介 徐淵,男,浙江鄞縣人,出生於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現爲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任同濟大學經學研究院副院長、中華孔子學會經學研究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上海儒學研究會理事。任《現代儒學》《春秋學研究》編委。中國訓詁學研究會、中國先秦史學會會員。著有《兩周秦漢禮典相關出土文獻考疑》《〈儀禮·喪服〉服敘變除圖釋》,整理古籍杜預《春秋釋例》、鄭玄《禮記注》等,參與點校《春秋公羊禮疏(外五種)》(獲華東地區古籍整理二等獎)。執行主編《十三經漢魏古注叢書》。發表學術論文三十餘篇,承擔國家社科基金等各類項目多項。圖書簡介本書從兩周禮典研究的角度出發,首先界定了出土文獻類禮典研究文獻與考古類禮典研究資料的基本區別,進而對禮典相關出土文獻做了分類,將目前已經出土的與禮典研究密切相關的文獻分爲六個大類。通過對這幾類出土文獻中禮典相關內容的深入分析,揭示利用不同種類出土文獻研究禮典的普遍原則和具體方法。將研究禮典相關出土文獻共同的普遍原則與研究不同屬性出土文獻的具體方法結合起來,應用到一個個具體的出土文獻禮典研究案例中去,以此檢討這些原則和方法的長處和局限。本書梳理了目前已經取得的出土文獻與兩周禮典研究的成果,並利用這些成果推進了對傳統禮典研究的討論。同時,本書還試圖利用傳統禮學的知識體系對出土文獻的字詞釋讀和文本整理提出新的設想,進而討論相關出土文獻的性質與成書過程。目錄前 言第一章 緒論第二章 兩周青銅器銘文與兩周禮典研究第一節 商晚西周出土文獻與兩周禮典研究概説第二節 釋讀錯誤引起誤收或失收青銅器銘文涉禮文獻第三節 青銅器銘文涉“禮”與涉“事”混淆的情況第四節 涉禮標準泛化引起誤收涉禮青銅器銘文文獻第五節 從時代性看祭祀禮類金文文獻的特點第六節 青銅器銘文涉禮但却没有對應禮典詞彙造成的失收第七節 “大叔”在先秦文獻中的特殊内涵第三章 出土戰國書類竹書文獻與兩周禮典研究第一節 郭店楚簡《六德》“爲父絶君”句析義第二節 上博簡《天子建州》與天子諸侯饗禮第三節 上博簡《鄭子家喪》所反映的春秋時代刑餘罪人喪葬儀式第四節 從清華簡《耆夜》飲至禮典推測其成書年代第五節 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篇涉禮字詞考釋第四章 春秋戰國出土器物文飾圖像與兩周禮典研究第一節 包山二號楚墓妝奩漆繪“昏禮親迎儀節圖”考第二節 射禮禮典與嵌錯刻紋銅器圖案辨誤第五章 戰國楚地出土卜筮祭禱簡與兩周禮典研究第一節 包山二號楚墓祭禱簡祭禮餘義淺述第二節 楚祭禱簡不具有祭禮禮典經典文獻性質略說第六章 秦漢出土簡帛禮類文獻與兩周禮典研究第一節 論馬王堆漢墓《喪服圖》題記所反映的“本服”觀念第二節 “陽春白雪”“下里巴人”古曲定名新證第七章 古代發現的出土文獻與兩周禮典文獻研究第一節 《穆天子傳》禮典禮類簡述第二節 《周穆王盛姬死事》中的周代王后喪禮主要參考文獻後 記
徐淵,男,浙江鄞縣人,出生於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現爲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任同濟大學經學研究院副院長、中華孔子學會經學研究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上海儒學研究會理事。任《現代儒學》《春秋學研究》編委。中國訓詁學研究會、中國先秦史學會會員。著有《兩周秦漢禮典相關出土文獻考疑》《〈儀禮·喪服〉服敘變除圖釋》,整理古籍杜預《春秋釋例》、鄭玄《禮記注》等,參與點校《春秋公羊禮疏(外五種)》(獲華東地區古籍整理二等獎)。執行主編《十三經漢魏古注叢書》。發表學術論文三十餘篇,承擔國家社科基金等各類項目多項。圖書簡介本書從兩周禮典研究的角度出發,首先界定了出土文獻類禮典研究文獻與考古類禮典研究資料的基本區別,進而對禮典相關出土文獻做了分類,將目前已經出土的與禮典研究密切相關的文獻分爲六個大類。通過對這幾類出土文獻中禮典相關內容的深入分析,揭示利用不同種類出土文獻研究禮典的普遍原則和具體方法。將研究禮典相關出土文獻共同的普遍原則與研究不同屬性出土文獻的具體方法結合起來,應用到一個個具體的出土文獻禮典研究案例中去,以此檢討這些原則和方法的長處和局限。本書梳理了目前已經取得的出土文獻與兩周禮典研究的成果,並利用這些成果推進了對傳統禮典研究的討論。同時,本書還試圖利用傳統禮學的知識體系對出土文獻的字詞釋讀和文本整理提出新的設想,進而討論相關出土文獻的性質與成書過程。目錄前 言第一章 緒論第二章 兩周青銅器銘文與兩周禮典研究第一節 商晚西周出土文獻與兩周禮典研究概説第二節 釋讀錯誤引起誤收或失收青銅器銘文涉禮文獻第三節 青銅器銘文涉“禮”與涉“事”混淆的情況第四節 涉禮標準泛化引起誤收涉禮青銅器銘文文獻第五節 從時代性看祭祀禮類金文文獻的特點第六節 青銅器銘文涉禮但却没有對應禮典詞彙造成的失收第七節 “大叔”在先秦文獻中的特殊内涵第三章 出土戰國書類竹書文獻與兩周禮典研究第一節 郭店楚簡《六德》“爲父絶君”句析義第二節 上博簡《天子建州》與天子諸侯饗禮第三節 上博簡《鄭子家喪》所反映的春秋時代刑餘罪人喪葬儀式第四節 從清華簡《耆夜》飲至禮典推測其成書年代第五節 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篇涉禮字詞考釋第四章 春秋戰國出土器物文飾圖像與兩周禮典研究第一節 包山二號楚墓妝奩漆繪“昏禮親迎儀節圖”考第二節 射禮禮典與嵌錯刻紋銅器圖案辨誤第五章 戰國楚地出土卜筮祭禱簡與兩周禮典研究第一節 包山二號楚墓祭禱簡祭禮餘義淺述第二節 楚祭禱簡不具有祭禮禮典經典文獻性質略說第六章 秦漢出土簡帛禮類文獻與兩周禮典研究第一節 論馬王堆漢墓《喪服圖》題記所反映的“本服”觀念第二節 “陽春白雪”“下里巴人”古曲定名新證第七章 古代發現的出土文獻與兩周禮典文獻研究第一節 《穆天子傳》禮典禮類簡述第二節 《周穆王盛姬死事》中的周代王后喪禮主要參考文獻後 記转载自公众号“燕园礼学”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汉语研究与社会应用实验室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