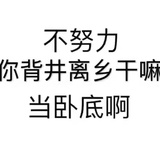《中國古典學》第五卷卷首語:
再談中國古典學的構建
文 / 黃德寬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一 引言
建設“中國古典學”或“重建中國古典學”,是近年來我國學術界關注的熱門話題之一。有關高校和單位在推進“古典學”研究、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和機構設置等方面開展了不少工作。(徐正英《扎實推進“中國古典學”學科建設》,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杜曉勤主編《中國古典學》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7-8頁。中國人民大學特設的“中國古典學”(050111T),已列入2024年教育部發佈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領域,裘錫圭(2000、2013)、林澐(2007)、劉釗(2007)等都討論過中國古典學重建及相關問題。“重建中國古典學”還被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列為國家“2011計畫”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的重點方向,編纂出版了《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論集》《出土文獻與中國古典學》等論著。(裘錫圭《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出土文獻》第四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劉釗、陳家寧《論中國古典學的重建》,《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論集》《出土文獻與中國古典學》,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2017年,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召開第一屆古典學國際研討會,專設一場討論中國古典學構建的圓桌會議,並於2020年正式創刊了《中國古典學》集刊。(在本次會議上,英國牛津大學聖安學院羅伯特·恰德(Robert L.Chard)教授以及國內學者徐正英、孫玉文、廖可斌、劉玉才等圍繞中西古典學關係、中國古典學建設等問題發表意見並展開討論,參見《北京大學第一屆古典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大學,2017年;《中國古典學》(第一卷)。)《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論集》一書編纂說明表示,論集的編纂是“為配合‘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學術研究的開展”;《中國古典學》創刊號發刊詞則明確提出:“中國古典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編纂《中國古典學》是為了“共同建設中國古典學的學科體系”。這些都顯示,“中國古典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關於“古典學”的討論,主要涉及兩個不同的學術領域:一是世界古代史和西方古典學研究領域,二是中國古代典籍、古文字和出土文獻以及中國歷史文化研究領域。前者關注的是我國關於西方古典學的研究和學科建設問題,後者則是根據自身學科發展的需要提出中國古典學學科的建設問題。雖然“古典學”概念的提出,受到西方古典學的影響,但中、西古典學各有自身的歷史淵源、研究對象和關注的問題。(《中國古典學》創刊號《發刊辭》宣稱:“‘中國古典學’中的‘古典學’一詞借自西方學術界。在西方,‘古典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學問,指對古希臘羅馬經典文獻的研究。”發刊辭還簡略概述了中、西古典學各自的研究基礎、核心問題和涉及的主要研究領域。)中國古典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提出,對建設我國人文學科體系是很有意義的。但是,由於參與討論的學者立足於不同的學科背景和學術取向,在中國古典學學科內涵、建設目標以及如何建設等基本問題上,還存在著較大的認識分歧,有必要將相關研究和討論持續下去,引向深入,儘可能地在學術界形成共識,以推進中國古典學的建設和發展。因此,在研究新出楚簡《詩經·召南·騶虞》詩闡釋問題時,筆者對當代中國古典學的構建及其可能路徑也提出了一些意見。(黃德寬《楚簡〈詩·召南·騶虞〉與上古虞衡制度——兼論當代中國古典學的構建》,《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12期。這篇文章是根據筆者2017年在北京大學第一屆古典學國際研討會上所作大會報告修改而成,因此,撰寫本文的目的就是通過個案研究探討中國古典學的構建問題。)由於該文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只是“兼論”而已,語焉不詳,故撰此文,以就教於各位同仁。
二 中國古典學的學科內涵
中國古典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建設,首先應該明確其學科內涵。中國古典學學科內涵的確定,涉及學科研究對象、主要問題、知識體系以及研究目的和方法等不同方面。經過梳理中國古典研究的歷史,與西方古典學進行比較分析,有多位學者已認識到:只有明確中國古典學學科內涵這一前提,才能闡明古典學建立的必要性並確立其在現代學科體系中的定位,把握其建設的重點和方向,取得預期的建設成效。(参看徐正英《紮實推進“中國古典學”學科建設》、廖可斌《借用、借鑒,還是另起爐灶——關於建立中國古典學的一些思考》、劉玉才《中國古典學的建構芻議》等文的討論,見《中國古典學》第一卷,中華書局,2020年。)
在中國古典學相關的研究中,涉及學科內涵的界定和表述大都較為簡單,學術界的認識也各有不同。關於何謂“中國古典學”,各家就有不同的表述,如林澐(2007)認為:“‘古典學’是指研究古書和古史的學問。這門學問在中國有很悠久的歷史。”“從古史辨派開創了疑古時代之後,中國的古典學,實際上就逐步進入了疑古和釋古並重的古史重建時期。這種重建是以對史料的嚴格審查為基礎,把古文獻和考古資料融會貫通而進行的。”(林澐《真該走出疑古時代嗎?——對當前中國古典學取向的看法》,《史學集刊》2007年第3期;收入《林澐文集·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68、280頁。)裘錫圭(2013)主張:“中國‘古典學’,應該指對於作為中華文明源頭的先秦典籍(或許還應加上與先秦典籍關係特別密切的一些漢代的書,如《史記》先秦部分、《淮南子》《說苑》《新序》《黃帝內經》《九章算術》等)的整理和研究,似乎也未嘗不可以把‘古典學’的‘古典’就按字面理解為‘上古的典籍’。”先秦典籍的整理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內容:“搜集、復原、著錄、校勘、注釋解讀以及對古書的真偽、年代、作者、編者、產生地域、資料的來源和價值、體例和源流的研究。”(裘錫圭《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出土文獻》第四輯;收入《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論集》,第13、14、15頁。)劉釗、陳家寧(2007)認為:“中國古典學可以被看作國學的一個分支,即研究漢代以前(包括漢代)中國古代文明的學問。”而“國學就是研究清代以前(包括清代)中國古代文明的學問。”中國古典學的“研究內容是‘國學’研究內容的前半段”,相當於李學勤所稱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劉釗、陳家寧《論中國古典學的重建》,《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論集》,第41、42頁。按:李學勤曾說:“我自知研究能力有限,所及範圍只中國古代文明前面一段,即自文明起源到漢代初年。”(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自序》,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頁))徐正英(2020)則認為:“既然是‘古典學’,就應該像西方‘古典學’那樣把握兩點:一是‘古’,二是‘典’。具體而言,就是在學好古代漢語的基礎上運用該語言工具闡釋中國早期經典、探討中國早期文明智慧。時段劃分則當以先秦經典為重點,延至兩漢時段,不宜再往下延。”廖可斌(2020)讚成裘錫圭的意見,主張把中國古典學作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一個分支”,“借鑒西方古典學的研究方法,以對出土文獻和文物、稀見早期文獻以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文獻、文化的研究為主,旁及相關領域,整合對中國古代文化中被掩埋、被遺忘的部分的研究,建立一門中國古典學。用這個概念可以把上述研究領域統一起來,它既相對寬廣,又有比較明確的邊界限定。”(廖可斌說他所據裘錫圭的意見,出自戴燕《陟彼景山》(中華書局,2017年)所刊裘錫圭教授《古典學的重建》訪談錄,見《借用、借鑒,還是另起爐灶——關於建立中國古典學的一些思考》,《中國古典學》第一卷,第26頁。)孫玉文(2020)認為:“中國古典學,就是對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的中國古代典籍進行研究的一門學問。當今流傳‘國學’這一術語,我所理解的‘國學’,跟這裡‘中國古典學’內涵和外延一致。我所謂的中國古典學,就是我所理解的國學。”(孫玉文《略談中國古典學》,《中國古典學》第一卷,第12-13頁,2020年;《“中國古典學”之我見》,《江蘇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
各家之說基於不同的學科和學術背景,既有一些共同的認識,也有各自不同的主張,分歧是明顯的。綜合各家意見,如下方面可看作基本共識:中國古典學是以古代典籍(古書)的整理研究為基本任務,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傳統,建設中國古典學應遵循中國古典研究的傳統,借鑒西方古典學的某些理論和方法。各家的分歧則主要表現在:(1)對“古代典籍”的時代劃分意見不一致,有“先秦”(裘錫圭2013)、“先秦秦漢(包括漢代)”(劉釗等2007)、“先秦兩漢”(徐正英2020)、“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孫玉文2020)等不同;(2)關於研究任務與學科屬性認識的差異,有“研究古書與古史”(林澐2007)、“先秦典籍的整理研究”(裘錫圭2013)、“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前半段)”(劉釗等2007)、“闡釋中國早期經典、探討中國早期文明智慧”的研究(徐正英2020)、“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分支)”(廖可斌2020)、“中國古代典籍研究”即“國學”研究(孫玉文2020),等等。這些不同的表述反映了各家對中國古典學學科內涵、研究任務和研究目的等方面存在著不盡相同的認識。
從研究對象來看,將中國古典學限定在先秦或先秦秦漢典籍(經典)的整理研究較有代表性,這是對古典學之“古典”含義的主流看法;將兩漢以後直到清帝退位以前的整個中國古代典籍都作為研究對象則顯得過於寬泛,只是少數人的主張。從研究內容來看,裘錫圭(2013)將古典學主要限定在先秦典籍文本的整理及相關問題的研究,並強調“沒有必要把先秦漢語漢字和先秦時代各個方面的研究都從相關學科裡分割開來納入古典學的範圍”。徐正英(2020)認為:“‘古典學’的任務則主要側重於對經典文本深度闡釋基礎上的文明智慧發掘”,應該與“國學”“傳統經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之間劃清邊界。劉玉才(2020)指出:古典學的“內容不能是現有專業領域的簡單歸併,而是貫徹以傳統小學為基礎,以文本研究為方法,致力揭示古典之學的思想核心及其在文學、藝術層面的呈現”。這些意見都是對古典學研究內容較為謹嚴的論述。至於將古典學表述為“研究古籍與古史” 或“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分支)”“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等,則使得古典學自身的學科內涵和屬性難以把握。如果將古典學限定為“古書與古史”研究,古典學與古代文獻學、歷史學學科之間的界限就變得模糊;而“古代歷史文化”“古代文明”研究則是涉及多學科、含義寬泛的學術研究領域,不是嚴格意義的學科概念,直接用來限定“古典學”,對釐清古典學的學科內涵和邊界並無助益。如劉釗等(2007)立足於古典學即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談到考古新發現對中國古典學諸學科的影響時,將古代文明起源和發展、哲學史、思想史、宗教學、語言學、文學史、民族學等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和學科都囊括在“中國古典學諸學科”之下,“中國古典學”似乎成為一個可以涵蓋各相關人文學科的大學科門類。“國學即中國古典學”是近年來頗有影響的看法,甚至連研究西方古典學的學者也有這樣的意見。(如南开大学世界史研究著名專家、西方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王敦書(1999)曾說:“中國是東方文明古國,具有輝煌的國學亦即中國古典學的研究傳統。”見王敦書《古典历史研究史·初版序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按:晏紹祥《古典历史研究史》一書,1999年由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初版。)眾所周知,“國學”一名的產生有其特殊的歷史緣由,從來都不是一個學科概念,其內涵和外延難以限定,而且從來就沒有納入現代學科體系之中。(錢穆曾說:“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其範圍所及,何者應列為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見錢氏所著《國學概論·弁言》,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頁。按:該書初稿完成於1926—1928年間,商務印書館1956年再版,1997年新一版。)前些年有些學者倡導建立“國學”學科,但引發學術界較大爭議,因而有學者主張以“中國古典學”來定義“國學”,以便確立“國學”的學科地位。(朱漢民曾在岳麓書院舉辦“國學學科問題會講”,邀請林慶彰、姜廣輝、李清良、吳仰湘、鄧洪波等討論“國學”與“中國古典學”問題,提出“國學即中國古典學”,目的就是“以‘中國古典學’來定義原來的‘國學’ ”,以推進“國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建設。見《光明日報》2010年10月20日“國學版”。)如果以並非學科概念的“國學”來定義“中國古典學”,不僅不能科學限定中國古典學,反而使得中國古典學學科內涵泛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實際上是消解了其學科屬性,有可能將中國古典學研究引向誤區。由此可見,以學科定位尚沒能解決的“國學”來定義“中國古典學”,或通過建立“中國古典學”學科來確定“國學”在現代學科體系中的定位,不僅在學理上而且在實踐中都會陷入難以擺脫的困境。
三 中國古典學學科建設的實踐
在開展古典學相關問題的研究和討論的同時,中國古典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建設也在積極推進。在中國古典學學科建設的實踐中,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北京大學中文系具有代表性。據徐正英(2020)介紹,2010年人大文學院創辦“古典學本科實驗班”,2014年設立“古典學”二級學科碩士、博士授權點,包括“中國古典學”“西方古典學”兩個研究方向,在現有學科體系中開始了構建“古典學”學科和開展古典學教育的實踐。北大中文系2016年打破古代漢語、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等專業之間的壁壘,以“三古”專業為基礎構建跨學科“中國古典學” 學科平臺。(見《中國古典學》第一卷《發刊辭》。)兩校古典學學科建設的實踐,體現了他們對中國古典學學科內涵的理解和建設目標的追求,是中國古典學建設值得關注的樣本。
2017年中國人民大學為打造“古典學學科”,以國學院為依託整合成立了“一體兩面”的辦學實體“古典學院”,其目的也“是為‘國學學科’爭取合法地位、登上‘戶口’。”(徐正英2020)人大“古典學學科”與“國學學科”的關聯,實際上體現了對中國古典學學科定位的認識。2022年,人大國學院烏雲畢力格、吳洋撰文闡述國學院建設中國古典學的一些設想,涉及中國古典學的名稱、時段、研究領域、方法論、學科建設等方面,主張秉持“大國學”以及“融貫中外文明”的交叉學科理念,提出“‘中國古典學’這一概念應該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對於中國古典’的學術研究,這直接延續了‘大國學’的理念;二是‘中國的古典學研究’,這有利於學科建設和融貫中外文明。”(烏雲畢力格、吳洋《建設中國古典學的一些設想》,《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11月17日。)雖然文章沒能展開充分的論述,但也較為全面地表達了作者對中國古典學學科內涵的認識和基本建設思路。
北大中文系構建“中國古典學”跨學科平臺,立足於研究中國古代人文經典作品,強調由古典語文切入,以文本考察為核心,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中國古典語文學、古典文獻學和古代文學三個方面,並將古典學術史、古典藝術史作為學科分支。(見《中國古典學》第一卷《發刊辭》。)《中國古典學》創刊以來各卷所發表的論文基本體現了以上範圍和古典學學科的建設宗旨。
如果能全面、深入比較分析兩家代表性高校“古典學”學科建設情況,對彼此關於古典學學科內涵的認識、建設思路和目標追求將會有更加准確的判斷。總體來看,兩校對中國古典學的認識及如何建設等方面差異明顯,各自也都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在我們看來,秉持“大國學”理念,除傳統經史子集的研究之外,把邊疆史地、民族語言文字、宗教人類學、考古文物乃至其他國家古代文明的研究都納入中國古典學的研究領域,儘管立意高遠,建設目標宏偉,但這樣的“中國古典學”建設思路在實際推進過程中難免會面臨種種困難。在中國古典語文學、古典文獻學和古代文學“三古”基礎上建設“中國古典學”,不僅體現了中國古典研究深厚的學術傳統,而且也有著較為充分的學理依據,但卻面臨著如何處理中國古典學與這幾個學科之間的關係、“跨學科”建設領域如何確定、古典學自身學科內涵和建設目標如何設立等問題,這些問題如不能得到合理解決,這樣的“中國古典學”建設也有可能難以實現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建設目標。
當然,中國古典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應該如何建設,並無先例可循,目前尚處於探索階段,因此,學術界應進一步開展相關學術研討,鼓勵不同建設單位結合自身學科基礎大膽嘗試,開展積極的建設實踐。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認為還是要立足於中國古典研究的傳統,從學科內涵的界定出發,吸收學術界對相關問題研究的成果,在諸如古典學研究的核心內容(領域)、時段限定、研究方法和目標等基本問題上盡可能凝聚共識,在正確理論指導下來開展中國古典學學科建設實踐,這樣才有可能取得更好的建設成效。與此同時,我們還要重視借鑒西方古典學研究和教育的歷史經驗,科學設計和規劃中國古典學學科建設的路徑和未來發展。Robert L. Chard認為:“中國和西方在古代階段有很多相同之處,可以互通有無的領域遠比我們現在所探討的範圍要大。中國建立‘中國古典學’這一新學科的學術價值將會遠遠超過現有學科,它可以擴展學術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並且促使學者將中國古代文化和遺產方面的研究與當代教育相結合。而中國和西方的‘古典學’專業有很多相似之處,其中很多觀點值得互相借鑒。”(Robert L.Chard《談“古典學”》,李卿蔚整理,劉玉才審定,《中國古典學》第一卷,第1頁。)Robert L. Chard的意見是非常中肯的,西方古典學在研究領域、研究方法、古典教育和學科建設的許多方面,對中國古典學學科建設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四 關於構建中國古典學的三個維度
綜合分析學術界關於中國古典學研究和建設的實踐,我們對中國古典學的構建有如下看法:
我們認為,以先秦時期元典性文獻和上古文明為中國古典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和基本任務是非常恰當的。這一點與西方古典學以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文獻和古典文明研究為根本任務頗為相似。雖然對整個中國古代典籍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任務,但那不是中國古典學學科所能全部包含的。明確了中國古典學研究的對象和範圍,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結合起來比勘稽考,從“文字”“文本”和“文化”等維度入手開展綜合性整體研究,也就成為當代中國古典學構建的一種路徑選擇。(黃德寬《楚簡<詩·召南·騶虞> 與上古虞衡制度——兼論當代中國古典學的構建》,《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12期。)
這段文字表達了我們對構建中國古典學的基本看法,下面做一些補充說明。一是關於中國古典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和基本任務問題。我們所謂“先秦時期元典性文獻”,也即裘錫圭(2013)“作為中華文明源頭的先秦文獻”。“元典性文獻”,指先秦時期原創的作為中華文明源頭的基礎文獻,不僅指歷代公認的儒家經典、諸子百家,還包括先秦時期所有與中華文明有關的文字記錄。同時,兩漢以降,先秦元典性文獻的傳承傳播以及歷代整理研究和闡釋成果,體現了先秦元典性文獻對中華歷史文明傳承、演進的深遠影響,也應作為中國古典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先秦是中華文明形成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古典學以產生於這一時期的元典性文獻為主要研究對象就抓住了根本。關於“上古文明”之“上古”,是一個限定並不嚴格的時段概念。中華文明從文字萌芽的“傳說時代”到有文字記載的“狹義的歷史時代”,經歷了漫長的持續不斷的沿革和歷史發展。(關於“傳說時代”“狹義的歷史時代”,參看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20頁。)我們所說的“上古文明”,主要指處於中華文明發展史上關鍵時期的先秦文明。(關於“先秦”的這一時段的限定,《中華大典·先秦總部》提要有如下表述:“本總部所涉及的中國歷史,約起公元前二十六世紀,迄公元前二二一年秦朝建立,共約二千四百年。在這一時段中,中國經歷了五帝、夏、商和周(西周、東周)四個階段。”見《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之《先秦總部》(編纂人員:錢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頁。)中國古典學的主要任務也就是探索從中華文明曙光初現的傳說時代到有文字記錄的夏、商、周(西周、東周)時代的文明。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是一個含義廣泛的學術研究領域,作為中國古典學基本任務的“上古文明”研究,主要指著重於以先秦元典性文獻為基礎、結合考古發現的先秦文明研究,與一般意義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既密切相關又有所區別。具體說來,就是從“文字”“文本”“文化”三個維度開展先秦典籍與上古文明的整體性研究。
二是關於“文字”“文本”“文化”三個維度的問題。“文字”是文獻形成的基礎,我們這裡所說的“文字”指的是先秦古文字及其記錄的上古漢語。文字是中華文明最為重要的載體,先秦時期典籍的形成、傳承都依賴於文字的發明和運用。中國古典學研究必須從語言文字入手,只有藉助語言文字才能走進先秦典籍,進而探索上古文明。因此,古文字、上古漢語是從事中國古典學研究者的基本素養,這就如同西方古典學者必須通曉古希臘文和拉丁文一樣。與西方古典學不同的是,記載上古文明的漢語言文字延續至今而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這是中國古典學研究得天獨厚的優勢。值得注意的是,上古語言文字的古今演變使後世對先秦典籍釋讀變得困難,因此,中國古典學研究既要充分發揮語言文字古今延續性的優勢,也要留意古今語言文字演進對典籍訓釋的影響,在充分挖掘和利用傳統古典文獻研究積累的訓釋成果的同時,充分重視運用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的成果,以新材料和新成果檢視傳世文獻和傳統典籍的訓釋,在“文字”這個維度上為構建中國古典學奠定堅實的基礎。
“文本”是古代典籍文獻的存在形式,由文本稽考以揭示其負載的歷史文化內涵是古典學的不二法門。西方古典學對古希臘—羅馬手稿、抄本、銘刻文獻的蒐集、校勘、整理以及來源、流傳的研究,中國關於古代典籍文獻製作、傳承、整理、校勘、辨偽、輯佚和闡釋等研究,都可歸之於“文本”研究的範圍。“文本”研究是古典學研究的基本任務,也是構建中國古典學不可或缺的維度之一。我國古代典籍文本研究源遠流長,裘錫圭(2013)認為:春秋戰國時代孔子及其弟子的經學文獻整理和傳授、漢代對先秦以來典籍的全面整理都屬於傳統古典學的範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疑古派對古史、古書的質疑和辨偽,以及七十年代以來戰國秦漢出土文獻考古新發現所引發的關於古書真偽、年代、體例、源流、校勘、解讀等研究,是現代古典學的兩次“重建”。(裘錫圭《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出土文獻》第四輯;收入《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論集》,第15—17頁。)“古典學重建”,一方面是基於對先秦典籍文本整理研究應歸屬於古典學的認識,另一方面是由於戰國、秦漢先秦文獻抄本新發現帶來的巨大影響。因此,裘錫圭(2013)指出:“發展古典學已經成為時代的要求。我們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早已過時的傳統古典學,也不能接受那種疑古過了頭的古典學,必須進行古典學的重建。而古典學的重建是離不開出土文獻的。”(裘錫圭在《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一文編入《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論集》時加了幾條按語,說明本文所說古典學的範圍與西方的古典語文學(Classical Philology)比較接近,跟以我國全部古文獻爲研究對象的古典文獻學的關係,類似於古文字學跟一般文字學的關係,並提出:“隨著先秦典籍的戰國、秦漢抄本的不斷出土和相關研究的日漸深入,古典學獨立的必要性已日漸凸顯。”見《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論集》,第35頁。)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繼長沙馬王堆帛書、 臨沂銀雀山漢簡的考古發現,戰國簡本文獻多批次問世,不僅有傳世的《詩》《書》《禮》《易》《老子》等先秦元典文獻的戰國楚地抄本,而且還有多種未能傳世的先秦典籍佚文。(參看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2年;李學勤、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壹—拾叁)》,上海:中西書局,2010—2023年;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 (二),上海:中西書局,2019、2022年。)這些戰國秦漢出土文獻是考辨先秦古典文獻原貌及其傳承流變的一手資料,為構建中國古典學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文獻支持。古代典籍研究優良傳統的繼承發揚、出土文獻文本研究價值的充分發掘,成為當代中國古典學構建重要的文本基礎。
“文化”之所以作為古典學研究的維度之一,一方面,由於任何古典文獻的產生和流傳都與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密切相關,“文化”對古典文獻的釋讀具有決定性影響,“文字”的辨識、“文本”的釋讀都要盡可能地契合其產生和傳播的歷史文化場景;另一方面,古典學研究古典的目的,是為了複現那個時代的歷史與文化。在西方古典學者維拉莫威茲(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看來,古典學的本質是“希臘-羅馬文明研究”,“該學科的任務就是利用科學的方法來復活那已逝的世界”。他認為“由於我們要努力探詢的生活是渾然一體的,所以我們的科學方法也是渾然一體的。” ([德]維拉莫威茲《古典學的歷史》,陳恒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1頁。)儘管古典研究要完全做到與歷史場景的契合並“復活那已逝的世界”,幾乎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終極目標,但維拉莫威茲對古典學的本質和學科任務的闡述,啟發我們在古典研究中應該將“文化”確立為一個重要的維度,要從這個維度來考索先秦典籍產生和流傳的歷史文化背景,並最終落實到對上古文明形成、演進歷程及其發展規律的揭示和闡釋。為此,在“文化”這個維度上,中國古典學研究必然要充分利用現代考古新發現以及歷史學、語言學、文獻學等多學科知識、方法和成果,並以整體意識來闡釋古代典籍的文化內涵,努力揭示我國上古文明的形成歷史和發展情狀。
從“文字”“文本” “文化”三個維度研究先秦典籍,是我國歷代典籍研究的悠久傳統,前人所謂“說字解經義”“由小學而經學”之類的表述,實際上已蘊含了類似的思想。需要強調的是,古代典籍研究並非從“文字”到“文本”再到“文化”的簡單遞進過程,“文字”是“文本”產生的基礎,“文本”是“文字”的存在形態,典籍的整理研究往往是“文字”“文本”統觀,並非將二者截然分開;而“文化”要素則更是貫穿於古典研究的全過程,為“文字”“文本”分析確定歷史背景和闡釋依據,並將古典研究導向最終目標的實現。因此,古典學的“文字”“文本”研究,與文字學、語言學、古典文獻學等學科密切相關,但也有著自身不同任務和學科屬性;“文化”雖然關涉古代史、考古學、藝術史、文化人類學等相關學科,但古典研究只是對相關學科知識、方法和成果綜合運用的整體性研究,而不是將相關學科都納入古典學的範圍。我們認爲,從“文字”“文本”“文化”三個維度來闡釋古典學的要義,有助於將古典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區別開來。
“文字”“文本”“文化”三個維度相結合,可爲構建當代中國古典學提供一種路徑選擇。在構建當代中國古典學這一新興學科的過程中,一是要重視發掘傳統“小學”積累的豐厚成果,與當代古文字、上古漢語研究結合起來, 在“文字”這個維度上實現古今語言文字研究的貫通;二是要重視發揚古代文獻研究傳統並利用歷代形成的成果,與新發現的出土文獻研究結合起來,在“文本”這個維度上實現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研究的融通;三是要重視將先秦文獻的整理研究與上古文明的探索結合起來,在“文化”這個維度上,揭示先秦典籍與上古歷史文化的深層關係,探尋上古文明的歷史面貌、演進軌跡和發展規律,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開拓思想源泉。
作者簡介

黃德寛,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清華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兼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語言文學學部委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評審委員會語言學科召集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中國文字學會會長、中國文字博物館館長、國家“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和首席專家。
转载自公众号“中国古典学”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汉语研究与社会应用实验室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