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张隆溪教授出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这本华人用英语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中有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一节,谈的是魏晋之间的“竹林七贤”。但是,该节只提及五贤的姓名,没有说另外两贤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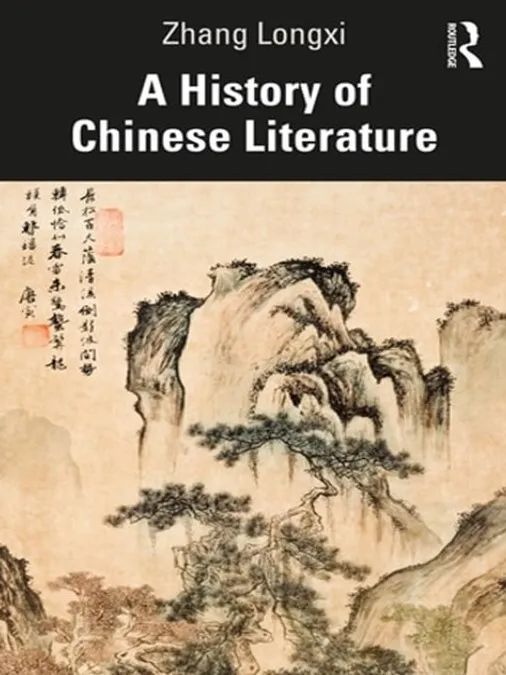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山涛、阮籍(210—263年)、刘伶、嵇康(223—263年)、向秀、阮咸、王戎。七人之中,阮、嵇的文学成就比较高。
张隆溪教授说:There appeared some men of letters with distinct characters who lived in seclusion, known as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among whom Ruan Ji and Ji Kang were the most well known. (p.60)
这句话中的who lived in seclusion, 是什么意思?有依据吗?“竹林七贤”是七人自称吗?他们居住在“竹林”吗?“竹林”是喻指七人隐居吗?七贤是特立独行“七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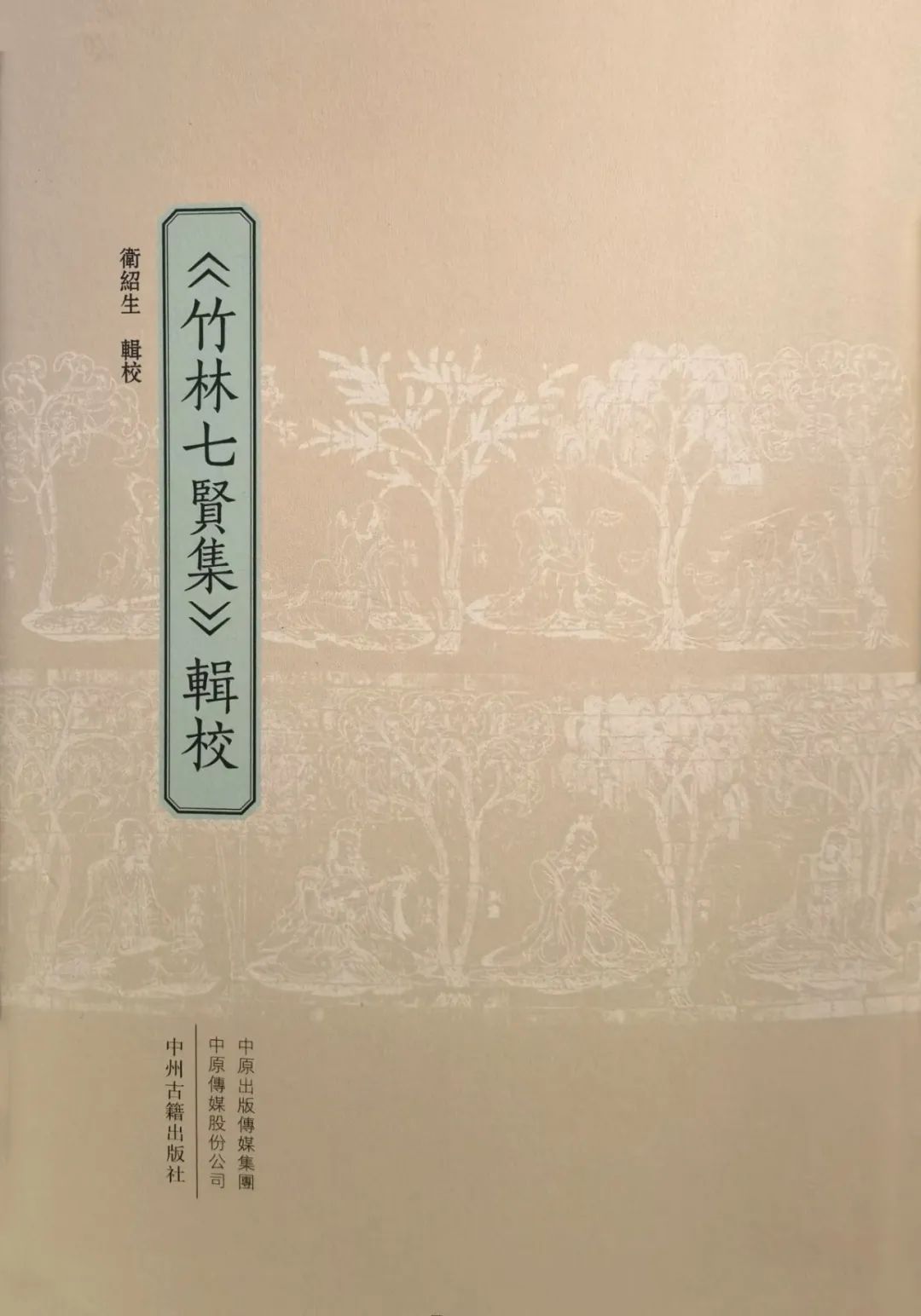
《竹林七贤集辑校》
竹林、“竹林之交”、“山林之游”
为什么“七贤”之前冠以“竹林”二字? 近人陈寅恪认为“竹林”是取自佛教“竹林精舍”中的前二字。但是,陈寅恪的说法不是定论。
有些学者据“竹林”而判定七人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里聚会 (卫绍生《竹林七贤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页16)。

卫绍生《竹林七贤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阮、嵇七人是否常常在竹林聚会?“集于竹林”就是“隐居于竹林”吗?
张隆溪教授所说的lived in seclusion, 应该就是“过隐居生活”。然而,山涛、阮籍、刘伶、嵇康、向秀、阮咸、王戎这七人,是隐者吗?
《晋书・山涛传》说山涛(205—283年)一遇阮籍,即为“竹林之交”(中华版《晋书》页1223),又说阮籍和王戎“为山林之游,戎尝后至”(中华书局版《晋书》页1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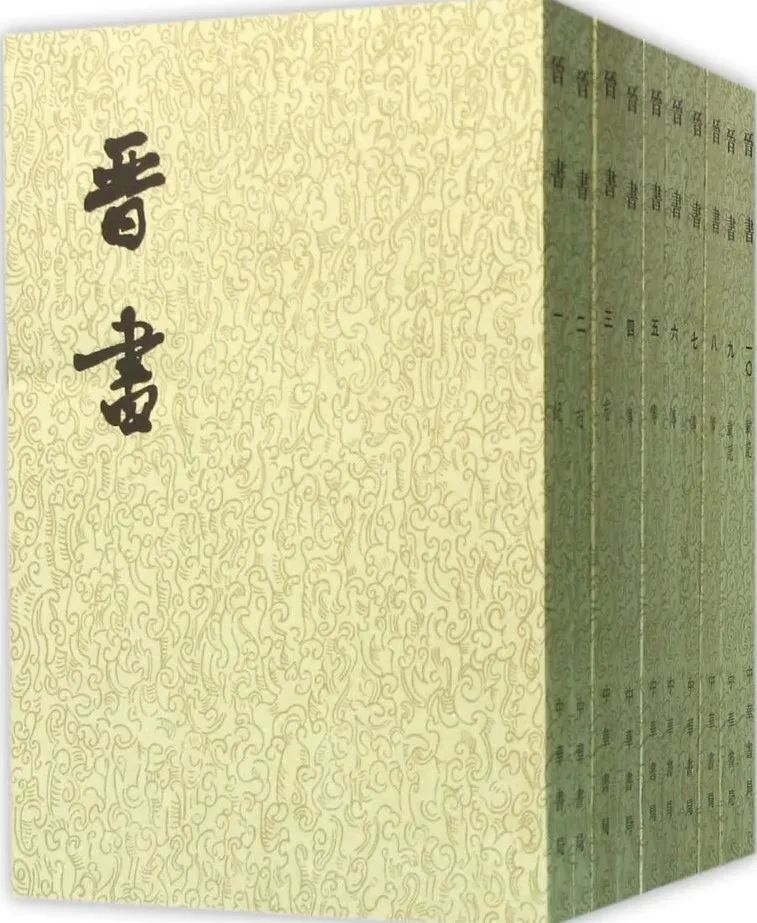
《晋书》
看来,至少王戎从山林之外赶到山林内。此外,“为山林之游”说明他们只是游。游,岂是居?
本来“竹林”这样的细节,不见得很重要,似乎无须深究,然而,如果认为“竹林”喻指七人lived in seclusion,那么,这seclusion就涉及七贤的人生态度(是否“隐居不仕”),值得一谈,况且隐逸是中国士人精神史上一个重要课题。
山涛、王戎当上大官还能隐居吗?
七贤之中,有人隐居不仕吗?近人徐公持指出:“〔山涛和王戎〕在司马昭时期都已做官……”(《阮籍与嵇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60。)既然山涛和王戎在司马昭辅政时就做了官,他们自然很难隐居。

徐公持《阮籍与嵇康》
山涛是七贤之中年龄较大的一位,他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太子少傅、左仆射。太康三年(282年),晋武帝下诏,升授山涛为司徒,位列三公,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晋书》页1227)。
山涛历任朝廷高官,因此,若说他 lived in seclusion (过隐士生活),有可能吗?山涛不但自己当官,还推举嵇康出来当官。
王戎(234—305年)袭其父的贞陵亭侯爵位,为司马昭之掾属,先后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晋武帝司马炎咸宁二年(276年)迁荆州刺史,四年改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晋书》页1232)。王戎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元康七年(297年)官拜司徒(《晋书》页1234)。
山、王之外,其他五人又如何?五人长时间过着隐士生活吗?笔者中学时稍涉魏晋史,记得阮籍又称为“阮步兵”,嵇康又称为“嵇中散”。其中“步兵”、“中散”都是职称。刘伶曾为健威参军,阮咸历任散骑侍郎。向秀也做过官(详下文)。
阮籍、嵇康什么时候当官?近人徐公持说,阮籍、嵇康都忠于曹魏,厌恶司马氏政权(《阮籍与嵇康》页13),那么,阮、嵇二人在司马氏当权时期(直到265年才由司马炎篡魏)就归隐山林吗?下面,我们讨论阮籍、嵇康的际遇和相关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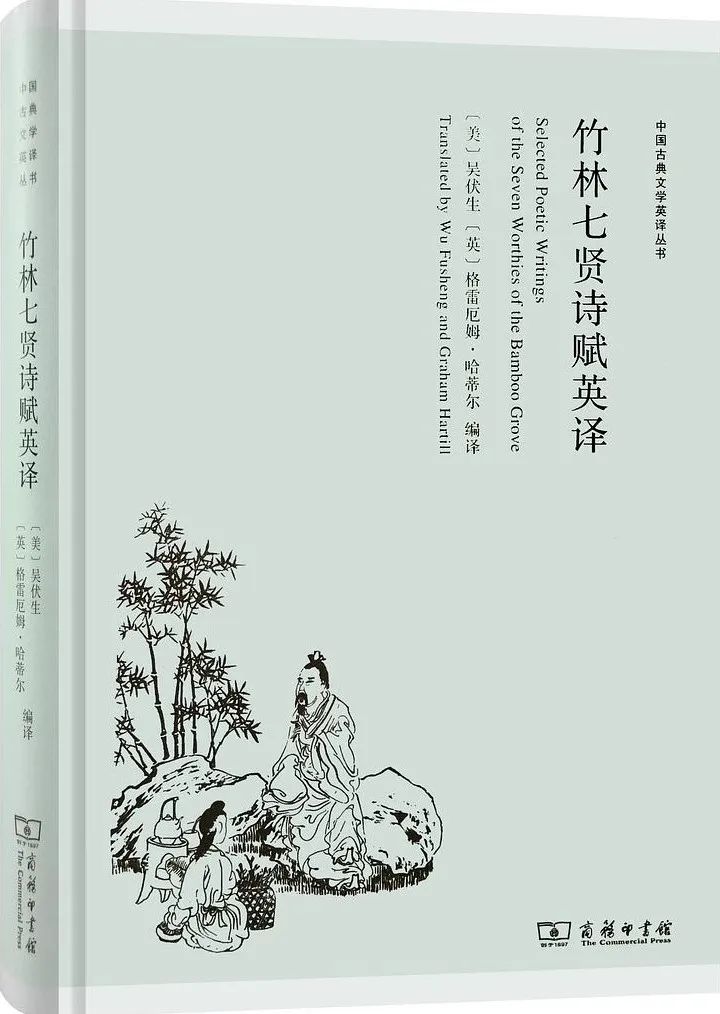
《竹林七贤诗赋英译》
自汉初淮南小山撰《招隐士》以来,“仕隐冲突”越来越激烈,因此,本文的论述取“出仕”为“隐”的对立面。
阮籍lived in seclusion?
阮籍的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籍初以门荫入仕,累迁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他的作品收录在《阮步兵集》之中。胡应麟说:“步兵虚无恬淡类庄、列。”(《诗薮》)刘熙载说:“阮步兵诗出于庄。”(《艺概》)
《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记载:“太尉蒋济闻其〔阮籍〕有隽才而辟之……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页1359-1360)
可见,阮籍在蒋济手下做官,又当过“尚书郎”“〔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曹髦,曹魏第四代皇帝)时期,甚至还获封为关内侯。曹髦死于260年,下距阮籍卒年263年只有3年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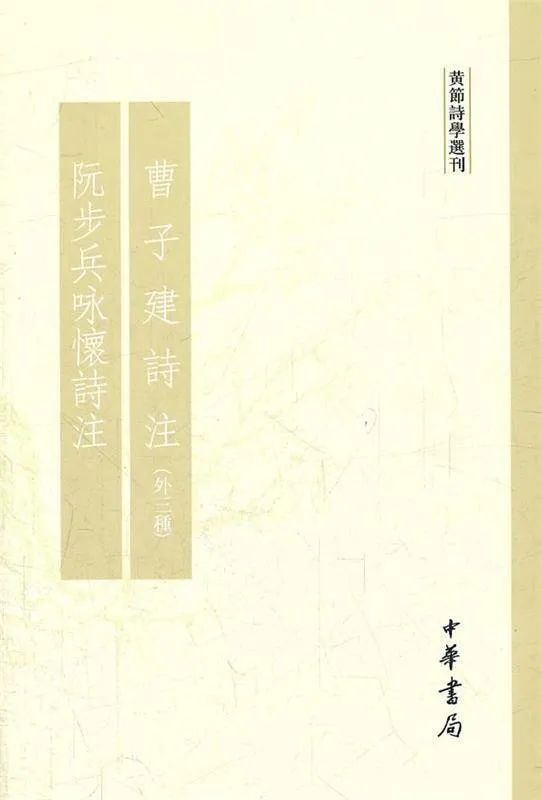
《阮步兵咏怀诗注》
据《晋书》本传,司马昭辅政时,阮籍曾对他表示过喜爱东平风土,司马昭即拜阮籍为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郭,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撰《东平赋》。《晋书》又记载阮籍“求为步兵校尉”,“朝宴必与焉”(《晋书》页1360)。在这种情况下,阮籍还能过隐居生活?
此外,司马昭要进封“晋公”,魏主下过诏书遂其所愿而司马昭假意谦让,须有人劝进,写劝进文的责任竟落到散骑常侍阮籍肩上,结果阮籍也写了出来(题为《为郑冲劝晋王笺》,见《文选》卷40)。
阮籍没有隐居,但是,他的诗作反映他对仕途心存疑虑,因为他知道高官厚禄都不可依恃。他留下《咏怀》诗八十二首(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页171),第六首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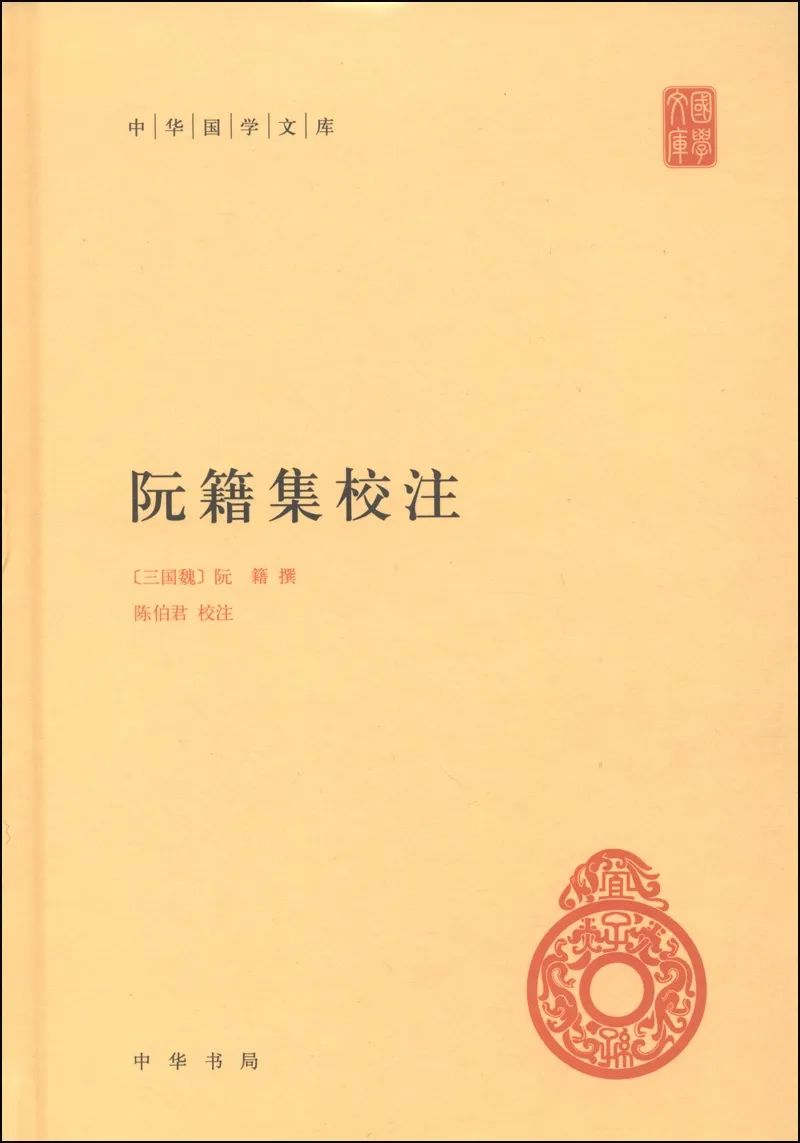
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
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
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宠禄”指朝廷的恩荣与俸禄。最后两句是说:当个普通百姓(“布衣”)可以平安到老,相反,在朝廷当官,风险高,不能确保安全。此诗或是讽喻党附司马氏之人(叶嘉莹《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中华书局,2017年,页102。)
再看《咏怀》其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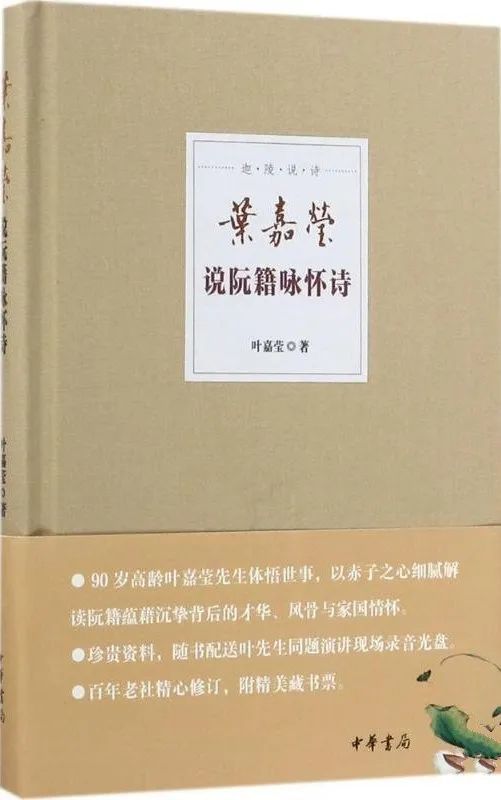
叶嘉莹《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中华书局2017年版。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
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
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说的是阮籍心中所愿(“松子”,可能指赤松子,他是古代传说中的仙人)。
此外,《咏怀》其三十四也有“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之句。诗句颇有陶渊明归农之风,但是,耕于东皋之阳只是阮籍之“愿”,他这愿望有没有付诸实践呢?
同样是归农之“愿”,陶渊明身体力行,他的《归园田居》其三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可见,陶渊明为“愿无违”而付出心力和劳力。

《陶渊明集笺注》,陶潛撰,袁行霈笺注,中华书局 2017年版。
嵇康lived in seclusion?
嵇康,字叔夜,三国时魏国人。嵇康当过朝廷的中散大夫,因此,后世又称他为“嵇中散”。南宋时期,陈振孙撰写《直斋书录解题》,录有“《嵇中散集》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有相同的记载(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页39和页520)。
嵇康因为替朋友吕安辩护(262年),被卷入吕安案件之中,受到牵连被捕下狱。他为此写了《幽愤诗》(《嵇康集校注》,页37),诗的最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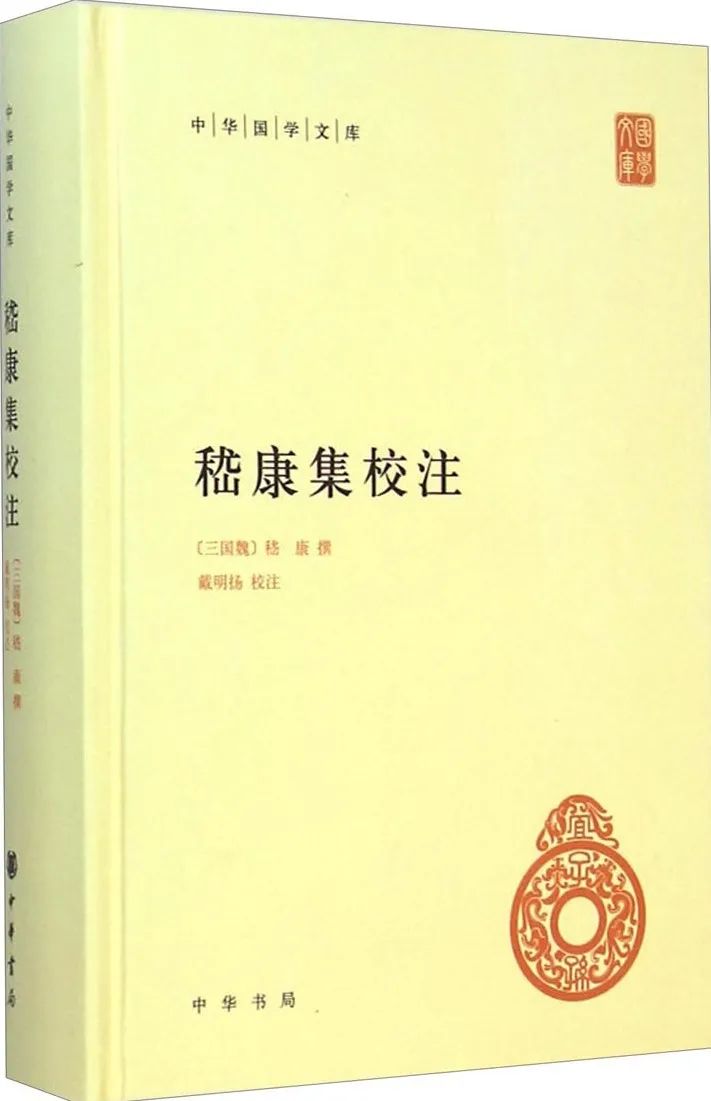
嵇康撰,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
庶勖将来,无馨无臭。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
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说的是嵇康自己幽于缧绁,只好寄望将来,一旦出狱,要学采薇的伯夷、叔齐那样隐居山野,颐性养寿。
可惜,嵇康没有机会“采薇山阿”了。不久他就被司马氏政权杀害了。钟会向司马昭建议杀掉嵇康,司马昭听从。
总之,嵇康被捕时不是隐士(他出面为吕安辩护、抨击吕安之弟),他也没有等到出狱当隐士之日。因此,如果说他lived in seclusion,真不知从何说起。
阮籍、嵇康有没有当过隐士? 据徐公持所说,阮、嵇的作品中流露出隐逸和神仙的观念。两人面对司马氏政权的虚伪和残暴,找不到光明的出路,又倾心于玄学,自然向往隐逸。 阮、嵇二人曾经到到苏门山拜访有名的隐士孙登,希望得到孙登的指点,但是孙登看出嵇康口头上“璞隐乐玄虚”,实际上不能忘情世事,因此冷待嵇康,而阮籍不是真正的隐士,因此孙登完全不理睬阮籍(《晋书・隐逸传》;徐公持《阮籍与嵇康》,页46)。
嵇康《幽愤诗》有一句“今愧孙登”(《晋书》页1373),是自惭未能如孙登的临别赠言那般调整心态、及早隐居,终致蹈祸入狱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商务印书馆, 2011年,页205)。

《中古文学史论》
“七贤”其实心态不一致,人生道路也不一样
有些人说竹林七贤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的竹林聚会。这说法,有历史依据吗?
房玄龄《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列出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之目,不包含山涛、王戎。山、王事迹见于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中华书局版页1223)。这似乎说明,王戎和山涛未必适合和前五人相提并论。历史上,王戎有逐利的恶名,连蝇头小利都要斤斤计较。
“竹林七贤”与“建安七子”不同。“建安七子”都是邺下文人,为曹魏政权办事,他们有邺宫西园之会,彼此赠答酬唱(何诗海《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155)。

《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
竹林七贤中,阮、嵇当过曹魏政权的官,山涛、王戎在司马氏政权当大官,刘伶当过建威参军,而向秀、阮籍也为司马政权效过力。向秀在嵇康遇害后,任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晋书》页1375)。竹林七贤没有七人同时在朝任职。
向秀在嵇康死后出仕,《世说新语・言语》记载: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向秀)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竹林七贤”处世态度不一,有时甚至是对立的,例如,山涛以吏部郎出缺为由,推荐嵇康出来做官,结果嵇康拒绝,还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原文见于中华书局版《晋书》页1370-1372。)昭明太子萧统将这文章编入《文选》第43卷。张隆溪教授书中也提及嵇康此信(p.62)。
世人往往将“嵇阮”并称,但是,南宋学者叶适(1150年—1223年)区隔嵇、阮二人,褒嵇而贬阮,他说:“籍得全于晋,是早附司马师,阴托其庇尔。史言‘礼法之士,嫉之如雠,赖司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马氏,未必能脱祸也。今《文选》载蒋济《劝进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何所不可?籍着论鄙世俗之士,以为犹虱处乎裩中,籍非委节于司马裩中乎?余观康尚不屈于锺会,肯卖魏而附晋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为‘嵇阮’,吾每为之太息也。”(《石林诗话》,见潘殊闲《叶梦得研究》,巴蜀书社, 2007年,页37 )。

《叶梦得研究》
简言之,叶适认为:嵇康“不屈”,而阮籍“附晋”,嵇阮二人的处世态度大不相同。所谓“竹林七贤”,可能只是个imagined community (Benedict Anderson, 1983)。
文学史书能否做到名副其实?
有些标榜“竹林七贤”的文学史书实际上没有讨论山涛、王戎、阮咸三贤的文学作品,可谓名实不相副。 张隆溪教授也没有论及山涛、王戎、阮咸的作品,只有一句话提到刘伶撰有“Ode to the Virtue of Wine” (p.62;当为刘伶的《酒德颂》)。王戎、阮咸两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获提及。这状况,是不是标题和内文不能相配?
王戎、阮咸,《晋史》本传未记二人有作品流传,而张隆溪教授声称王戎、阮咸为The other poets of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张教授怎知王戎、阮咸是 poets? 说是poets,有何依据?“贤”者,就是poets?没有这个道理吧。 如果史家将想象当成史实(facts)记载在史书中,妥当吗?
近几十年出版的文学史书,不少已经舍弃“竹林七贤”这个旧标签,没有“七贤”的题目,例如,民国二九年序本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只有“正始到永嘉”(页190),题目不标示“竹林七贤”。

《中国文学史新著》,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又例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有“建安七子与蔡琰”之目,不立“竹林七贤”之标题。台湾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相应的章节标题是“正始之音的双星——阮籍、嵇康”(2014年,上册,页261)。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着(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没有“竹林七贤”之目。阮籍、嵇康、向秀的作品放在“曹魏文学”一节加以讨论。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编第一章第五节也不列“竹林七贤”之目。第一章第五节名为“阮籍、嵇康与正始诗歌”(第二册,页45)。
张隆溪教授参考过上述两部文学史(复旦章骆、北大袁行霈),却标立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想必是自有主见,但是,张教授没有解说为什么。如果以“七人皆隐居”为由,能说得通吗?如果以“七人皆poets (诗人)”为由,能说得通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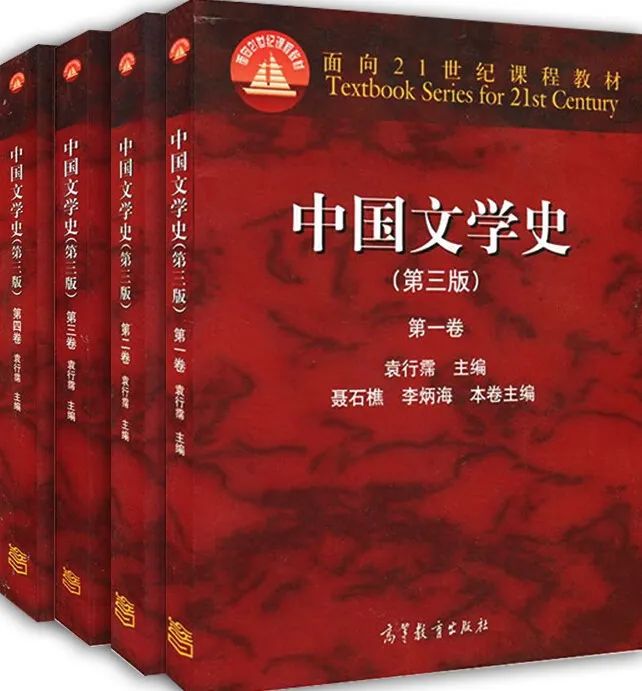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略论其他英文版中国文学史的论述
美国学者Victor Mair 主编的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pp.258—259 没有列出“竹林七贤”的题目,只在THE CHENG-SHIH PERIOD这一节提及阮籍和嵇康:The most famous poets of the period are Juan Chi (210–263) and Hsi K’ang (also pronounced Chi K’ang; 223–262)。换言之,这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正始时代”略论阮、嵇。
撰稿者(Robert J. Cutter)也指出七贤对司马氏政权的态度不同(different opinions regarding Ssu-ma rule)。Cutter 可能是考虑到山涛和王戎在司马氏政权当上大官。

梅维恒主编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2年版。
另一部英文版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之中有The Seven Worthies of the Bamboo Grove一节 (p.177)。撰稿人指出,“竹林七贤”可能不是七人在世时的称号,而是a fiction created several generations later。意思是:称号疑为后世人所拟。
论嵇康的段落里,剑桥版文学史提及嵇康撰有《琴赋》。这可能和撰稿人是David R. Knechtges有关(按:Knechtges似乎偏爱研究赋),也可能是因为七贤之中嵇康《琴赋》确实独特,因此值得在史书中记上一笔。
音乐理论是魏晋间讨论的一个热点:阮籍撰有《乐论》、嵇康撰有《声无哀乐论》,都是当时音乐美学的重要著作(参看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103)。嵇康和琴曲《广陵散》密切相关(p.182),而“广陵散绝”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憾事。

R. H. van Gulik, 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
关于嵇康与琴,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撰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n Essay in the Ideology of the Ch'in Ideology (Tokyo, 1941) 和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 (Tokyo, 1941) 二书。Hsi K'ang,就是“嵇康”,整个英文书名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翻译成中文就是《嵇康及其〈琴赋〉》。由此可见嵇康《琴赋》很受重视。
笔者认为,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突出人物和作品特点,这一部分比较接近“个性化的历史”。这样书写个人气质、感情、个人创造,比起老生常谈复述时代的影响(指文学的生成条件,例如:老庄的影响、清谈的流行)更有意味。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谁才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竹林七贤,是不是一个“文学集团”?
《晋书・嵇康传》说:“〔嵇康〕所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晋书》页1370)
所谓“神交”,应该是指嵇、阮、山三人不能见面或不能常常见面,只是在精神上彼此有契合之处。另外四人只是“豫其流”。一般词书解释“神交”:精神交往,不见面而相投合仰慕。

高智《六朝隐逸诗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版。
“竹林之游”的“游”反映七人不是隐居山林。也许有人认为他们的山林之游也算是“隐”,可是,真正的隐居生活恐怕不是群聚、宴游,《晋书・隐逸传》所记孙登事迹可以为证(参看Aat Vervoorn, Men of Cliffs and Caves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remitics Tradition to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0 第二章第七节“无条件隐逸”)。
《晋书・孙绰传》记载: 孙绰尝鄙山涛,而谓人曰:“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若以元礼门为龙津,则当点额暴鳞矣。”(《晋书》列传第二十六) 这反映山涛在处世方面露出过矛盾,所以孙绰才那样鄙视山涛。山涛进出官场,退完又进,像是个投机者。
山涛和阮、嵇,可能一度向往游仙,企慕隐逸、口说隐逸(lip service),但是,他们根本没有付诸实行。因此,“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殊荣落在南朝宋时期的陶潜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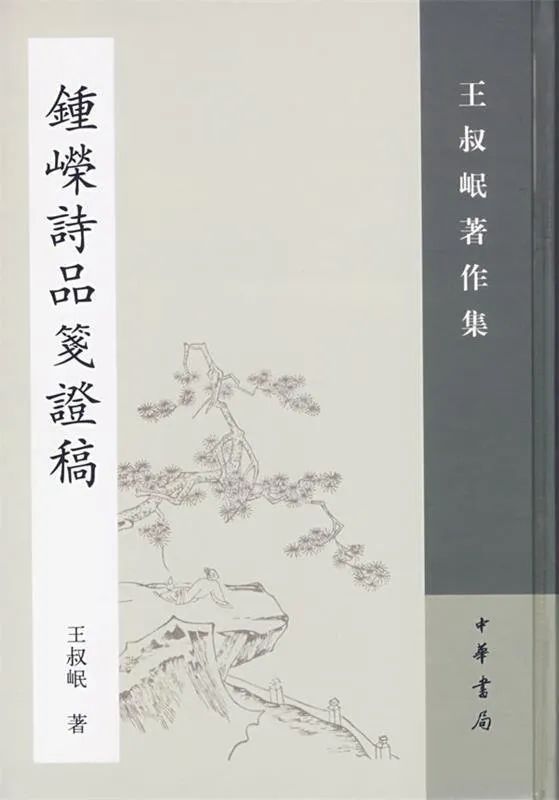
读过钟嵘《诗品》的学者,都会知道“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来历(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页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