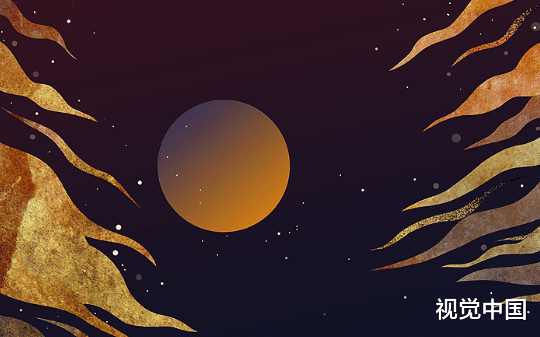简介:
“请皇上自重......”
他年少时顽劣,总不正经:“待宴散了,你领我回你坤宁宫可好,那日你与我亲热......我总惦记着,每每煽动我。”一会都歇不住便要用手碰碰她的手,这碰上了又不肯松开。
面朝百人,御上他面目严肃,可这话说得就是一登徒子不正经样。

精选片段:
朦胧睁眼。
稍稍有了意识,方察觉自己在河岸边儿上。
身上麻木不堪,半泡着水,四肢已然发白,似在这躺了一夜。
红日直直烘着,眼前昏沉,撑着爬起来,素色衣裙被染得处处泥黄,脚上的布鞋散了麻,是扣子不知落到哪里去了,别扭得紧。
泥岸南面百里尽是灌木树丛,了无人烟。
“我叫,我叫颜卿……陈颜卿。”
回春堂的药师,黄河水患流迫的孤女,还是相门掌上明珠......辗转万千——不记得,真的不记得......
头一阵阵发蒙。
四面绕高山,顶着炎日,她沿着干岸朝里迤逦徒步百余里,才有了人迹。
是一座破旧的避风亭。
她倚在树阴底下细瞧,方见那花间下正有一人偎在石桌旁饮茶。
分外清秀的侧颜。
皆说人有眼缘,有的人,只消一眼便心生欢喜。
那人举手投足间的温润在她看来就十分受用。
她呆愣着瞧。
忽觉肩头隐约有些痒,她伸手去挠。
摸着个毛毛赖赖一团,登时尽身一僵,扭头去看——竟是只黑得发亮的毛虫崽子。
顿时大叫。
惊呼引得那兀自吃茶的人亦是一愣,他瞧见她,起身走来。
歪在一边,她忙捡了根细枝一戳一戳的。
“你是谁?”也不顾陌生熟识,他先开口了。
她抬头。
这人挑着眉,傲娇得很。
“你是谁......”她愣愣。
“身上这样邋遢,真是碍眼得紧,怪不得这蜰子爬了来作弄你。”他一面说着,拾起枯叶儿往她肩上裹了这虫摆回枝桠里。
木讷望了望枝桠,埋头看看自己污迹斑斑的衣裙,挠挠肩嘀咕着:“管得宽……”
他瞥着她腕上瓷镯,低声喃喃:“不想果真又见着你了…”他扬眉笑道:“还是个泼毛。”
糊里糊涂,她懊恼回嘴:“你才是泼毛!”
“这才刚立春,你便穿得如此单薄?”说着便解了自己的斗篷。
他上前来将它披在她身上,斗篷有幽香,竟叫她舍不得推开,顾忌生疏,又将斗篷还予他,顿顿道:“我......我同你尚不熟稔,不消你的袍子,谢过了。”
他愣了愣,面上无甚表情,却走上前来,伸手将她面庞上几点灰尘拭去。
瞧着倒似几分情不自禁。
望着他的眉宇间,莫名红了耳根,手脚凌乱间竟将斗篷摁在他脸上,忙转过身去不敢看他。
以为她负气,他上前一步去,是要辩解:“你脸上有秽物,我将你.......”
一语未了,她便又打断:“脸上有灰是自个儿的事,不用你来。”
他手上一僵,默了半刻,稍显厌烦便把眼瞟别处,晓得了自己失态:“是我鬼迷了心窍,倒也——不稀罕你。”
这就不满,气鼓鼓的:“我也不稀罕你!”
思量着自己竟会痴馋一素不相识之人,挠了挠脑袋瓜子,心虚得很,还是开溜得好。
他追上来,拽住她的腕,张着两眼:“怎么,你要走?”
“你做什么?”
竟上下打量她。
“做什么,放开!”
见她紧张,惹得他来了兴致,戏弄道:“不放如何?”手上紧了紧力道儿,笑得仿个登徒子。
稍稍犯怵,她伸爪子掐了他的手背:“放手......”
指甲陷的愈深,他非但未怒,反笑细细的瞧着她,像个登徒子……
“你这人好生古怪,竟仍不撒手,仔细姑奶奶叫你哭。”她瞪眼望他,欲想涨些气势。
似找着了乐子,他笑得更欢:“泼毛就是泼毛,敢情还是个横主,小姑奶奶,我倒瞧瞧你拿什么叫我哭。”
管她叫横主,她便心中一横,抬腿用劲顶了他的子孙根。
他面上一僵,额头青筋显出,两手护着痛处,只觉腿要立不住:“泼毛……”
“这便是姑奶奶我的本事儿。”她悦心一笑:“告辞。”
————————————————
老爷子端坐在棕木椅上,短短一撮分叉的白山羊胡黏在下颚。他眯眼养神,神情怡然。
“喊琉璃阁那丫头来。”他道。
旁的姑姑应了声,快步出去,这将珠儿寻来。
丫头进来,福了福身子,委身道:“老爷,您有什么吩咐?”
他轻叹,闭上眼,似是养神,确是担忧:“你姊妹如何了?”
“回老爷,她仍这般昏睡着,不见醒来。”珠儿顿了顿:“大夫说,玉笙当是受了恫吓。”
他未睁眼,良久。
“去罢。”
“是。”
她提步方到门槛边,耳边是淡淡的声。
“在外头,一旦漏了风声,老夫断不会轻饶你们。”
“奴婢紧记。”
甚惶恐。
这一方,又传信来。
“老爷,太皇太后暗谕,召您进宫,商権要事。”
老爷子黄目深邃:“更衣,起车马。”
半吊在心的石,终算落下。
话说溜烟没溜成,扛着日头走了几里路没一人毛,又是饥又是渴,不承想半路杀出一咬金兄名为曹寅,把她半路给截了,原二人是一伙,一主一仆,寅为仆。寅道出她伤了他家主子,故拦了她的去路要她说个四五六。她自是讲不出理,毕竟自个儿险些断了人家香火,只好规规矩矩的给五花大绑回了回来慰问。
她强笑嫣然,:“伤......伤势可还重?”
他还在那石凳上坐着,悠闲着轻酌小酒:“怎么,不跑了?”
她尬笑:“您看...这大热天儿的是吧...能上哪去呢。”
说着,哪知她腹里传来咕噜声儿。
他仰头大笑:“你且饱腹了再跑也不迟。”
她一愣。
本无心闹趣,顿时恍然,倒是他一语惊醒梦中人,眼下自个儿啥也不知,啥也不会,就单单知道个大名儿。委实无甚可维生计之物,说去以名寻亲,只怕亲未寻着,人已成饿殍,瞧着眼前这人不若奸邪之辈,倒不如抓紧这稻草,混些银两,以防曝尸荒野。
悄咪着瞟了眼他腰间的布囊,嗯,够鼓。
“兄台,可否借我些碎子儿,吃口饭去。”她赔笑。
他不解,转问道:“你是一人在此?”
见时宜,她变作楚楚可怜模样,张嘴扯瞎话:“我……我是发水涝流迫来的孤女……如今……甚么也不记得了。”掩面泣涕:“几天没沾着个馒头了,我本冰肌玉骨,最是绝世一人,如今......如今饥黄面瘦......”
他又瞥了瞥她腕上瓷镯。
“大老爷,您也瞧得出来,我这身邋遢,瞧瞧,我这鞋,大脚趾都来见您了......”
“当真是孤女?”
“是。”可怜巴巴。
“跟我走吧。”
她一愣,偏过脑袋,瞪圆眼瞅着他:“一肚子坏水......”
他朗声大笑,问她:“你觊觎我兜里的钱财就不坏了?”
“有啥好笑的......”她在喉咙里嘀咕:“咧嘴王八小气鬼......”
“好了,正经的。”他一改面容,认真道:“想要银子,就跟我走。”
她不肯,埋着脑袋,杵在那。
“我是宫中当差的郎中,只近日出来走动走动。”他道:“不是人贩子。”
她不肯,杵在那。
朝兜里抓了把银子,在掌心里捣腾:“你若真是孤女,还这般穷酸落魄在这荒郊,也活不好,甚至活不了。”
她不肯,瞅着他手里的银子杵在那。
他挑眉望着她:“过时不候?”
......
天下哪有这好事,这人出手救济,还将她收留,好吃好住供起来。
怕是老天爷眷顾她。
她便也厚着脸皮尾随人家,挤进一客栈来住。
————
只是这人有些古怪。
这日她爬来房檐上,一个人玩儿。
她伸出俩指,在瓦上走:“你是谁呀。”
“我是陈颜卿!”又伸出另一只手。
“你为何在这?”
忧伤窘起了眉毛:“我不记得……”
这般惬意,委实像个傻十三。
兀自开心着,突觉有人在瞧自己。
她转眼看去,他站在底下,眼底占尽柔情,正盯着傻十三。
她呆呆望着他,红了脸。
他仰朝她伸出手来,温声道:“丫头。”
只觉莫名羞赧,躲了起来。
本说人在屋檐下,她已有心任凭差遣给他打杂来叫自己住得心安理得,本觉他多半缺个粗使丫头才留的自己。没想这几日来,他也从未遣过自己,倒是偶时邀她来院中品个小茶倒是有的。
几日来,他只有对她的好,不曾有不好,便不作多想,只需待得舒坦,不管那三七二十一。
而况,这日做了冗长的梦。
顿时醒来,鬓角还挂着泪花,梦已然忘却。身上渗出冷汗,拉了帷幔,下床来,这日午时小憩,只道一会儿看窗格外天色见晚,心下莫名得生出些惊惶来。
摸出了屋,曹寅一人在院里。
见了她,曹寅反道:“姑娘一人可还打紧?”
“不打紧,怎么?”
曹寅闻此,往四面扫了一圈:“那姑娘且回屋歇着,主子半日未归,在下去寻。”
颜卿一道跟了去,只怕他们跑了,将她一人撂下。
“瞧这月黑风高,不会是给豺狼刁去也难说。”
“这话不得乱说。”寅道。
“不是,你说这林子阴森森,毒蛇猛兽的不见得少,给啥玩意咬一口,指不定这会躺哪等回光返照呢。”
曹寅虚得慌:“姑娘……”
“你看,地上处处是深坑,摔了进去怕也不成事,至少得碎骨头。”
这曹寅也是一老实巴交的人,他心中焦灼:“主子吉人天相,不惧的。”
“咱们都找了这么一时,连个人毛都没有,你说半日未归,脚滑一跤栽河口里也说不准。”
他愠怒:“姑娘,主子待你如此,你却咒他。”
瞧他较真,她陪笑:“不不不,我揣测一二罢了。”
曹寅面色铁青,扔了火把子,走得愈快。
“好黑呐!”颜卿吓得直叫:“我怕鬼,你等等我。”一时慌了,连同背后渐生寒气,跌跌撞撞跟上去,被一木橛撂倒,崴了腿脚,擦破了皮,她又急着一瘸一拐爬起来:“不说还不成,等等我——”腿一痛,又摔了下去,干脆不管了,坐地上揉起脚踝来,瞪眼睛鼓腮帮子的,横竖也就一死,死了也不消受这人间罪。
曹寅想了想,又回头来。
见她摔在地上。
他把她拽起来,背在背上,她一吓:“你做什么,放开,赖皮头!”一面打骂,一面扯人家的耳朵。
曹寅实在难忍,冷声言:“托主子照料您,您安分些可好?”
她心下突生一丝温存。
瞅了瞅他,一改善容,温声道:“你主子对我甚好,我猜想......你那主子不是瞧上我了罢?”
寅不语。
“说来我闭月羞花,舒雅之至,自是教人一眼钟情,他倾心于我也是情理之中......”她厚着脸嘴叨叨。
寅不语。
“我才见他时,就觉投缘,他面目俊秀,瞧着亦有二文钱财,同我年纪相当,倘若他直白些对我,我亦是会从的......”她仍厚着脸嘴叨叨。
寅不语。
“只不晓得他可是衷情的人,他若肯悉心照料我,我便随他走南闯北……”
寅无奈,便言:“我诚然好奇姑娘的身份,竟会独自一人在这老林子。”
“我……我是孟津渡口泛滥的流民……”随口而出,不知何来,她皱眉思量:“我不记得……"
绕回客栈。
门前,一眼便看见他,背着手在院内。
听见脚步声,忙转过来,本要说些什么,见曹卿二人如此架势,脸色一沉打住了。
凉凉。
走来曹寅跟前,他讽道:“ 不晓得做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会儿竟如此亲热了。”
曹寅不敢抬头,一时语噎,傻里傻气,半晌哼出一句:“您说要照看......”
“照看到身上去了?”他似是不肯罢休。
曹寅仍不敢多言,他将折扇打开悠悠的扇着:“你两人竟如此不知羞辱。”
“姑娘伤了……”曹寅低声道。
“伤了?伤了面色如此红润?”他转过身来,看着她,笑道:“受伤好啊,我是郎中,我给你看,何用假惺惺的去勾引他。”
他走近,拽住她,扯了扯她的衣肩:“哪里伤了,我给你瞧瞧。”
只觉他句句话刺耳。
“放手。”她冷声,
他却也还是不甘示弱,拽着她的衣袖:“怎么?同我不熟稔,碰都碰不得,同他,便要投怀送抱?”他讥诮,语气古怪:“好一个贞洁烈女。”
受不得委屈,嫌他说话难听,她拔脚跑了。
他瞪着曹寅。
曹寅立时跪下,惶恐万分:“卑职同姑娘清白无私,只因昏时姑娘要同卑职寻您,路上不巧崴伤了脚......”他唯唯诺诺抬头望了他一眼,又埋下头道:“姑娘说——若您有意,她是愿跟您的...”
他眉间一动:“何由?”
“姑娘她......瞧出您的心意......她自述初见时投缘与您......”曹寅顿了顿·:“故您有意,姑娘她是肯的。”
用手中的折扇敲了敲曹寅的脑袋,他颇有些怨怪:“你这二愣子,支支吾吾的。”
语罢,几步出了院子,顺着小路跟上去。
步子急切,许是多年沉寂的心,如沐春风。
找见她时,她坐在杉树底下,在捏.弄泥巴。
竟在捏泥人。
明月吐光,丫头的样子,玲珑剔透。
他刹那间面红耳赤,心底兴奋渐生,她仍旧是她。
“我来陪你玩儿。”
她闻他声响,默不作声。
“我晓得你是正经本分姑娘,言语伤了你,自知有过……”
他坐下来,挪到她旁边。她斜睨了他一眼,搓了搓手上泥巴,厌嫌的挪开些。
他却兴致勃勃涎皮涎脸:“你别嫌我。”他伸手在她眼前晃晃:“莫要同我闹别扭,我不是有心的。”他微微皱眉,柔声道:“若你脚还疼,我替你看看。”
转过头来瞅了他一眼,心里边念叨他十足是个半大不大的毛孩子。
“你对曹寅说那话......可当真?”
她一怔,默了。
他又握了她的手,慌道:“那你有何顾忌?”
抽了手,也不望他,低头默不作声。
“若你怕此番有些轻浮,我们亲近些可好?”
她看他一眼:“我都不知你唤做什么。”
“叫我小玄子。”
“玄黄之玄,小玄子。”他亮着眼睛望她,顺着说:“我定是本分人,阿玛额娘走得早,留下我独自一人,因自幼与曹寅结识,大了便随曹寅一同去宫里当差,做了大夫。”
“我自小便略通医学,替人瞧病……”
她心中纠结,他一味任性,只当他是在胡闹,随口应了她:“我唯独记得名字......你喊我颜卿好了。”
“颜卿。”他定定望着她。
你说过会陪我——
————
月明星稀。
“主子,方才的信,说老祖宗来过乾清宫了。”
“怎么说。”
曹寅低眉,弱弱道:“老祖宗说,野够了怕是该回了。”
“就回吧。”
“这姑娘......”曹寅抬眼打量他面上颜色。
“随进宫。”
倒吸一口凉气,他这般任性,若是被老祖宗瞧见了定是要斥他几时。
“她来历不明,又恐是汉家女子......”曹寅小心翼翼道,抬眼望着他。
他眯着眼看着曹寅:“是,是汉人又如何?”
“姑娘她......她是汉人,若您落人把柄,招人摇唇捣舌不说......而况,祖制上有规定…...”
他眉毛一挑,冷声道:“何必忌惮。”他忿然:“宫中本就无趣,难得隐匿着出来游玩,身旁带个人也需他们左右。”他一赌气:“这位子让给你好了。”
“卑职不敢。”曹寅连忙跪下。
少年轻狂,他没耐性,直皱眉。
“请听卑职一言,领姑娘入宫,定会引起宫人不满,以她身世,借机构陷,姑娘在宫中就难以立足。”曹寅深知他自小固执,倒也知他禀性。
果然如此,他方才有了动摇:“那你怎么说?”
“卑职认为,先将姑娘留此,等风头过了,禀了太皇太后,便也好办些。”曹寅应。
若有所思,他道:“如此……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