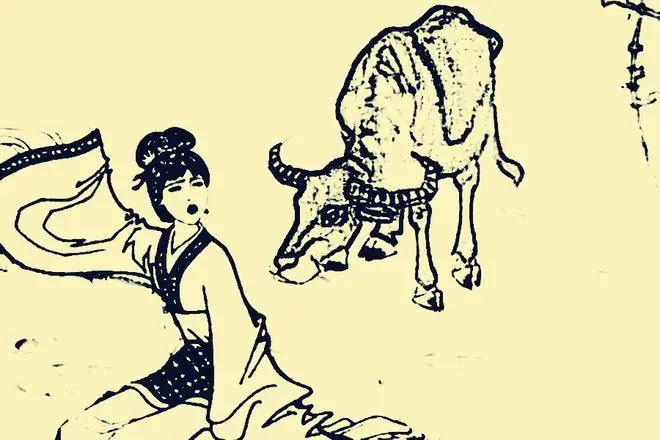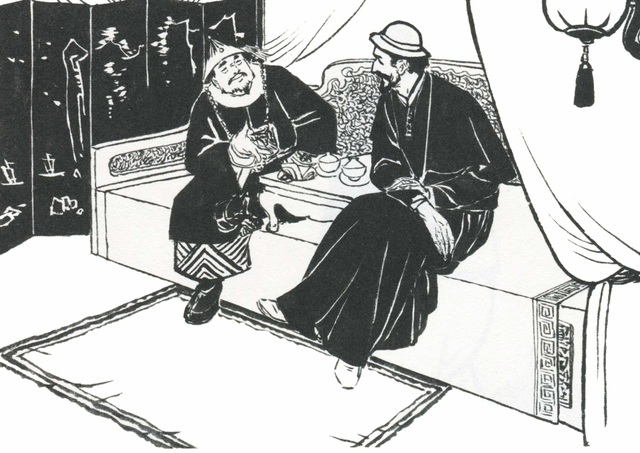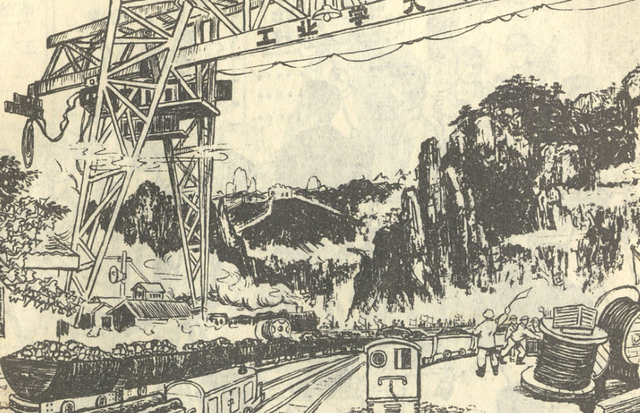近卫骑兵团军官纳罗莫夫家里的牌局,到早晨四点多才散。餐厅里,赌赢的人狼吞虎咽,其余客人心不在焉地面对着吃空的盘碟。香槟酒上来时,谈话热闹起来。
“格尔曼这人真怪!”主人纳罗莫夫指着一位年轻的工程兵军官说,“他平生从没下过一次赌注,却天天看着我们打牌。”另一位来客接了上来:“他从不动心赌上一次,这种坚定真令人惊讶!”
而格尔曼不慌不忙答道:“打牌我是十分感兴趣的,可我不能因为指望发横财而丢掉来之不易的金钱。”这就是他虽有强烈的欲望却从不下注的原因。他只是狂热地注视着赌局中瞬忽万变的金钱流转。
年轻而颇有身价的保尔公爵开口了:“格尔曼是个精打细算的人,不容自己有丝毫放纵。他不打牌,有什么奇怪?倒是我那位祖母安娜·费多托夫娜伯爵夫人,她从不染指赌局,实在使我不解!”
人们哄笑起来:“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不赌钱,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保尔公爵微微一笑:“那么,你们实在是对她毫无所知咯?要晓得,她年轻时赌得可凶,简直是一掷千金!”
有趣的话题吸引着大家。保尔公爵兴致勃勃地说:“六十年前,我祖母在巴黎轰动一时,人们都想一睹“莫斯科女神”的风采;当时出名的李希留公爵也追求过她,由于她的冷淡,李希留几乎自杀。
那时贵妇人都爱打牌。有一次她在凡尔赛宫里打牌,输给奥尔良斯基公爵,欠下一笔巨款,怏快地回家。
“到了家里,她把输钱的事告诉祖父,要他付账。我祖父本是祖母府上的管家,平常对她十分惧怕,但听说输了吓人的一笔钱,他勃然大怒,取出账本给她看,半年来他们已经花掉五十多万卢布了。
在巴黎可不比在俄国,他们手头没有大片田庄可供抵押,祖父断然拒绝付款。祖母打了他一个耳光,独自走进卧室,以示气恼。
“第二天她吩咐把丈夫唤来,指望这种家庭惩罚对他起些作用,然而发现他毫不动摇。她平生第一次同他反目争吵。祖父大发雷霆,吼道:“不行,休想!
“祖母不知怎么办才好。她有个密友叫圣·茹尔曼伯爵,是位爱冒充点金术发明者的老怪物,在社交界十分讨人喜欢。祖母知道他能筹措大笔金钱,就写信请他帮忙。
“老怪物召之即来。祖母向他描述丈夫的蛮横,最后表示,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了。圣·茹尔曼考虑了一会,说:“你不必借债,我有办法帮你赢回输掉的钱。'
“祖母答称,她根本没有赌本了。圣·茹尔曼指出,这用不着钱,他附耳告诉她一个秘诀。这秘诀是人人都肯出高价换取的·····.”
青年赌客们加倍注意听讲了。保尔公爵继续说:“当天晚上祖母就到了凡尔赛宫。奥尔良斯基坐庄分牌;祖母说明她没有带来欠款,对此略表歉意,然后坐在他对面下注。
“她选了三张牌,一张接一张下注。这三张牌一注接一注,她都赢了。就这样,祖母赢回了所输的钱。”
客人们听到这儿议论纷纷:“这是碰巧呗!”“说不定是魔法?”“显然是信口开河!”纳罗莫夫追问道:“怎么,你祖母能接连猜中三张牌,而你至今没传授到她的秘诀?”
公爵叹道:“嗨,哪能呢!她有四个儿子,全是不要命的赌徒,但她没有向任何一个公开过她的秘密。只是,已故的恰普里茨基,那个挥霍掉百万家财、最后忧愁而死的人,据说曾得过她的指点。
“这是我叔叔依凡伯爵讲的,他以人格担保确有此事。恰普里茨基有次赌输了30万卢布,他陷于绝境,前来向祖母告急求助。
“祖母对年轻人的放荡胡闹一贯十分严厉,这次却不知怎么怜悯起他了。她指点他三张牌,教他一张挨一张地下注,并要他以名誉担保今后决不再赌。
“恰普里茨基去找赢他钱的人,他们坐下赌牌。恰普里茨基在第一张牌上押了五万赌注,一举获胜;再下一注,又下一注,竟捞回了本钱,还转赢了一些······”
讲到这儿,保尔公爵突然停住话题,掏出怀表瞧一眼说:“差一刻六点,该回家睡觉啦!”大家这才喝干杯中的剩酒,恋恋不舍地各自散去。
格尔曼回到住处,许久不能入睡。他想:要是老伯爵夫人向我公开她的秘诀,那该多好!干吗不碰碰运气呢?向她作自我介绍,赢得她的宠爱,哪怕做她的情夫也成。
第二天,他在彼得堡街头徘徊,心中暗自盘算:那老太婆已经87岁了,也许过两天就会死掉的!·······那个传闻本身,能相信么?······不!勤勉、节制、精打细算,这才是我最牢靠的三张牌。
想着走着,他不知不觉停步在一座大厦前,但见华贵的轿式马车一辆接一辆驶进灯火辉煌的大门。他向岗警打听:“这是谁家府邸?”岗警说:“是安娜·费多托夫娜伯爵夫人的家。”
格尔曼一阵哆嗦,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令人惊奇的秘诀。他绕着大厦徘徊,想着它的女主人以及她那神奇的本领,简直不愿离去。
踌躇到很晚他才回家。当他终于被瞌睡征服时,梦境中出现的就是纸牌、绿色的赌桌、成堆的金币,他梦见自己果断地下注,不停地赢钱······
醒来时,他还为失掉梦中的财富而叹息。伯爵夫人的府邸在他眼前浮动,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召唤他。他决意再到那里去看看。
他又到了那座大厦面前,站下来张望各个窗口。在一扇窗子里他发现有个姑娘的侧影,低垂着头大概在看书或做手工。
姑娘便是老伯爵夫人的穷养女丽莎。她一抬头,看见大街上有一个青年军官在徘徊。第二天,她坐在窗边绣花,无意中朝街上一望,又看见了他。
她低头继续绣花。过了五分钟,她又对窗外看一眼,青年军官仍在原地站着。姑娘脸上泛起一阵红晕,头几乎直低到绣花布上。
这时伯爵夫人走进来,要丽莎陪她出去散步。丽莎不敢怠慢,赶紧收拾活计。脾气古怪的伯爵夫人却嚷道:“怎么,我的小姐!你聋啦?快去吩咐套车。”
女仆呈上老夫人的孙儿保尔公爵捎来的几本新书,都是时新的长篇小说。伯爵夫人又把丽莎喊住: “先不忙换衣服。坐下,翻开这一本,大声给我念…………”
丽莎拿起书读了几行,伯爵夫人说:“响一点!我的小姐,你嗓子哑了,还是怎的?······等一等,给我把凳子移近些,再近一点·····读吧!”
小姐又读了两页,老夫人打呵欠了。“丢下书本,”她说,“这上面全是胡说八道!把它送还给保尔公爵·······马车怎么样啦?”
丽莎答称马车已经备好。伯爵夫人瞟着她皱皱眉:“你怎么还没有换衣服?总要等你!小姐,这真无法忍受。”丽莎急忙跑到自己房里去换衣服。
不到两分钟,伯爵夫人就拼命摇铃了。三个女仆和一名侍从应声而至。伯爵夫人对他们说: “怎么喊都喊不应你们?去催催小姐,我在等她。”
丽莎进来了。伯爵夫人没好气地说:“你到底来啦,我的小姐!干吗这样打扮?干什么!去勾引谁啊!·······可是天气怎么样?好像起风啦。”
侍从答道:“一点没有风,天晴气爽!”伯爵夫人瞪他一眼:“你总是信口开河!打开通风窗。就是有风么!还冷飕飕的!卸车吧,丽莎,我们不出门啦。”
瞧我过的是什么生活!丽莎心说。她是这儿最可怜的人。有道是“他人的饭菜难咽,他人的台阶难跨”,又有谁能像她那样懂得寄人篱下的苦楚呢?
她忍住泪,忐忑不安地走到窗子跟前。那军官已不在了·······
两天后,她随伯爵夫人出门时,又看见了他。丽莎吓了一跳,怀着说不出的惊慌坐进马车。他就站在大门口,支起大衣领遮着脸,一双黑眼睛在帽子底下炯炯闪光。
回家时,她首先奔到窗前。军官站在老地方,双眼正紧盯着她。她走开了,心里觉得好奇,一种从未体会过的情感激动着她。
从那时以来,这年轻人没有一天不来到她的窗下。在他和她之间建立了默契的关系,尽管她仍坐在老地方做活,却感到他走得越来越近了。一周以后,她对他微微一笑…………
这天上午,丽莎正在帮伯爵夫人梳妆,保尔公爵前来拜访,请求允许把一个朋友介绍给伯爵夫人。老祖母点点头:“好吧,你带他到星期五的舞会上来见我。”
保尔公爵和丽莎闲谈。姑娘低声问:“您想介绍谁呢?”公爵笑答道:“纳罗莫夫。您认识他?”“不!他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军人。”
姑娘心头猛跳起来:“是工程兵军官么?”公爵道:“不!是近卫骑兵军官。您为什么认为他是工程兵军官呢?”姑娘红着脸不回答,悔不该让一句不谨慎的问话把心事泄露给了轻浮的保尔公爵。
老夫人要出门访客,保尔公爵先行告辞。丽莎跟老夫人走出大门,正当仆人扶老太太上车时,姑娘发现那个工程兵军官就在一旁。他上前握住她的手,她被吓懵了。
年轻人很快退去,却塞了一封信在她手里。她把信藏进手套,一时心乱如麻。
路上,她无心听也无心看。伯爵夫人在马车里照例问个不停:我们遇见谁啦?这座桥叫什么名字?那招牌上写的什么?丽莎信口回话,答非所问。
老夫人十分生气:“你昏了头啦,我的小娘儿!我说的话你没有听见,还是听不懂?······谢天谢地,我口齿还清楚,也还没有老糊涂哩!”丽莎并不作声。
到了客人府上,丽莎趁着进更衣室整理服饰的机会,从手套里取出那封信。信没有封口,她匆匆读了一遍。
信的内容是表白爱情,写得温存、恭敬,是一字不差地从德国小说里抄来的。不过丽莎不懂德文,也没看过德国小说,对这封信十分满意。
但这封信也引起了她极大的不安。她责怪自己行为缺乏检点,不知怎么办才好:以后不再坐在窗口,表示冷淡吗?把信退还给他吗?她没有人可以商量。
丽莎决定给他写封冷冰冰的复信。回到家里,她在自己房里拿出纸笔思索起来。她几次写了个开头,又撕掉了,时而感到用词过于温婉,时而又觉得口气太硬。
最后她下定决心写道:“我相信您是诚心诚意的,并非想以如此轻率的行为令我蒙受侮辱;但我们的相识不应通过此种方式开始。今将贵信奉还,望今后勿再使我抱怨您的无礼。”
第二天,丽莎一见格尔曼走来,就从窗口把信掷到大街上。格尔曼拾起信,进了一家糖果铺。
他撕开信封,发现了自己的信和丽莎的复信。这不出他之所料。年轻人便回家,专心致志策划他的下一步计谋。
三天后,一个眼明手快的姑娘在时装店里给丽莎捎回一封便函。丽莎不安地拆开,以为是来收账的,忽然认出是格尔曼的笔迹。
您弄错啦,这张条子不是给我的。”她说。姑娘并不掩饰她那狡黠的笑容:“不,确实是给您的!请念吧!”丽莎飞快地看了一遍来函。格尔曼要求会晤。
丽莎对他这仓促的要求和传信的方式感到害怕。“这封信确实不是给我的!”她说着把信撕得粉碎。姑娘含笑:“假如确实不是给您的,您干吗把它撕了呢?”
由于被对方一语点破,丽莎面红耳赤:“好吧,以后请别再给我捎什么信来。您告诉托您带信的人,他应该觉得害臊······”
但格尔曼并不就此罢休。丽莎每天都会收到他用各种方式捎来的信,它们已经不是抄自德国小说,而是用他自己特有的语言写成,显示出他的百折不挠和想入非非。
丽莎已经不想把它们退回去了,这些信使她陶醉;她开始答复,回信越来越长,语调越来越温柔。
最后她掷给他这样一封信:“今晚法国公使举行舞会,伯爵夫人要去参加,我们将逗留到午夜两点。您和我单独会晤的机会到了。您在十一点半来吧,直接上楼梯找我的房间·····.”
格尔曼整天不安,等待着指定的时刻。晚上十点他已经站在伯爵夫人府邸门前。天气异常恶劣,狂风呼啸,鹅毛大雪纷飞,街灯昏暗,街上杳无人迹。格尔曼穿得很单薄,对大风大雪毫无知觉。
漫长的等待过后,终于他见到伯爵夫人的马车套好了,仆人们扶着裹在貂皮大衣里的驼背老太婆上了车,她的养女也跟着上了车。
马车从松软的雪地上驶过。守门人关上大门,窗户黑了。格尔曼开始绕着冷清下来的府邸走了一阵,在街灯下看看表,十一点二十分。他等待余下的几分钟过去。
十一点半整,格尔曼跨进伯爵夫人家的大厅。守门人不在。他顺着楼梯往上跑,万一被人撞见,就问一声伯爵夫人在不在家,这是丽莎在信上教给他的办法。
过道上,他看见灯光下有个仆人在安乐椅里打盹。格尔曼迈着轻而坚定的步伐从他身边越过。

大厅和客室很暗,借助过道里射来的灯光,格尔曼走进伯爵夫人的卧室。摆满古老神像的神龛前点着长明灯,墙上挂着两幅肖像画,一幅画的是胸佩勋章的男人,另一幅是位年轻的美女。
这里到处摆着贵夫人收藏的、形形色色的小玩意儿,从名贵瓷像到孔雀羽扇,应有尽有。格尔曼按丽莎的指点转到屏风后,那儿有两扇门,右边一扇通书房,左边一扇通走廊。
打开左边那扇门,看见一架狭窄的螺旋梯,这是通到可怜的养女房间里去的。按约定他应该到那边去等她······然而他并不往左边去,相反转过身来进了黑洞洞的书房。
时间过得很慢。客厅里钟敲十二点,所有房间的钟此起彼落都敲了十二下,随后又寂静无声。格尔曼十分镇定,正如一个人决心去干一件无可避免的冒险事一般。他侧身靠在冷冰冰的火炉上,继续等候。
时钟敲过一点,两点。这时他听见了远处的马车行驶声,不由得激动起来。马车驶近了,停下了。屋子里忙乱起来,人们跑着嚷着,又是灯火通明了。
伯爵夫人进入卧室,倒在安乐椅上。丽莎匆匆退出。格尔曼听见她走在螺旋梯上的匆促脚步声,心里似乎产生了某种愧悔的感觉,但立刻又平静下来。他麻木了。
老夫人在穿衣镜前宽衣。扑粉的假发从她秃了的头上掀下来,固定假发的别针像雨点似的散落在她身边。格尔曼成了这一令人厌恶的内幕的见证人。三个老仆人服侍伯爵夫人卸装。
伯爵夫人换上睡衣睡帽,这种装束同她的龙钟老态更般配,因而她反倒显得不那么可怕和丑陋了。仆人们被打发出去,房间里只剩长明灯照亮。
突然,老夫人那张死人似的脸莫名其妙地变了色:她面前站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别害怕!我没有加害您的意思;我是来恳求您帮我一点忙的。”他清清楚楚地低声说着。老太婆默默地望着他,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
格尔曼以为她聋了,便凑到她耳边又说了一遍,并恳求道:“您能促成我一生的幸福,这在您是不费一点儿力的;我知道您能接连猜中三张牌·····.”
伯爵夫人似乎听明白了,她思索了一会儿,终于说道:“是开玩笑。我向您发誓,这是开玩笑!”格尔曼不高兴了:“这里没什么玩笑可开的。您记得恰普里茨基吧,是您帮他捞回本钱的。”
老夫人显然窘住了。她的脸色表明她内心一度十分激动,但很快又陷入原来的麻木状态。格尔曼催促说: “您能否给我指出这三张可靠的牌呢?”伯爵夫人默不作声。
格尔曼接着说: “您的秘密还要为谁保守呢?为孙子们吧?您帮不了那些败家子的忙。可我不是败家子,我看重金钱,您那三张牌对我不会白费的。请说吧!…………”
他跪下来,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伯爵夫人一言不发。格尔曼说:“假如您胸膛里跳动的是一颗人类的心,那么我恳求您凭夫妻的、情人的、母子的,总之生活中所有的一切神圣感情,别拒绝我的请求!
“向我公开您的秘密吧!您守着它有什么用?想一想,一个人的幸福就掌握在您手里!只要您把秘密告诉我,不仅我,还有我的子子孙孙,都会对您感恩戴德······”
老太婆仍是一句话都不回答。格尔曼火了,咬牙切齿地威胁说:“老妖婆,你不开口,那我只有强迫你回答······”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伯爵夫人一见手枪,又一次大惊失色。她摇摇头,举起一只手来,仿佛要挡枪弹似的·······然后仰面倒下······一动不动了。
“别胡闹,”格尔曼拉住她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一次:愿不愿把您那三张牌告诉我?愿不愿?”伯爵夫人没有回答。格尔曼一看,她已经死啦。
丽莎到家以后,惴惴不安地奔进自己的卧室,既盼望看到格尔曼在房中,又希望见不到他。她第一眼就确信他没有来,感谢命运设置了阻挡他们相会的障碍。
她坐下来,开始回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使她走得这么远的种种情景。她如此轻易地让他取得夜间相会的允诺,而她根本对他的底细一无所知······真是怪事!
她也想起今晚舞会上的情形。保尔公爵由于波琳娜小姐一反常态不向他献媚,特意招呼丽莎同他跳舞以示挑衅,他一个劲嘲笑她对工程兵军官的偏爱,声称他对格尔曼的了解远比她所能猜想的更多。
这几句戏言恰恰击中要害,以至丽莎担心自己的秘密已经被他识破。保尔公爵笑道:“他是个十分出色的人,名叫格尔曼!”丽莎感觉手脚发凉,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个格尔曼,”保尔继续说,“他的侧影像拿破仑,但有个魔鬼的灵魂。我认为他良心上至少有三桩罪恶。啊,您的脸色多么苍白!······.”丽莎嗫嚅着:“我头疼······”
保尔道:“我认为,格尔曼正在打您的主意,他也许在教堂里见过您,也许在·······天知道,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三位女士走到他们跟前,邀公爵同舞,他们打断了丽莎密切关心的谈话。丽莎一直想再和保尔公爵讲两句,但老伯爵夫人却要回家了。
保尔的话,深印在沉湎于幻想的少女心里。他给格尔曼画的像,不料同她心中的构图相似。她正心事重重的,冷不防门打开了,格尔曼走了进来。
她哆嗦了一下,惊惶地低声问:“您到哪里去啦?”格尔曼答道:“我在老伯爵夫人卧室里,刚从她那里过来。伯爵夫人死啦。”
“我的天哪!·······您说什么?”丽莎大吃一惊。格尔曼低下头说:“看上去我是她致死的原因。”丽莎望了他一眼,想起了保尔公爵的话:他良心上至少有三桩罪恶!
丽莎恐惧地听完格尔曼吐露的全部真情。原来,那些热情洋溢的书信,那些大胆顽强的追求,统统不是爱情!金钱,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而她不过是谋杀她老恩人的强盗的盲目帮凶罢了!
她后悔不迭,嚎啕大哭。格尔曼默默望着她,但无论是少女的眼泪,还是她的痛楚中包含的惊人魅力,都没有触动他冷酷的心灵。他抱憾的只是:指望赖以发财的秘密永远失去了。
“您是个恶魔!”丽莎终于说。格尔曼分辩道: “我不希望她!死,我的手枪没装子弹。”他们都不作声了。
晨曦来临。丽莎擦干哭肿的双眼,举目注视格尔曼:他交叠双手,阴沉地皱着眉头,姿势与拿破仑的肖像出奇地相似。这种貌似,使丽莎感到吃惊。
“您怎么走出这座宅子呢?”丽莎最后问道。格尔曼表示只要告诉他怎样找到暗梯,他自己出去。丽莎从五斗橱里取出钥匙,递给格尔曼,对他作了详细说明。
格尔曼握了握她冰冷的、毫无反应的手,吻一下她低垂的头,独自走出去了。
他走下螺旋梯,又进了伯爵夫人的卧室。死去的老太婆直挺挺坐在那里,脸色十分安详。格尔曼站在她面前,看了她良久,似乎想查明这可怕的事变是否确实。
最后他走进书房,摸着了墙上的小门,顺着黑暗的梯子往下走,在楼梯尽头发现一扇小门,就用那把钥匙打开,于是穿过走廊,上了大街。
祸事发生后的第三天早晨,格尔曼来到教堂参加伯爵夫人的葬礼。他尽管毫不愧悔,但毕竟不能彻底压制良心的责难;他缺乏信仰,却颇有偏见,相信死者能加害他的一生,所以决定前来求她饶恕。
教堂里挤满了人,格尔曼使劲挤进去。死者的亲属们都身着重孝,但谁也没有哭。伯爵夫人早已风烛残年,大家早把她看成过世的人了。
一个青年牧师念了祭文。他用朴素动人的词句,说明死者是经过长年累月默默修身而达到善终。祭文说:“死神接受了她,把她乐善好施的灵魂引进天堂。”
最后是哀悼仪式。亲属们首先向遗体告别,后面随着无数宾客。最后走来死者的同龄女友,她已衰老得无力磕头,只有她一人洒了几滴眼泪,吻了老夫人冰凉的手。
格尔曼决定跟在她后面走到棺材跟前。他跪下磕头,在冰冷的、铺着杉树枝的地板上伏了几分钟。
站起来时,他脸色像死者一样灰白·······这一瞬间,他似乎瞧见死者嘲弄地眯着一只眼睛向他看了一眼。他心发慌急忙后退,一失足跌倒在地。
人们把他扶起来。就在这同一时刻,丽莎也昏厥在教堂门口。这个插曲把阴森的仪式搅乱了几分钟,大家窃窃私语,议论着这青年军官也许是死者的私生子·····
格尔曼整天情绪极端恶劣。他到一家偏僻的小饭馆吃午饭,并一反常态喝了很多酒,指望借酒浇愁。
但酒精使他的思想更加狂乱。他脚步踉跄地回到家,和衣往床上一倒,呼呼酣睡起来。
半夜时他似乎醒了过来。月光照亮房间,他的睡意消失了,坐在床上回想老伯爵夫人的葬礼。这时窗外好像有人朝他看了一眼,随即走开了。他毫未留意。
过一会儿,他听得有人推开外屋的门,以为照例又是那酩酊大醉的勤务兵夜游回来了,但脚步声有点陌生。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
格尔曼把她当作自己的老乳母了,正惊异她怎么在这个时候进来。但白衣女人轻飘飘地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于是格尔曼认出那是老伯爵夫人!
“我到你这里来并非出于本意,”她坚决地说,“但我遵命来满足你的请求。记住:三点、七点和爱司,能使你接连赢钱。
“附带条件是,你不能在一昼夜间发一张以上的牌,而且从今以后一辈子不要再赌。我饶恕你把我吓死,但你要发誓娶我的养女丽莎为妻······”
说完这些话,她悄悄转过身去,朝门口走出去,不见了,只听见鞋子的窸窣声。格尔曼听到外屋的门“砰”一声关上了,又见窗外有人看了他一眼。
半晌,格尔曼才定下神来。他走到另一间房里,使劲把勤务兵唤醒。勤务兵照例烂醉如泥,因而从他嘴里问不出一句准话。
外屋的门锁得好好的。格尔曼回到自己房中,点起蜡烛,记下了所见的情景。
这三张牌开始牢牢盘踞在格尔曼脑子里。当他看见一位艳丽的少女,就嘀咕说:“她多俊秀!真像个红桃三。”有人问他几点钟,他回答:“七点。”任何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在他看来都像爱司。
三点、七点、爱司追随他入梦,变成千奇百怪的模样:三点变幻成盛开的石榴花在他面前怒放,七点化作哥特式大门,爱司是个大蜘蛛。
他的全部思想集中到一件事上:运用这使他付出高昂代价的秘诀。他想去巴黎赌场迫使幸运女神献出宝藏,但一个良机免除了他的奔波—莫斯科富豪赌客总会的主持人到彼得堡来了。
该主持人是颇有名望的契卡林斯基。他把毕生消磨在赌博上,一度赢过上百万钱财。纳罗莫夫把格尔曼介绍给主人。
契卡林斯基坐庄分牌。这一局牌持续很久,每次分完牌庄家都会稍待片刻,让赌客有时间考虑、下注。他记下输的账,笑容可掬地听取每位赌客的要求。
一局牌打完,契卡林斯基洗牌分另一副。格尔曼伸出手说:“请允许我放一张牌。”主人笑笑,表示悉听尊便。纳罗莫夫庆贺格尔曼解除多年的赌戒,祝他马到成功。
“好啦!”格尔曼用粉笔在自己一张牌的上方写了数目。庄家眯着眼问:“多少?请原谅,我看不清。”格尔曼回答道:“4.7万。”
刹那间,所有目光都集中在格尔曼身上。纳罗莫夫想,这小子发疯啦!然而庄家始终满面笑容: “请允许我指出,您赌得太大了,这里还没有人孤注下过300卢布以上的。”
“怎么?”格尔曼提出异议,“您打不打我的牌?”契卡林斯基行个礼表示同意,并说:“我不过想告诉您,这里赌现金。为了赌场的规矩和计算方便,请把钱放在牌上。”
格尔曼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支票,这是他的全部财产。他把支票递给契卡林斯基,后者迅速扫了一眼,把支票放在格尔曼的牌上。
他开始分牌。右边揭出九点,左边三点。格尔曼指指自己的牌说:“三点,我赢了!”格尔曼手中的牌也是三点。
赌客中一阵耳语。契卡林斯基皱皱眉,但脸上又立刻挂上微笑。他问格尔曼要不要立刻取款,格尔曼点点头,说:“劳驾。”契卡林斯基用几张支票把账付清。
格尔曼接过赢的钱,离开了赌桌。纳罗莫夫简直摸不着头脑。格尔曼喝了杯柠檬水,回家去了。
第二天晚上,他又出现在契卡林斯基那里。主人在分牌,和蔼地向他行礼。赌客们立刻让给他一个座位。
格尔曼等到赌第二局时,摆下一张牌,把自己的4.7万以及昨天赢得的4.7万都放在牌上。契卡林斯基开始分牌。杰克出现在右边,七点在左边。格尔曼翻出自己的牌:七点!

所有的人都惊呼起来。契卡林斯基显然发窘了,他数出9.4万,递给格尔曼。格尔曼若无其事地接了钱,当即就离开了。
第三夜格尔曼又出现在牌桌旁。人们都在等待他,想看看这不寻常的赌博。他们有的停下手中的牌局,有的从沙发上蹦起来。大家都给格尔曼让路。
其他赌客都停止放他们的牌了,着急地等着看他如何结局。格尔曼准备一对一地同脸色苍白、但依然含笑的契卡林斯基对赌,两人各自拆开一副牌。
契卡林斯基洗牌。格尔曼抽出并摆好了自己的一张牌,把一捆银行支票押在牌上,一共是18.8万。这好像是一场决斗似的,周围鸦雀无声。
庄家开始分牌,他的手在颤抖。右边摆出皇后,左边是爱司。“爱司赢了!”格尔曼说着翻开自己的牌。
“您的皇后输了!”契卡林斯基和蔼地指出。格尔曼哆嗦了一下;确实,他的牌不是爱司,而是黑桃皇后。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明白他怎么会抽错的。
这一霎那他仿佛感到,黑桃皇后眯缝着眼,冷笑了一下。这不同寻常的貌似使他震惊······他惊恐地喊道:“老太婆!”
契卡林斯基把赢得的支票搂到自己面前。格尔曼站着一动不动。人们热烈地谈论,众口一词发出同样的惊叹:“赌得真痛快!”庄家重新洗牌,赌博继续进行。
结局是不难想像的,格尔曼疯了。他枯坐在工程兵医院的病房里,不回答任何问题,嘴里异常急速地嘀咕着:“三点、七点、爱司!三点、七点、皇后!…………”
丽莎嫁了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他有公职,有相当数量的产业,是老伯爵夫人已故管家的儿子。保尔公爵晋升为近卫骑兵大尉,娶了波琳娜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