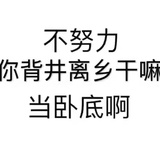入乎《易》内,出乎《易》外——姚彬彬著《〈周易〉诠释与清代新义理学的思想源流》序
文丨周积明
观堂先生之《人间词话》言:“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其“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一语,道出学问之道的基本路径,非此,文章无生气,亦无高致。今武汉大学姚彬彬君以书稿《〈周易〉诠释与清代新义理学的思想源流》赐余,拜读一过,顿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之感,遂借王观堂之意,以“入乎《易》内,出乎《易》外”为题,概言其书立意述论之精彩。

盖清代思想史之研究,肇始于清末民初,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胡适等筚路蓝缕,钱穆、熊十力、余英时等步履其后,其间佳作倍出,星汉灿烂。至20世纪90年代,则有“清代新义理学”之概念异军突起,开启斯学之新路径。
所谓“清代新义理学”,所针对者有二,其一,“乾嘉无思想”。此论源流甚长。早在民初,梁启超于《清代学术概论》中言:“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新儒家熊十力曾于《读经示要》中更谓:“夫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不过拘束于偏枯之考据,于六经之全体大用毫无所窥。其量既狭碍,其识不宏通。其气则浮虚,其力则退缩。”他的弟子牟宗三,后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于此意又有进一步发挥:“我们讲中国的学问,讲到明朝以后,就毫无兴趣了,这三百年间的学问,我们简直不愿讲,看了令人生厌。”当代学人朱维铮也以“思想界的沉闷达于极致”来描绘乾嘉时期的格局。因此,“乾嘉新义理学”的提出,是对“乾嘉无思想”论的重大反拨;其二,“义理”范式唯一论。晚清方东树曾于《汉学商兑》中言:“夫古今天下,义理一而已。”其所言之“义理”唯一范式,即“言心言理言气”之宋学。事实上,早在乾嘉时,焦循已曾提出“戴氏之义理”的概念,并强调“戴氏之义理”非宋儒之义理。“乾嘉义理学”将“戴氏之义理”扩展为乾嘉时期的一种新思想、新取向,掘发“义理学”从形式到内容的更新,乾嘉思想界的地图由此得以重新绘制。
“乾嘉新义理学”树立旗帜,大张其军,虽始于三十余年前,但却有前驱思想之轨迹作为铺垫。1923年,胡适撰《戴东原的哲学》,文中指出:“戴震在清儒中最特异的地方,就在他认清了考据名物训诂不是最后的目的,只是一种‘明道’的办法。他不甘心仅仅做个考据学家,他要作个哲学家。”其影响所及,“这时期的经学家逐渐倾向于哲学化了”。凌廷堪、焦循、阮元等,“虽然都不算是戴学的真传,然而,他们都想在经学上建立他们的哲学思想”。他因此断论:“从戴震到阮元是清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叫做‘新理学时期’。”此如姚君著中所言:“其所言‘新理学时期’的划定,在时段和范围上,均基本契合今人所言‘清代新义理学’的定义,实为孤明先发之论。”
1947年,钱穆在南京《中央周刊》上发表了《论清儒》。文中,钱穆一方面批评说:“清代学风,总之是逃避人生。魏、晋、南北朝时代之逃避人生是研读老子、释迦,清代的逃避人生是研穷古经籍。”但他又指出:“但清儒到底也有耐不住的时候,或者是他们的不自觉而对人生问题有所论列,则他们亦有一共同态度与共同意见。他们大抵反对抬出一个说法来衡量一切或制裁一切。换言之,他们反对思想上的专尊,或说人生理论上之独裁。他们大抵主张解放,同情被压迫者。”“求平恕,求解放,此乃乾、嘉诸儒之一般意见,而非东原个人的哲学理论。”其论亦在不经意间揭示了今人所言“乾嘉新义理学”之思想底色。
1970年代中期,余英时撰写了影响深远的《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余英时于著中对“汉学考证完全不表现任何思想性(义理)”之说提出批评,指出:“尽管清儒自觉地排斥宋人的‘义理’,然而他们之所以从事于经典考证,以及他们之所以排斥宋儒的‘义理’,却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儒学内部一种新的义理要求的支配。”并进一步深入剖析说:“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在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之中。相反,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好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尽管余氏的论述主要集中于章学诚和戴东原,但他的见解无疑亦为乾嘉学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方法论。
张寿安继承前贤关于清代学术的新视野,她在1993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举办的“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乾嘉义理学”这一概念。张寿安说:“我们不妨以宏观的态度把‘义理’一词视为儒学思想,儒学思想在不同时代有不同面貌和性质,魏晋是玄学,隋唐时是佛学,宋明时是理学,而乾、嘉所呈现的面貌,现在仍在探讨中,不妨暂且称为乾嘉义理学。”这一倡导与张寿安著作《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的出版,对“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1998年7月,文哲研究所又在林庆彰的主持下,开始执行为期三年半的“清乾嘉学派经学研究计划”。第二年的子计划是“乾嘉学者的义理学”。一时之间,台湾地区之“乾嘉新义理学”研究“气象蓬勃”(张寿安语)。随后,“乾嘉新义理学”之说在大陆清学研究者中得到积极呼应,王俊义、黄爱平、陈居渊、吴通福等均参与其中,余与雷平君亦忝列其内。
余治清代思想史昔从《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入手。初,余在华中师范大学师从吴量恺、张舜徽先生习史。吴量恺师专研清代经济史,张舜徽先生乃文献学大家。舜徽师屡以张之洞之语教导:“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其时初入学术之门,根基薄弱、知识疏浅,遂决心遵师之命,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是时所读《四库全书总目》乃中华书局1964年影印本,字迹虽小,余却兴致盎然,多次通读,并于重点部分抄录笔记。犹记一个雪夜,母亲因病住院,余在病房外守护,天寒地冻,虽以军大衣裹身,仍手足冰冷。是夜,陪伴余者惟一册《四库全书总目》,读至深处,竟不觉寒冷与夜深。在反复研读之下,余深感《四库全书总目》绝不仅仅是一般的目录学著作,更是一部清代思想史著作,故以往之刊误、补正、考核、纠谬,虽有功于《四库全书总目》之研究,但却忘却了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在内的中国古典目录,其本质是人类的文化实践活动,其间无一例外地积淀和凝聚着主体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情感趋向、理想愿望以及知识、才能等文化品性,蕴含着活生生的灵魂。如果不是从修纂主体的角度去理解它,发掘它的思想世界,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那么,必然无法取得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真正全面认识。
由于对《四库全书总目》形成了有关思想性的文化理解,余之硕士学位论文拟定为《〈四库全书总目〉之史学思想研究》,蒙吴量恺师宽宥,恩允余做此与清代经济史范畴无关之题目。论文答辩时,舜徽师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他第一句话是:“周积明同志今天不应该坐在这里。”余初大为震骇,随之体会到其中深含的奖掖与鼓励。三十多年过去,其情其景记忆犹新。获得硕士学位后,余以硕士论文为基础,加以扩展,遂成《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其意在一反传统“四库学”的研究路数,着力透过《四库全书总目》的“外壳”,把它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加以还原和分析,从中探寻中国文化的“种族心理”、十八世纪的“时代心理”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制作者的“群体心理”。30年后回看,是书实在颇为粗疏,资料考证未精,论证未及详密周到,论述简单化平面化,未能深入揭示其中复杂的权力关系。但在1990年代初,该书的出版还是带来了清代思想研究的新鲜气息。《江汉论坛》上曾发表署名“石玉”的书评《文本解读——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读后》,评价此书的方法论意义说:“作为社会科学一般方法论的阐释学(狄尔泰如是观)近年来已被介绍到中国来,从文本的字里行间发现符号的下面深藏不露的‘意义’,也深得有识之士的赞同。但是,虽然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发现‘吃人’那句名言颇有些阐释学味道外,至今用这种眼光来进行研究的具体成果尚属稀见。我感到周积明这部专著即属其一。因为作者意图‘穿透古典目录的物化外壳,追寻深藏其间的文化灵魂’。他力图通过此‘从一个新的角度、新的领城去获得对传统的更为深入的认识’,虽然并未言明这个角度或领域是什么,然而窃以为这便是文化阐释学。作者不满于传统‘四库学’对《总目》的‘纠谬补遗’,而要进一步‘将它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加以还原和分析,捕获它的魂灵’,象丹纳那样去寻找‘一个时代的心理,一种种族的心理’,便是说明。”其时尚不知“石玉”先生是谁,多年后方知是赵世瑜兄,在此专门拜谢。
农历丁丑年,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筹备召开以“两岸四库学”为主题的“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其时两岸学术初通,彼此并不熟稔,故余收到邀请大为意外。到台北后方知,会议筹备时,台湾四库学大家,故宫博物馆文献处处长吴哲夫先生专门嘱咐淡江大学周彦文教授,一定要把周积明先生找到,请来参加会议。余深受感动。哲夫先生待余甚厚,有时赴台竟邀请我居住其宅,并开车带我周游台岛。张寿安教授不仅与其夫君周昌龙教授殷勤接待,并携余广泛结识台湾学术界朋友。有次在台北“中研院”胡适图书馆拜见朱鸿林先生,朱先生言,他将《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指定为研究生班必读书,令余大受鼓舞。在与台湾学术界之交流中,余接触到台湾学术界之“乾嘉新义理学”研究,蓦然发现,以往关于《四库全书总目》“思想世界”之研究、其与戴震、袁枚相合的议论,顿时呈现出一种新的意义。由此而从《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折入“乾嘉新义理学”研究。言既至此,特别怀想当年在台北与张寿安、张丽珠、杨晋龙、郑吉雄、刘又铭等友朋切磋清代学术,向吴哲夫、昌彼得、林庆彰、胡楚生等先生请益,与仕华、彦文、佩琪游览九份老街,贝宇一家为余过生日的种种情景。此时此刻,恍如隔世。
迄今之“乾嘉新义理学”之研究,多从解构宋学之“义理”概念展开。宋学以形上之“心性”探讨作为“义理学”之模式。倡言“乾嘉新义理学”者,则转换视野,破除成见,从赋予“义理”新内涵破局。如张寿安言:“我们不妨以宏观的态度把‘义理’一词视为儒学思想。”胡楚生言:“义理之名,为思想、义趣、理念、意旨之总称。”从这一层面来理解“义理”之概念,承认乾嘉学者同样有“义理”,事实上是并不困难的事。余虽对朱维铮先生极为钦佩,但对他所言乾嘉时期“思想界的沉闷达于极致”一语无法认同。正如福柯所言:“思想存在于话语的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起来,但却为日常的行为提供了动力,甚至在最愚蠢的制度中也存在思想,甚至在沉默的行为中也存在思想。”关键在于如何发掘那一时代思想的表现形式。张寿安言:如果“坚持使用‘理学’这个秤,去衡量乾嘉义理学,不但要大失所望,更可以坦白而直截的说,这根本是缘木求鱼。”诚哉斯言。其所著《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便以坚实的考据、绵密的论证,呈现出被视为“经生之绪余”的十八世纪的礼学考证中是如何活跃着关于“时代议题”之讨论,“其迫切性与崩裂性令人扼腕”。余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亦旨在掘发在这部被视为“汉学思想的结晶体”的目录学著作,又是如何杂糅着帝王意志与学者意识,从一个侧面映现出十八世纪的思想脉动的。
然而,前述研究虽然揭示了乾嘉时期并非思想荒漠,但却普遍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即“清代新义理学中是否亦有形上之思?”而直面这一问题的就是彬彬君的这部《〈周易〉诠释与清代新义理学的思想源流》书稿。
《易》原本是上古卜筮书之泛称,战国时代《易传》形成,在六十四卦卦象变化的组合规律中演绎出了一套统贯天人的哲理体系,牟宗三《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函义》中说:“《周易》全是以‘卦象’或‘卦号’来表象世界。卦象间的关系即是表示世界的关系;解说卦象即是表示吾人对于世界之知识。”此论实阐述了《周易》诠释学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一,用来表象世界的“卦象”或“卦号”均是抽象符号,由此决定了关于《周易》的诠释有极大的空间,诚所谓“《易》无达占”,“《易》道广大,无所不备”。其二,“解说卦象即是表示吾人对于世界之知识”。这里的“吾人”即解说《周易》者,换言之,如何解说卦象,取决于“吾人对于世界之知识”的状态与程度,此论颇近于伽达默尔的“前见”之说。高亨先生言:“《易传》解经与《易经》原意往往相去很远。”余固不知何为“《易经》之原意”,亦不知如何抵达《易经》原意之彼岸,惟知“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个释《周易》者也会有一千个关于《周易》“原意”的表达。
如姚著所言:“由于《周易》哲学的完成,使得《周易》成为儒家元典中独一无二的具备统贯天人的完整哲学体系之著作。”而关于天人关系的哲学讨论,不可避免地以形上论辨为主要途径。《四库全书总目》说:“夫《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心性之理未尝不蕴《易》中”。故彬彬认为:“汉代以降的学人,凡言及义理之学,皆不可避免地援《周易》为元典资源,对其不断进行‘创造性诠释’。”无论是汉代象数派的“象能尽意”,还是魏晋王弼等“得意忘象”,“其实都无非旨在探讨形上的本体论问题乃至世界和宇宙的生成演运模式”。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亦无不从《周易》诠释中衍出。由此,姚著论断:“在一定意义上,研《易》者几无不涉及义理。易学研究本身就可以视为中国传统的义理学之一大统系。”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来研究乾嘉学者的《周易》诠释,由此直接切入乾嘉新义理学中的“形上之思”视域。
关于清代学者的《周易》诠释,当代学界创获已颇丰富。如汪学群之《清初易学》、林忠军等著《清代易学史》等,已展开叙述了清代易学沿革之波澜起伏。于王夫之、胡煦、黄宗炎、惠栋、张惠言、焦循等人的易学研究亦有广泛讨论。彬彬君又出以新意,着力发掘清代学者在《周易》诠释中的形上之思,揭示乾嘉学者虽然以“由训诂以明义理”,由小学以通经明道,为学术宗旨,与宋儒“摆落训诂,直寻义理”别分两途,但同时亦以《周易》诠释为主要路径,讨论“性与天道”的相关核心范畴。如果说,张寿安以《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呈现了在乾嘉考据中活跃着丰富的思想,那么,姚彬彬的《〈周易〉诠释与清代新义理学的思想源流》则以清儒的《周易》诠释呈现了清儒的义理论辨。两者互为补充,构成更为完整的“乾嘉新义理学”的思想版图。
余与彬彬君因“乾嘉新义理学”而相识相交,又因诸多喜好与观念相近而成忘年之友。彬彬君聪慧敏锐,不羁不俗,文史功底扎实,于中西哲学思想多有涉猎,又兼研习佛学,颇悟禅理,故于思想史研究别具优势。其书稿既深入易学诠释,又返身于“乾嘉新义理学”之大格局,剖析源流,辨章学术、评骘精当,颇有可观之处。称之为“入乎《易》内,出乎《易》外”,诚如其分。
余不敏,于“易学”领域向怀敬畏之心,平生向未作专门研究。彬彬君书稿既成,丐余一言以序其端,余逊谢不获已,谨述余于《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理学”之治学经历与阅读过程中之所思所想,勉之为序。
辛丑年十二月初三
于汉口滨江苑

书名:《周易》诠释与清代新义理学的思想源流
作者:姚彬彬
ISBN:978-7-5227-3381-4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内容简介
本书系作者所主持的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题成果,全书合计30万字,由周积明教授作序推荐。
清代学术的“汉宋之争”说法由来已久,就本义而论,“汉学”非特指训诂考据,“宋学”亦非专指思想义理;宋儒于文献考据研究早已开启先河,汉儒亦自有其义理关怀向度。乾嘉学术以重振“汉学”为宗旨,同时颇受汉儒义理学的影响。本书提出,汉学中的《周易》象数学之复兴,是“清代新义理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清儒虽有为古典经籍去神圣化、视“五经”为先秦遗献之倾向,但仍普遍认定“《易》以天道而切人事”。统贯天人的超越性追求,实为中国传统一切学问的精神底蕴,在清学中亦莫之能外。
作者简介

姚彬彬,1981年生,山东龙口人。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先后师从宋立道、麻天祥、冯天瑜三先生。现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任研究员、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已出版《现代文化思潮与中国佛学的转型》等著作6部,于《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各级课题6项,多次获省部级科研奖项。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佛教哲学。
目录


正文选读
以清代乾嘉学术较为忽视义理学的探索,是长期以来在学界颇有影响的一种观点。在1990年代,有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提出“清代新义理学”(亦称“乾嘉新义理学”、“乾嘉义理学”等)这一概念,多年来引发争议和讨论。事实上,回溯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史,若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侯外庐、钱穆等,皆曾对此问题有所探讨,他们对清儒的义理学成绩的高下得失,虽有多种不同意见,但于“乾嘉学者是否有义理学关注”这一问题,本无原则性争议。给予清儒义理学以严厉的负面评价的看法,主要来自于20世纪后半叶港台地区的新儒学学者,迄今仍有一定影响。故有关“清代新义理学”的学术争议,与百年学术“新旧之争”乃至古典传统的“汉宋之争”的文化背景密切关联。
清代学术的“汉宋之争”说法由来已久,实则就本义而论,“汉学”非特指训诂考据,“宋学”亦非专指思想义理;宋儒于文献考据研究早已开启先河,汉儒亦自有其义理关怀向度。乾嘉学术以复兴“汉学”为宗旨,同时颇受汉儒义理学方面的影响。汉代的易学象数学之复兴,也是乾嘉汉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就历代易学“二派六宗”的“二派”而言,象数派以“象能尽意”,义理派以“意在象外”,其实都无非旨在探讨形上的本体论问题乃至世界和宇宙生成演运模式,都是广义上的“义理”之研究。在一定意义上,研《易》者几无不涉及义理,易学研究本身就可以视为中国传统的义理学之一大统系。象数易学研究及对《周易》文本的新诠,对“清代新义理学”的构建有重要影响。
张岱年等早曾提出,清儒戴震等承继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气论哲学,气论哲学自有其形上关注维度。由这一线索来回溯气论哲学的学说渊源,可见先秦《易传》哲学本为“气论”观念之端绪,汉代象数易学的“卦气”说亦与汉代的气论哲学构建相关联。基于象数易学的“以气为元”论是汉代哲学的主要构成部分,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儒孔颖达、张载等的哲学思想形成,宋儒张载更正式创建了一套体大思精的“气本论”体系。汉儒的易学象数学与宋儒张载的“气本论”哲学均对清代新义理学有直接影响。清代汉学的奠基者惠栋承继汉易的“以气为元”论,并立足于这一学说对宋儒义理观念有所批评和驳议;戴震的义理学之形成很可能受到过惠栋易学观念的一定启发,他接续张载、王夫之的气本论哲学理路,明确质疑宋儒天理观念的合法性,并在人性论上主张“理者存乎欲者”之说,《周易》中的“生生”等观念为戴震哲学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和古典文本依据。其后的乾嘉诸儒,亦多有持气论之宗旨者,焦循以戴震气论思想为问题出发点,并基于汉儒虞翻、荀爽的象数理论,建构了“旁通、相错、时行”等象数学新范式,将《周易》视为具有严密内在逻辑的整体运行结构,从而与天道循环的规律乃至世间森罗万象、人情物理相通贯,建构出一套较系统的自然主义哲学。要之,《周易》诠释及相关易学思想,堪称乾嘉义理学“气本论”的重要来源。
清儒治学承继汉儒的“以经释经”之法并继有发明,其中寄托了他们视三代文献为整体,希图从中探寻社会理想图景的义理思考向度。汉儒的“以《易》解《礼》”传统,亦在清代易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张惠言《虞氏易礼》一书,立说专宗虞翻,参以郑玄、荀爽诸家之说,认为《周易》中包含大量的周代礼制内容,可以与《周礼》相互印证,其说又隐隐与清学“以礼代理”思潮相呼应。清初胡煦易学兼容汉宋,已提出了“以《易》解经”的理论模型;焦循基于“旁通”说演绎出“以《易》解经”的经学解释体系,以《周易》涵摄群经微言大义,认为《周易》中蕴含了普遍性的深妙哲理,《论语》《孟子》中之说则为儒门所论列的具体事相,可以相互印证,由此,《周易》被焦循视为儒家经典共同的形上学天穹。清代中期以来的“以《易》解经”之风气,本有宋学渊源,其影响亦不限于文化精英学者群,于祖述周子的民间儒学群体太谷学派中,亦有见之,该学派的晚近后学刘大绅、缪篆、杭辛斋等又有进一步之发明。
要之,清儒或参以《周易》象数,或通过《周易》文本新诠,在义理学上进行探索,确有所成。他们虽有为古典经籍去神圣化,视“五经”为先秦遗献之倾向,但仍然普遍认定“《易》以天道而切人事”,其中存在贯通天人之际的形而上指向。任何学术体系达到了一定高度之后,都不可能忽视或回避形而上之“道”的问题,统贯天人的超越性追求,实为中国传统一切学问的精神底蕴,在清学中亦莫之能外。
虽然,乾嘉以降诸家,除戴震之外,其说或略嫌粗糙,或习于附会,单纯从哲学深度的造诣上衡量,其得失之处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他们所求之鹄的,在于一“通”字:求“天理”与“人欲”之“通”,求天道与人事之“通”,乃至求中西学问之“通”。这一义理学向度,既继承了既往宋学义理径路蕴含的人文理性成分,又扬弃了其文化保守主义乃至人性禁欲主义倾向;更是对明末清初诸家思想宗旨的演进和接续,承先启后,开显中国哲学“近代性”之曲折径路,当自有其思想史和哲学史的重要地位。
部分信息转载自公众号“湖大历史文化学院”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汉语研究与社会应用实验室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
责任编辑:李玉晴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