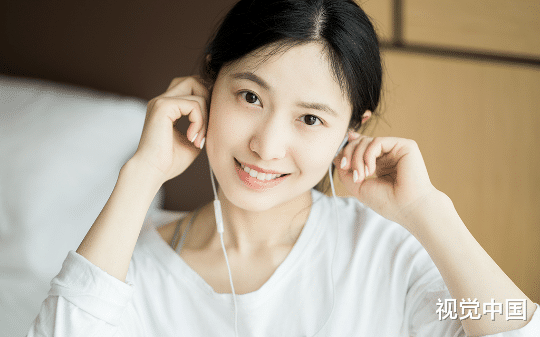第1章
1980年,肿瘤研究所。
“王教授,我已经申请了强制离婚,我愿意加入您的医疗研究项目组!和您一起去沪市攻克国内脑瘤难题。”
孟云淑神色坚定朝面前的王院士开口。
听到这话,王院士神色一愣:“云淑,你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你能加入,我很高兴!但你申请强制离婚的事,会不会太冲动?你丈夫知道吗?”
孟云淑垂下眼眸,苦涩一笑:“他应该求之不得。”
没人比重活一世的孟云淑更清楚,她的丈夫贺泽铭从不爱她这件事。
前世,她为了家庭拒绝了王院士的邀约,自此成为家庭主妇,相夫教子,平淡人生。
最终丈夫步步高升成了首长,儿子从商成了大企业家,她沾了父子俩的光,也算得上一生圆满。
直到五十岁那年,她患上脑癌晚期。
重病弥留之际,孟云淑才知道自己这一生活得多可笑。
她自以为是性子冷淡的丈夫贺泽铭,其实心里一直没有放下他的初恋。
就连她一手养大的儿子,也在她的病床前跟贺泽铭说:“爸,等妈走后,你就和洛姨领证吧,我心里早将她当亲妈了……”
她还没死,丈夫和儿子已经在准备迎接别的女人进门了。
那一刻,孟云淑后悔了。
她后悔对贺泽铭一见钟情执意要嫁给他,更后悔为他拼死生下儿子。
最后悔的就是为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所幸今生,她还有重选一次的机会。
最终,王院士没有再多问,只说:“那你回去收拾一下,这段时间先来研究所熟悉项目,下个月我们就正式搬迁去沪市。”
“好。”
跟王院士确定好后,孟云淑走出了研究所。
看着路边极具年代感的国营饭店和供销社,孟云淑心里总算有了重生的实感。
她骑着二八大杠,一路往家里去。
刚到门口,迎面跟单手抱着孩子回来的男人撞了正着。
正是她的丈夫贺泽铭,凛北军区旅长。
此刻他刚出完任务,身上笔挺的军装甚至还没换下来。
四目相视,贺泽铭却是拧起眉头:“你今天怎么没去托儿所接儿子?把他一个人放在洛老师家!”
他怀里的贺霖,此刻正气鼓鼓瞪着她,水汪汪的眼里含着控诉。
看着他们父子俩如出一辙的脸色。
孟云淑的心重重一沉,这一刻,她仿佛又回到了前世。
前世每次有矛盾,他们父子总是同仇敌忾,将她视作这个家的外人。
今生,她已经彻底累了。
回过神来,孟云淑攥了攥手,轻声说:“是贺霖自己说喜欢洛老师,想在洛老师家里住。”
闻言,贺泽铭一愣,随后皱起眉头:“五岁孩子说的话,你也当真?”
孟云淑听在耳里,却没多作声。
前世的她确实不把孩子的话当真,如今她却知道,哪有什么童言无忌,孩童不懂掩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话。
没在门口多留,贺泽铭先一步推门回家。
晚上,儿子早早在屋里睡下。
孟云淑洗漱完出来,却看见贺泽铭正站在桌前,不知在看什么。
听见动静,贺泽铭转过身来,他眸色黑沉:“你要回研究所工作?”
孟云淑这才看清,他手里捏着的,是她研究所的工作通行证。
沉默片刻,孟云淑点了下头。
贺泽铭神色沉了几分,却也没说什么:“贺霖已经上幼儿班了,你回研究所上班也没事,但平时别为了工作忽略儿子。”
他以为她只是回了研究所上班,并不知道她的项目组准备搬迁去沪城。
见状,孟云淑应了声‘好’,并没多说。
她了解贺泽铭的性子,如果知道她要抛下孩子家庭走,他肯定不会答应的。
所以她只能偷偷离开。
一个月后,当她随研究项目组去沪城时,她申请的强制离婚书也会同步到贺泽铭手里。
第2章
次日清早。
孟云淑醒来时,贺泽铭已经不在家,家里只剩下她和贺霖。
贺霖才五岁,正是活泼好玩的时候,床上地上,他的玩具书本扔得到处都是。
孟云淑正准备收拾满地狼藉。
冷不防,耳朵上被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石子重重击了一下。
转身看到贺霖手里的石子,孟云淑下意识冷斥:“贺霖!妈妈跟你说没说过,不能玩一些伤害到别人的东西?”
平日里,贺霖顽皮不好带,孟云淑对他管教得也是颇为严苛,因为不想他以后长大走上歧途。
此刻被训斥的贺霖低着头,眼里闪着泪花却不满嘀咕:“妈妈好凶,洛老师就不会这么凶我。”
细微的声音入耳。
孟云淑当即愣住,心冷不防一揪。
余下的话顿时堵在了嗓子眼,再说不出一句来。
她看着儿子眼神中对自己的抗拒,再想到儿子在洛清清面前的懂事。
这一刻,她泄了气,也没了管教的心思。
“书包背好,该送你去幼儿园了。”
贺霖一愣,眼里闪过诧异。
这还是妈妈第一次没有惩罚他。
但孩子的心思多变,转瞬就变成欢喜,他忙不迭进屋背上了书包。
一路将孩子送到了幼儿园。
孟云淑没有像平日里那样千叮万嘱,调头就走了。
她直接去了研究所里报道。
多年没有参与研究,孟云淑一整日都在看国内外最新的脑肿瘤研究资料,想尽快融入项目组。
等她下班时,已经天黑了。
急匆匆回到家的时候,贺泽铭已经把孩子接回了家,洗完澡给哄睡觉了。
男人关上儿童房的门,冷冷瞥了刚回家的孟云淑一眼,倒是没多说什么。
进了卧房。
贺泽铭张口却是跟她说:“今年中秋节我有任务,又得你自己回家了。”
听见这话,孟云淑神色一顿,紧抿了下唇:“我爸妈已经很久没见你一回了。”
前世,过年过节,贺泽铭鲜少陪她回娘家一趟。
她独自回去时,邻里街坊都传闲话,说她是不是和贺泽铭感情不和。
孟云淑自己可以不放心上,可父母在家里的面子上,总归不太好看。
哪知道,贺泽铭却误解了她的意思。
他当即从怀里掏出一封鼓囊的信封来:“你放心,我知道你爸妈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是我这几个月的工资,你拿去买点补品送去。”
那里面,起码有上百块。
可这暖黄色的信封,却生生刺痛着孟云淑的心。
她没有接,眼眶一瞬泛了红:“贺泽铭,在你眼里,我爸妈就是图你的钱吗?”
父母关心的从来就不是他拿给他们多少钱,而是他有没有心!
贺泽铭淡漠的神色看她时,却透着莫名。
“这些年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你突然之间闹什么?拿着,我明天还要早起出任务。”
说完,他直接将钱放在了桌上,转身就去洗漱了。
总是这样的。
孟云淑的怒火,孟云淑的情绪总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他没有任何反应。
前世,孟云淑还认为这是他情绪稳定。
可现在她明白了,是他压根就不在意。
他从不在意她的喜怒哀乐,所以才会不动声色。
心口如同压了一块大石,闷堵得孟云淑几乎喘不上气来。
直到她余光看见了墙上挂着的日历。
“孟云淑,再忍忍吧。”
“只剩最后29天了。”
这样安抚过后,她才渐渐平缓下来自己的情绪。
一夜同床异梦。
隔天清早,孟云淑醒来时,贺泽铭已经出门了。
她照常收拾好,送儿子去幼儿园。
路上,贺霖看着道路两边鲜红的宣传标语,突然问孟云淑:“妈妈,什么叫结婚?”
孟云淑骑车目不斜视,回答:“结婚就是和爱的人组成家庭。”
贺霖若有所思,几乎是脱口而出——
“那爸爸又不爱你,为什么会跟你结婚?”
第3章
自行车猛地停在路边。
孟云淑被这话击中,顿时僵在原地,她脸色泛白,却回不上一句话来。
是啊,他不爱她,又为什么要跟她结婚呢?
当初相亲时,她一眼看中了贺泽铭,可贺泽铭其实是拒绝过她的,是她追着他跑,最终让他松口娶了她。
前世的孟云淑总以为是自己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可她重活一遭才想明白,男人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的人,就算勉强结婚了,他也是不喜欢的。
沉默半晌,孟云淑转头看向儿子:“孟霖,那如果我和你爸离婚,就是分开,以后都不在一起了,你选谁?”
贺霖想也不想就回:“当然是我爸!”
稚嫩的声音,如细针狠狠刺在孟云淑的心上。
她怀胎十月,细心养育五年的儿子,对她是真的没有半点留恋。
孟云淑回过头去,冷风迎面吹来,将她通红眼眶里的泪意吹散干净。
她重新蹬起自行车往前走。
“好,我知道了。”
……
下午下班后,孟云淑收拾东西准备带儿子回娘家。
谁料,贺霖却不肯走:“我不想去,姥姥家一点不好玩,我可以去洛老师家里住!”
他毫不掩饰对洛清清的喜欢。
一股强烈的无力疲惫感袭来,孟云淑定定凝视他:“你想清楚了?”
贺霖重重点了下头:“当然。”
孟云淑垂眸:“好。”
随即,她直接就将贺霖送到洛清清家里。
出发前,孟云淑去通讯局给贺泽铭打了个电话告知这事。
贺泽铭一听,语气沉了下来:“胡来!贺霖才多大,你一而再再而三把他扔到洛老师家里,你简直是给洛老师添麻烦!”
洛老师、洛老师。
贺泽铭口口声声都是站在洛清清的角度想。
孟云淑捏紧了话筒,半晌才哑声道:“孩子不肯走,我能怎么办?”
贺泽铭却冷笑:“我看你就是图自己省心,不想带孩子。”
这么多年,贺泽铭军人身份鲜少在家,都是她把孩子拉扯大的。
孟云淑心狠狠揪起,她不知道他怎么能说出口这种话。
可辩驳的话到了嘴边,却没能出口。
最终,她红着眼,咽下喉头无尽委屈和酸苦,只说:“总之孩子我已经送到洛清清家了,你到时候先回来的话,记得去接。”
说完,孟云淑再不顾电话那头贺泽铭是什么反应,直接挂断了电话。
然后她憋着眼泪,坐了一个小时的客车,抵达了乡下老家。
在看见孟云淑独自回来时,孟家父母一愣:“怎么今年就你一个人?贺霖那孩子都没一起过来?”
看着父母期盼又失望的眼神,孟云淑的心也狠狠揪起来。
她攥紧了手里的行李包,最终开口说道:“爸妈,我打算和贺泽铭离婚了,孩子归他。”
“再过20天,我就要跟着以前的项目组去沪市做研究。”
她一口气将话都跟父母说了。
随后,她低着头,紧张等待着父母的责骂。
等了许久,等到的是孟母将她轻轻抱住:“妮儿,你这些年,受了很大委屈吧?”
孟父抽着焊烟,默默叹着气:“这些年他怎么对你的,我们都看在眼里,离!你要离婚,爸是一万个支持!别担心外面的闲言碎语,只要你过得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父母的体贴关怀让孟云淑强撑的心一瞬崩塌。
手里的行李包啪嗒落地,她再也忍不住,趴在孟母的怀里放声大哭,释放自己前世今生所有的委屈来。
……
在娘家待了三天。
孟云淑提着父母给她准备的大包小包回了家属院。
谁料,刚到院子里。
正在玩耍贺霖,看见她后突然神色一慌冲上来,张开双手拦住她。
“妈妈,你不能进去!”
刚坐了一个小时车,孟云淑疲累得很,“别闹了,让妈妈进屋。”
“不可以!你就是不可以进去!”
孟霖眼神闪躲着,却执拗不让她进去。
孟云淑眉心一跳,她推开贺霖,大步往里走去。
到门口看清屋里的一幕,孟云淑身形僵住,瞳仁骤然收紧。
只见屋内沙发上,贺泽铭背对她。
而洛清清正躺在他怀里,脸色潮红!
孟云淑脸色一白,攥紧了手问:“你们在干什么?”
第4章
听见声音,屋内的两人迅速分开。
洛清清慌张看向她解释:“嫂子你回来啦,贺大哥前两天为了救我手臂受了伤,要换药,我心里过意不去,这才主动过来帮忙换药……”
闻言,孟云淑这才看见贺泽铭的左手手臂缠着绷带。
可他们刚刚那姿势,哪里是换药的姿势?
孟云淑喉头哽了下,没忍住冷讽:“换药需要躺在怀里吗?”
话音落地,洛清清眼眶发了红,看向了贺泽铭。
接着,贺泽铭站了起来,脸色黑沉至极:“孟云淑,你不要一回来就像个疯子,洛老师确实是在帮我换药,刚刚是一个意外。”
疯子。
原来在贺泽铭的眼里,就是这么看她的。
孟云淑僵在原地,她很想再问他一句:怎么就那么恰好意外扑在他怀里去了呢?
可看见他和洛清清站在同一边,冷眼看过来的姿态,她喉咙像是被刀子割过,半个字都发不出声来。
她攥着行李包的力道紧了又松。
最终,孟云淑轻扯唇角:“原来如此,那我还得多谢洛老师。”
贺泽铭眉头皱起,还要再说什么。
洛清清当即起身讪笑道别:“既然嫂子回来了,那我就先走了。”
她走到院子里时,还不忘温柔地对贺霖说:“贺霖!老师走了,你记得要好好写作业哦。”
“好,我会的!”
向来调皮叛逆的儿子,在洛清清面前乖巧得不像样。
这一刻,孟云淑忍不住想,或许真的是自己这个妈做得太失败了吧。
她苦涩低头,踏步进了屋。
身后手打着绷带的贺泽铭却也跟了进来。
哐当一声门合上。
贺泽铭面色严肃看向她:“孟云淑,你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
孟云淑继续整理手上的行李包:“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紧接着,贺泽铭单手夺过她手里的行李包,沉声问:“你之前是不是跟孩子说了,离婚不离婚这种胡话?”
心口倏然一怔。
孟云淑看着被他丢在一旁的行李包,垂下眼眸,没有说话。
这便是默认了。
贺泽铭拧起眉头,语气更是冷了几分:“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可以跟我说,把大人之间的事在孩子面前乱说,你还有没有身为一个母亲的自觉?”
闻言,孟云淑静静抬眼看向面前的男人。
这张脸依旧俊朗非凡,和初见时别无二样。
一样冷漠,一样在他脸上看不见对她的一丝爱意。
孟云淑攥紧了手,红着眼问:“那你呢?你有身为我丈夫的自觉吗?”
“结婚以来,你没跟我过过一天结婚纪念日,你也从来没有送过我任何礼物,没有跟我说过一句情话!”
“贺泽铭,我们是夫妻,夫妻间最重要的不是爱情吗?”
她再也没能忍住,将前世今生所有的委屈向他控诉。
可换来的,是贺泽铭拧紧眉头冷声说:“年轻人才搞这种东西,我们都结婚六年了,好好过日子就行,在意这些形式主义做什么?”
所有的涩苦尽数堵在嗓子眼里。
这一刻,孟云淑心彻底如坠冰窖。
因为他此刻口中不屑的‘形式主义’,二十年后,他悉数给了洛清清。
前世,在她病入膏肓躺在病床上时,她亲耳听见他们父子两在商量要给洛清清送生日礼物,言语间对洛清清的喜好一清二楚。
心一点一点拧成结,连呼吸都好似带着腥甜。
可孟云淑张张嘴,最终却也只是点头:“好,我知道了。”
她已经彻底认清,前世今生,他确实从不爱她这件事。
争辩再多,也没有意义了。
好在,好在再过17天,她就可以离开了。
第5章
接连几天,孟云淑基本上都在研究所里加班。
可贺泽铭除了能去接孩子放学外,其他一切还是照旧。
这天晚上,孟云淑刚给贺霖带去洗澡,等都收拾好一切,疲惫回到屋里。
一进屋,却听见贺泽铭的斥责:“我说没说过,不要因为工作耽误家庭?你倒好,天天这么晚回来?怎么,你们研究所离了你就转不了了?”
“这几天是有我在家里,以后你再这样,我看你这工作也别干了,好好在家待着!”
一如往常带着命令的语气。
这一刻,孟云淑好似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下属。
这就是他们前世近三十年婚姻的相处模式。
孟云淑盯着他的绷带,也不想跟他再争,她只叹了口气:“好。”
自从上次的争论过后,她已经不想在他身上寄任何期盼。
见她难得顺从,贺泽铭脸色好转不少,随即开口:“明天我能拆绷带了,你陪我一起去趟医院。”
孟云淑没有拒绝,点头又是说好。
随即,她上前去,开始解开贺泽铭的衣服。
由于贺泽铭手上打着绷带行动不便,这几天都是她帮忙的。
她就这么熟稔一颗颗替他解开纽扣,脱下外衫。
前几天他任凭她摆弄,没甚反应。
可今日挨得近时,孟云淑能明显感受到男人明显变重的呼吸。
抬眸,她对上了贺泽铭隐晦的眸色。
夫妻多年,孟云淑自然知道贺泽铭要干什么。
可在他即将贴近她身躯时,她先一步往后退去:“很晚了,睡吧。”
熄了灯,孟云淑上坑后,背对贺泽铭睡下。
黑暗中,她能明显感受到贺泽铭沉沉落在她身上的目光。
可她闭上眼,不再理会。
一夜过去。
次日清早,孟云淑便陪着贺泽铭来到了解放军医院。
里面,医生正在给他拆绷带,门口护士在叮嘱孟云淑。
“孟同志,贺旅长回去后,还是得清淡饮食,注意休息,不能劳累。”
孟云淑点头,一一记下来。
就在这时,医院大厅突然一阵骚动,送进来好几位急救病人。
孟云淑听到有人喊道:“国营饭店起火了,赶紧去救人……”
国营饭店起火!
这几个字猛然激起孟云淑的记忆。
她记起来,前世这场大火波及到了脑癌研究所,虽然没伤到人,但烧毁了很多重要资料,让国内的脑肿瘤研究倒退十年。
孟云淑不敢想下去。
她急不可耐,也不管贺泽铭还在拆绷带,起身往外跑去!
抵达起火现场,浓烟滚滚。
由于风向,此刻火势已经往研究所蔓延而去。
所有人都惊慌往外跑,只有孟云淑逆着人流跑去研究所。
“哎——孟同志!!”
身后有人在喊她,可她已经顾不上了,披着打湿的被单就毅然决然冲进了火场。
那里面可有着整个项目组好几年的心血,她绝不能让它们就这样付之一炬……
等孟云淑抱着一堆资料从火场内出来,火已经被扑灭得差不多,到处都淌着水,湿漉漉的。
她满脸黑灰,不过脸上却是庆幸的笑。
前方的王院士看见她出来,松了口气,却还心有余悸。
“云淑,你没事就好,东西没了可以再研究,人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
孟云淑擦擦脸上的灰,却是摇头:“不,资料比我重要。”
王院士无奈看她,随即又想起什么来。
“哦对了,刚刚贺旅长也来了,我告诉他你去抢救资料了,只不过……”
王院士话到嘴边又打住。
孟云淑一愣,贺泽铭也跟来了?不等她多问,转过头已经看到了贺泽铭。
此刻,他正搀扶着一名中年妇人从饭店走过来,而他身旁,是亦步亦趋的洛清清。
孟云淑一瞬明白了王院士的欲言又止。
只不过……她的丈夫急着去救别的女人去了。
第6章
孟云淑收回视线,很快和王院士整理资料。
所幸重要的都保了下来。
就在这时。
她身后传来贺泽铭满是不悦的怒斥:“孟云淑!你做事未免太冲动!知道你擅自跑进火场的举动有多危险吗?”
没有关心,没有慰问。
即便她刚从火场九死一生逃出来,他对她,永远只有指责。
孟云淑脸色有些难堪。
倒是面前的王院士看了看两人,缓声开口:“贺旅长,云淑也是心急,现在人也没事,你们两人好好谈谈,别吵架。”
说完,王院士带着资料很快离去,给他们留出空间来。
孟云淑回过神,目光一点点落在他的手臂上。
那刚拆完绷带的手臂上,再度添了几道鲜红的伤痕。
旧伤刚好,又添新伤。
这两次伤都是为了救洛清清,可见洛清清对他贺泽铭的重要性。
刺眼的红灼痛着孟云淑的双眼,她轻声问:“贺旅长既然知道危险,怎么自己也奋不顾身跑进火场?”
孟云淑进的是没有完全起火的研究所,可贺泽铭进的,是火势正盛的国营饭店。
贺泽铭脸色冷沉:“我是军人,进火场救人是我应该做的!”
听见这话,孟云淑目光又落在不远处毫发无伤的洛清清身上。
她相信贺泽铭身为军人本能会进火场救人,可是能让他这么拼了命去的,更是因为在火场里的人是洛清清,是他放在心尖上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在火场被呛的浓烟,也比不上此刻心口的憋闷。
孟云淑缓了许久才开口:“就跟救人是你职责一样,抢救资料也是我身为研究员的职责,你没资格来指责我冲动。”
语罢,她直接转身往研究院同事那边走去。
后方的贺泽铭盯着孟云淑离去的背影,眼神变了几变。
从前孟云淑的心思很好猜,无非是对孩子的管教,和怪他常年不在家。
可如今,他已经看不透她到底在想什么了。
心里,总有一种他快要抓不住的感觉。
……
从研究所回来。
孟云淑洗完澡回到屋里,定定看着日历。
三天后,是儿子贺霖的生日。
十天后,是孟云淑去沪市的时间,也是她和贺泽铭强制离婚书下来的日子。
房门吱呀一声。
贺泽铭推门而入,见她盯着日历出神,只当她是在看儿子的生日。
他沉声提醒:“贺霖念叨着想吃生日蛋糕很久了,他生日那天,你记得买个回来给他吃。”
贺霖小时候吃糖把牙都蛀坏了,因此孟云淑这两年都管着他不让吃甜食。
不过……孟云淑想到今年可能是自己陪儿子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了,也就点了头:“好。”
贺霖生日当天。
孟云淑放下手头上的事,早早下班来到了蛋糕店里。
她跟店主商量好,借用场地,自己亲手做了一个蛋糕。
奶油蛋糕做得很完美,孟云淑提着回去准备好好给儿子庆贺一番。
谁料,刚到家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了生日快乐歌。
推开门看去,只见院子里,贺泽铭和洛清清已经捧着蛋糕在给贺霖庆祝生日。
这一瞬间,好像他们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三口。
听见动静,三人的目光齐刷刷过来。
洛清清立刻识相地起身:“嫂子回来了,正好,一起给小霖庆祝生日吧。”
这话的口吻,更显得她像个外来者了。
贺泽铭解释道:“洛老师早就提着蛋糕来了,贺霖急着想吃,所以就没等你先庆祝了。”
“没事,是我回来得晚了。”
孟云淑走过去,将蛋糕放到桌上打开,准备一起吃。
谁知刚打开,贺霖看了一眼,当即瘪嘴:“妈妈的蛋糕没有洛姨买的好看!我不喜欢!”
说着,他手一推。
啪嗒一声!
孟云淑精心制作的蛋糕,就这么重重掉在了地上!
如同她此刻的心,落个稀碎。
第7章
屋内气氛一瞬寂静下来。
孟云淑盯着地上那已经瘫成一团的蛋糕,半晌没能回过神来。
贺泽铭则当即拧起了眉头,板着脸怒斥。
“小霖,你这是在做什么,赶紧给妈妈道歉。”
洛清清也打圆场:“嫂子,孩子肯定也不是故意的,你别往心里去。”
他们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维护着贺霖,衬得她更像外人。
而贺霖小小的身影坐在凳子上,却是瘪嘴小声嘀咕:“我就是不喜欢妈妈的蛋糕,哪里错了。”
见状,孟云淑攥了攥手,最终轻声叹气:“没事,不喜欢就不吃了。”
她蹲下来,亲手将自己做的蛋糕,一点点收拾干净。
收拾完,孟云淑落下一句‘你们玩’后,就转身进了屋。
屋外,贺泽铭看着她沉默的背影,心中那种不对劲的感觉更加强烈。
犹疑片刻。
贺泽铭踏步追着进了屋,关上门他叹了口气:“贺霖是做得不对,但今天毕竟是孩子生日,你跟他置气做什么?一个蛋糕而已,明年你再给他买就是了。”
孟云淑背对着他,没有吭声,眼泪却落了下来。
没有明年了,她这辈子,已经不想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
孟云淑‘嗯’了一声,只说:“我只是太累了,你们玩吧。”
贺泽铭定定看了她几眼,才转身离开。
……
次日早上。
孟云淑还是照常起床,照常要送贺霖去幼儿园,可到了床边,叫了孩子半天叫不醒。
一捂额,才发现贺霖额头竟然烫得很。
孟云淑脸色一变,立刻喊贺泽铭一起抱着孩子去了医院。
解放军医院儿科。
医生诊治完给孩子吊上水后,开口:“是急性肠胃炎,孩子都吃了什么?”
孟云淑想了想,将昨天给贺霖准备的饭菜一一跟医生说了。
顿了一顿,她又记起来:“他还吃了个蛋糕。”
这话一出。
病床上脸色还煞白的贺霖,当即尖着嗓子喊:“不可能!绝对不是洛老师的蛋糕,肯定是妈妈给我吃的饭有毒!”
孟云淑一瞬僵住,眼底满是不可置信。
贺霖就这么喜欢洛清清……为了维护洛清清,他竟然恨不得把病因归到她这个亲妈身上。
寒意从她的脚底蔓延心口。
贺霖到底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即便是昨天晚上他糟蹋了她的心意,今早看见他生病,孟云淑忙上忙下,依旧心急得很。
可贺霖却一次又一次用行动化作刀,狠狠刺在了她本就伤痕累累的心上。
而医生听了这话,语气沉了几分带着责怪:“你这当妈的也是心大,估计是孩子昨天吃得东西太杂了,以后注意些。”
“好,谢谢大夫。”
送走医生后,孟云淑静静看了一眼不敢看她的贺霖。
她没有多说什么,提上包迈步要走。
没想到刚转身,就碰上缴完费回来的贺泽铭,他脸色当即一沉。
“孩子还病着,你这是去哪儿?”
孟云淑深吸一口气,对上他不悦的视线:“你今天不是还在休假吗?有你在医院照顾孩子,我要去上班了。”
这话一出,贺泽铭脸色更为黑沉。
“孟云淑!你儿子在医院躺着,你还有心思去上班?”
闻言,孟云淑心不住沉了沉。
可不等她回话,病床上的贺霖已经开了口:“爸爸,妈妈好凶,好吓人!我不要她陪,我想让洛老师来陪我……”
孩子弱弱的声音响彻在寂静的病房里。
贺泽铭眉头皱起,脸色一变。
孟云淑轻扯嘴角,不再多说什么,直接绕开他迈步离开病房。
她现在已经清晰认知到,他们父子俩的心不在她身上,她做再多都是徒劳。
倒不如把自己所有心思只放在研究上。
半个小时后,研究所。
孟云淑刚踏入大门,迎面就见王院士神色匆匆走过来。
“云淑,上次火灾研究所被烧毁了不少设备,接下来的实验不好继续。”
“所以你回去收拾一下,我们决定提前去沪市了。”
第8章
“哪天走?”
“明天中午12点整的火车。”
孟云淑怔了下,随即点头:“好。”
日子比原本的计划提前了三天。
也好,早些走也好。
……
当天下午,孟云淑没有去医院,而是去了趟婚姻登记处。
她对窗口询问:“同志,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8月10日申请的强制离婚书,通过了吗?”
工作人员看了她的证件,在登记簿里翻找过后,很快告诉了她答案。
“已经通过了!离婚档案已经送往部队了,明天就会由军区政委亲手交到贺旅长手上。”
“好的,谢谢。”
这一刻,她心里长久以来的大石终于落了定。
随后她又去了通讯所,向父母告知了自己要提前去沪市的事。
挂了电话,孟云淑直接回了家,她进屋打开衣柜,收拾起行李。
收拾到最里处,一件红色旗袍映入了孟云淑眼帘。
她认出来,这是她和贺泽铭结婚时穿的。
这旗袍衬得她身段柔美,那也是贺泽铭唯一一次夸她漂亮。
可就穿了那么一次,孟云淑就再未穿过了。
此刻,孟云淑拿过旗袍,才发现后背竟然好几个洞,丝线疏断。
这件旗袍,就像他们的婚姻一样,表面无恙,实则背地里早已千疮百孔。
她拿着旗袍走出来扔进了院子里的垃圾桶。
这时,门外传来声响,是贺泽铭抱着贺霖回家了。
进门看见早已在家的孟云淑,他身形一顿,脸色当即一沉。
将熟睡的贺霖抱进屋内后,贺泽铭来到院里,张口是一贯的指责。1
“你早就下班了,为什么不来医院接儿子?”
孟云淑看了眼他:“不是有你在吗?”
说完,她转身要进屋去继续收拾东西。
可贺泽铭一把拉住她的手臂,他眉头紧拧。
“你还在生气?孩子在医院胡说的话,你也当真吗?你跟他计较什么?”
院子里安静下来。
孟云淑静静注视着面前的男人,开口:“你心底不也是这样想的吗?”
贺泽铭不解皱眉:“你说什么?”
孟云淑沉默片刻,唇角勾起一抹讽笑:“贺泽铭,有时候你还比不上你儿子,至少你儿子敢说出口他就是喜欢洛清清,你却不敢。”
贺泽铭听到这话,脸色当即又黑又沉:“你瞎说些什么?”
“你少用你的肮脏心思胡乱揣测,我和洛老师清清白白。”
孟云淑听着,只觉可笑。
他们若是清白,前世怎么会纠缠了三十年?
他们若是清白,前世洛清清怎么就为了他一直未嫁?
他们若是清白,前世怎么她一病,贺泽铭就迫不及待要和洛清清结婚?
可这些质问,孟云淑今生无从问起,此刻的贺泽铭也给不了她答案。
所以孟云淑泄了气,只点头:“那就当是我胡说吧。”
时间总会证明一切的。
她已经不想再过多关注了。
……
离开当天,是很普通的一天。
孟云淑照例打理好家里的一切,然后和贺泽铭一起将贺霖送去幼儿园。
在孩子踏入幼儿园时,孟云淑朝那小小的身影喊:“小霖,跟妈妈再见!”
可一心扑向洛清清怀抱的贺霖,连头也没回。
孟云淑笑了笑,却再也没说什么,和贺泽铭在幼儿园门口分开时。
孟云淑同样喊住了准备迈步走向部队方向的男人:“贺泽铭。”
贺泽铭一身军装,回头看她:“怎么了?”
他英俊的脸庞在朝阳下,渡上一层金光。
孟云淑将这张爱了两辈子的脸,最后一次认认真真端详了一遍。
许久后,她勾起唇角,朝他挥手。
“贺泽铭,再见。”
闻言,贺泽铭狐疑看她一眼,却还是因为归队时间紧迫,点了个头直接转身就走。
孟云淑看着他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远方,自此他也将彻底消失在她的人生里。
他不会知道,这是她在跟他道别。
随后,她踏步回家拿上行李。
关上家门的那一刻,孟云淑看着这生活了六年的家,心里升起感慨。
这屋里的一桌一椅,都是她亲手置办。
刚嫁进这个家时,她眼里心里都是对幸福婚姻的期待。
可谁能料到,这个家却困住了她前世一生,还好今生她已经离婚了。
孟云淑想,此刻离婚档案大概已经交到贺泽铭手里了吧。
他们之间,总算结束的毫无牵绊。
此时,门外传来声音:“孟同志,该走了!”
“来了!”孟云淑应了声,而后,她哐当将院门合上,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贺家。
坐上研究所派来接她的专车后,她跟随者同事们的步伐,一同踏上了去往沪市的火车。
她孟云淑此生,将投身医疗研究,为国为民全力贡献。
至于贺家这对父子,这狼狈的情感,她一个也不要了!
余生,只为国。
第9章
与此同时,凛北军区旅长办。
“贺旅长,有你的信件。”
政委敲了敲门,将一个黄封皮的信封交到贺泽铭手上。
他打开来,震惊得瞳孔紧缩。
这是——孟云淑给他的强制离婚书。
贺泽铭手指捏紧这封强制离婚书,手背青筋暴起。
他知道这段时间,孟云淑不再像从前一样,事事都围着他和儿子转,态度也冷淡了很多。
可却从来没有想过,孟云淑是要和他离婚?
两人结婚已经六年了,孩子也五岁了,她竟然舍得抛下这一切和自己离婚?
贺泽铭感觉自己的胸腔像被堵住一样,他看着这封强制离婚书,双眸猩红,最终指骨作响,将离婚书狠狠揉碎。
……
开往沪市的火车上。
绿皮火车晃晃悠悠,车厢里各路人马鱼龙混杂。
四周有些嘈杂,还弥漫着一股难闻却又不知道从何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汗臭味,搅得孟云淑脑仁有些疼。5
她太阳穴突了几下,有些睡不着了。
再看对面的王院士和两个师弟都已经睡着,孟云淑因此小心翼翼走出来。
她想去火车车厢中间位置,透透气。
结果刚打开门,就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在抽烟。
他低着头,狠狠抽了一口,然后吐出一阵白雾,空气比车厢中更难闻了,孟云淑下意思皱起眉头。
这时候,男人也注意到了这里闯进了人。
他摁熄了香烟,锐利的目光透过来。
孟云淑这才看到他的脸,年轻而温润,但那一双眼,深邃如寒潭,让人望而却之。
就这短暂的一眼过后,突然,孟云淑听到车厢广播里传来声音。
“各位乘客,现在有突发情况,9车厢中部,一位乘客突然突然发病,陷入昏厥,现在广播寻医,若车厢中有医护人员,恳请立刻前往救人。”
孟云淑听到,心中揪起。
她学了好几年的医,虽然目前没有从事医生而是医学研究,但是治病救人,像是被刻在了骨子里。
因此,孟云淑没有半分迟疑,立刻转身往9车厢跑去。
而正在抽烟的男人听到广播,也赶紧掐灭了香烟,步履匆忙,跟着往9车厢走去。
一路上站票的人太多,通通都挤在过道里,因此孟云淑只能很艰难地挤过去,这才终于到达。
这时,听到女乘务大声喊道:“有医生吗?有医生吗?”
孟云淑开口:“我不是医生,不过我从事医学研究,能做简单的急救措施。”
这时,身后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我是医生。”
话音落下,女乘务员那双急切的眸眼突然泛起激动的光。
她忙朝两人招手,孟云淑和身后的男人视线撞上,接着快步往前走去。
……
军区大院,幼儿园门口。
贺泽铭看着蹦蹦跳跳跑过来的孩子,脸上的阴霾丝毫没有消散。
贺霖高兴地喊着“爸爸”,冲过来扑进他的怀里。
贺泽铭也一把将贺霖抱了起来,想说什么,喉咙有些涩,又没说。
还是贺霖自言自语:“我想吃妈妈做的糖醋排骨了,爸爸,今天让妈妈给我烧排骨吃好不好?”
第10章
9号车厢里。
孟云淑和男人一齐蹲在了晕倒的大婶身前。
贺泽铭抬起眼,看了一眼面前的女子。
头发盘在脑后,露出一张鹅蛋小脸,皮肤白皙,目光明澈。
她连忙询问起四周乘客原因:“毫无预兆地昏厥吗?”
旁边有个急得快哭出声的男人,正是大婶的儿子,他连忙回答:“我妈先是说心口疼,然后就慢慢昏倒了。”
男人低下身去看了一眼情况,简单判断,应该是心梗亦或者突发性的心脏病,有些棘手。
只因为心脏疾病发病太快,抢救不过来,往往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要了人的性命。
孟云淑看着他神情不佳,于是问道:“什么情况?”
孟云淑听完,犹记得王院士的包里,携带了治疗突发心脏病的药,孟云淑于是当机立断将情况告知。
乘务员也是立刻就去找了王教授,接着,男人便开始给大婶做起心肺复苏来。
这需要速度和力气,一下一下,按压着大婶的胸腔,直到没有力气。
孟云淑接替过来,不过她的力气没有男人持久,很快便没了力气。
男人又补上。
两人就这样一直轮换交替,直到乘务员从王院士那里取来了救心丸,喂大婶服下。1
没多久,火车靠站,乘务人员将大婶送到下火车,送到最近的医院抢救。
到这里,孟云淑终于松了口气,额头上覆了满满一层汗珠。
两人的目光再次撞上。
为着刚刚,两人一同努力救人的情谊,孟云淑主动朝他伸出了手,自我介绍道:“我是孟云淑。”
男人也弯唇,握住了她的指尖,很快松开。
“我是顾修京。”
短暂的介绍后,孟云淑起身往自己的车厢走去。
而男人则看着孟云淑清丽的背影,有一瞬间的愣神。
孟云淑回到座位上,王院士赶紧来问情况。
孟云淑也是一一回答。
当听到孟云淑说“已经被送往就近医院了”,王院士才松了一口气。
随即,他称赞了孟云淑:“云淑,做得好极了。”
毕竟从事医疗行业,治病救人,应当是每个医者心中的热忱。
贺泽铭抱着贺霖回到了家里。
夜幕慢慢降临。
说起来也奇怪,明明孟云淑只是带走了自己的一点衣服,可这个家,却莫名空荡了很久。
贺泽铭走进厨房,却是冷锅冷灶,没有一丝烟火气。
贺泽铭走进客厅,平时,孟云淑喜欢坐在沙发上看书,现在幻影一闪而过,却什么都没有。
贺泽铭最后走进卧室,犹记得孟云淑喜欢站在窗边梳头,也喜欢坐在窗边给孩子织毛衣,每次他进门来,她总是笑眼弯弯唤一声“泽铭”。
现在再也不会出现了。
这时,贺泽铭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就错了。
从前,他总觉得,孟云淑是离不开自己,离不开这个家的。
当初相亲结婚,这么多年,孟云淑看着他的眼神里,总是盛满了爱意。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双眸眼,开始冷淡了。
贺泽铭却一直没有在意过,直到现在,她走了,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
没有预兆的心痛,如同突然之间被重物砸中胸腔。
这时,门外传来一个中年女声:“贺旅长,贺旅长,你媳妇让我找你!”
第11章
“媳妇?”
听到这两个字,贺泽铭一愣,下意识往外走去。
沉闷的心,瞬间也开阔起来。
他就知道,孟云淑不会这么狠心,就这样轻易抛弃他们父子俩的。
两人六年婚姻,多少酸甜苦乐,都这么走过来了。
她怎么可能舍得下啊?
贺泽铭以为是这些天,两人感情不好,孟云淑闹了脾气故意来的这么一出。
怀着激动的心情,贺泽铭匆匆忙忙赶过去。
到小巷口,跟着大娘到了小巷口,却发现不是孟云淑。
原来是洛清清骑自行车路过这附近不小心摔倒,于是央求路人去找了贺泽铭。
贺泽铭有些不悦地皱起眉头过去将她扶起来,洛清清抬起头,看着贺泽铭坚毅流畅的下颌线条。
两人身体相触,呼吸相闻,似乎有暧昧气息涌动,洛清清脸颊绯红,像是飞上了一朵红云。
她也忍不住,有些羞涩地低下头。9
可下一秒,贺泽铭冷沉的声音却打破了这种暧昧氛围。
只听到他开口说道:“洛老师,你怎么和那大娘说是我媳妇?”
洛清清听到这话,心里五味杂陈。
她们家和贺泽铭家是旧识,贺泽铭比她大了四岁,十六岁的时候便参军入伍去了边疆,两人也就再没见面。
等四年后,他回来,洛清清也正好到了适婚年龄,在贺泽铭回家的接风宴上,洛清清也是一眼就相中了他。
洛清清是家里的独生女,对这个女儿,洛家也是要什么给什么的。
回来后,听说洛清清对贺泽铭有意思之后,也是立马就和贺泽铭家里商量。
如果不是因为洛清清家里成分不好,政审没过,恐怕现在她就是贺泽铭的老婆了。
可惜天意弄人。
她低下头,故作歉疚地说道:“不好意思,贺大哥,许是那大娘理解错了意思,我没说是你媳妇,她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去你家,亲自和云淑姐解释,实在不想她误会了。”
贺泽铭听到这话,心情却更差了。
孟云淑走了,她还要和谁解释?
看贺泽铭这里宛若黑云压城,洛清清察觉到了一丝异样,不过嘴唇动动,倒是忍住了什么都没问。
只是轻轻“嘶”了一声,故意说道:“好痛啊。”
贺泽铭的注意力,这才挪移到洛清清身上。
只见她衣服因为骑车摔倒而刮擦了破损,手肘膝盖都磨出了血痕,于是开口道:“先回一趟我家,我帮你处理伤口吧。”
听到要去贺泽铭家,洛清清自是犹豫都没犹豫一下,立刻便同意了。
“好啊。”
走了几步,一瘸一拐的,贺泽铭见状,自然是上前搀扶。
洛清清挽着贺泽铭的手,举止亲昵,唇角,也不可遏制地浮现笑容。
本来她摔倒的地方离贺泽铭家就不远,很快,两人便进了院子,屋里亮着灯。
明明都到了贺泽铭家门口,洛清清却还偏偏要矫情一下:“贺大哥,云淑姐见到我,不会生气吧?”
贺泽铭语气更加沉闷:“不会,她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