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知道为什么战地要带接生婆吗?
当年郑和下西洋,船上除了两万正规军,还有一种职业人——接生婆。
在当时,很多地方的医疗技术比明朝差。他们去了以后,能帮当地妇女接生,同时也能和当地人打好关系,必要的时候是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战争。
在援老抗美时期也有个男孩,加入部队参加战斗,却被要求成为一个战场上的接生婆。
他一生的任务,就是保护那一千个孩子和母亲。

20年的12月,我们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兵,在云南文山聚会。按照约定,所有聚会人员都带上了自己最有意义的纪念物。
战友们带来的有立功证书,有用打下的敌机残骸做成的小手枪、碗筷,还有中央发放的参战纪念章,荣获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等等。
一堆勋章和证书里,只有我的纪念物格外显眼。
那是一只破旧的草绿色军用药箱,仅仅鞋盒大小,外表是塑料布,能防水。
有的战友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带这么一只箱子。我看着它,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
当年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我正是背着这只药箱,接生了许多孩子。

我作为医务兵,跟随部队去老挝的时候,还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
1968年5月8日深夜,我们先遣连脱下军装,换上老挝军队的服装,乘坐伪装好的汽车,秘密朝老挝边界进发。
连队刚到老挝,被下达的任务是要和当地百姓打好关系,为后续部队的进入做好工作。
但来了几天后,虽然路经了十多个寨子,可就是见不到老百姓。这让我们不仅不能进行宣传工作,而且了解不到敌情,十分危险。

在老挝的罗东钦
入夜,原始森林被夜幕笼罩。部队在森林里宿营,指导员把老挝向导叫来,向他打听老挝老百姓为何不愿见我们,现在做什么最有效?
向导想了想,手不停地摸头发,良久才说,老百姓回避你们是由于敌人做了反动宣传,而最有效的反击,是在遇到临盆的妇女时帮她们生下孩子,因为老挝缺医少药,又讲迷信,小孩出生率只在50%左右。
指导员向他道谢,并告诉他,如见到有生小孩的妇女,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有医生。
说完,他把连队做卫生员的我和军医一起叫去布置任务,让我们今后遇到有分娩的妇女,特别是难产的,一定要及时去做抢救工作。
指导员特意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不要害羞。
可是要在老挝接生并不容易,那里相对落后,人们普遍相信巫婆,接生也不例外。我第一次救回一个孩子时,就被巫婆带着一寨子的人围攻。
那是在一个茅草屋,一个年轻妇女躺在床上,大汗淋漓,不停地流泪,身旁躺着一个婴儿。她的丈夫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
旁边一个老年妇女对他们说,男孩已无缘活在世上了,我招魂两个小时,没有用,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走到婴儿旁,用手摸了摸它的鼻梁,又用手掰开嘴唇,然后摸了摸胸部,判断新生儿只是被口腔中的分泌物阻塞了呼吸。
我立刻嘴对嘴吸出分泌物,婴儿立刻哇哇大哭,活了过来。我很高兴,心想回到连队后一定会受到连长表扬。
谁知我回到驻地的时候,老百姓男女老少一百多口齐刷刷跪在连部,高喊着什么。
看我走过去,其中一个头戴黑色绒布帽,帽顶上野鸡毛,身穿黑色长衣,手持杏黄扇子的老年妇女冲了出来,拽住我的手,不停地说我们听不懂的本地话。
连队的翻译来了之后说,老年妇女是寨子里的在巫婆,寨子里的人都靠她的巫术求平安,下午她认定婴儿已经死亡,而我又救活了婴儿,因此断定我有妖术。
这时寨子里的族长因病死亡,让她觉得我们能救活婴儿,代价是让族长失去生命。现在大家来求情,希望让婴儿死去,族长活过来,一命换一命。

我用医学知识救人,没有什么妖术,根本不会起死回生。但我怕自己不去,巫婆会出阴招儿,害死好不容易救回来的婴儿,所以立刻答应去寨子里看看。
军医和我一起来到他们的寨子,族长的尸体就停放在寨子坪里的聚事厅,尸体上盖了床毛毯,已停放一天,准备按习俗进行水葬。
军医蹲下去,摸了摸死者手腕,又翻看了眼睛,再用听诊器听心脏,发现还有微弱的心跳,他立即叫巫婆将尸体抬进屋。
军医发现族长患的是急性疟疾,因高烧昏迷,所以给他进行了治疗。
我们整整守护族长一晚上,第二天天亮,族长奇迹般坐了起来。他的妻子儿女跪在我面前叩头致谢。
这次事件之后,我才明白在当地开展工作有多困难。连长要我去帮助妇女分娩,可是当地从来都是女性接生,没有男性接生的先例。
老挝属亚热带,最常见的病一般有肠炎、痢疾、疟疾。我和战友们只能频繁给当地人看病,获得他们的信任后,才能有机会给妇女接生。
6月的一天,我们正在一处寨子里做好事,突然天上出现了飞机轰隆隆的声音。八架美国鬼怪式飞机朝我们投下一颗颗巨型炸弹,又低空机枪扫射。
连串炸弹在身边炸开,落下的流火瞬间点起滚滚浓烟。
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几乎将人震得双耳失聪,但在地上的战壕里,仍能时不时听到战友被弹片炸伤后支离破碎的呻吟。
我循着这些声音不停地在战壕中穿梭,撕开一个个急救包,为战友包扎。
又是一声巨大的爆炸,我听到一声熟悉的惨叫,整个人激灵一下,立刻冲了过去。
这次倒下的是黄西林,我们部队的老卫生员,在他被飞溅的弹片击倒之前,他还在为一个受伤的战友包扎。
我试图用绷带将他受伤的头部缠紧,却没有什么作用,鲜血几乎遮满了他的脸。
他抓住我的手,说出来人生中最后一句话:"小罗,寨子神龛阁下的防空洞内,有个孕妇……"
话还没说完,他头一歪,闭上了双眼。
我悲痛欲绝,夺来战友的步枪,朝着在天空中高高盘旋的飞机连开三枪,最后颓然坐在地上,仰望着飞机越飞越远。
太阳西坠的时候,我向连长说了黄西林牺牲的经过和他的临终嘱托,但刚一提出想去神龛阁帮孕妇接生的想法,立刻遭到了战友们的反对。
天已经快黑了,又要穿过战场,除了什么都看不清,他们更担心在路上遇到埋伏的特务,如果敌机回来继续轰炸,连躲都没地方躲。
况且随着我们一路行军,美军一直在头顶轰炸,老百姓也见到我们就跑,也许等我们赶到,孕妇已经和家人跑了。
我知道,每次我去接生都要有人给我做保镖,但战友们似乎都不愿意做这份差事。
我的战友都年纪轻轻,没进过产房,也不清楚接生是怎么一回事。
除了不好意思,大多数人都觉得接生是女同志的事,让他们给我当保镖,不如给他们派一些其他任务,多干点活。
还有说法,在战场上打仗的人,给妇女接生之后会变倒霉,不吉利。在国内,接完生之后要讨红包,插红旗,去去霉气。
每次都有人说,下次不要派他来了。
以前也就算了,但这一次我却比以往都渴望去,因为这是黄西林的遗愿。连长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最后还是派了一个班的战士做护卫,与我同去。

我入伍不久就认识了黄西林,那时我经常遭到战友的讥笑,就因为我是一个特殊的医务兵,要给妇女接生。
我出生在湖南农村,因为发小高烧成了痴呆,我从小发誓要做医生,救死扶伤,帮人看病。
但当时正值文革,只有上工农兵大学才能当医生,而上大学则需要靠乡镇推荐,一个镇只有零星几个名额。
好在从部队回来的哥哥告诉我,部队和外面不一样,大家对当医生根本不感兴趣,只要跟上级申请,很轻易就能当医务兵。
1968年3月2日,我如愿入伍,从湖南出发,到达云南边防部队,成为部队的卫生员。
就像哥哥说的,部队里没人愿意当医生,几乎所有人都理所当然觉得,只有上战场杀敌才叫战士,谁杀人多谁功劳大。
至于医务兵,只能给人包扎疗伤,自然与立功无关。
在新兵发枪仪式后,别的新兵收到的是长长的步枪和手榴弹,但我收到的是只绿色药箱,武器也只有一把防身用的手枪。
尤其药箱里有本《妇产科学》,被同乡翻出来后,故意笑嘻嘻地问我,一个大男人还为妇女接生小孩?
我心里也尴尬,不知道怎么向他们解释。
之后,我需要看更多的妇产科书籍,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风言风语。
不但有人跑到我们宿舍乱翻,还总有人把那些书偷偷拿走去看。甚至有人故意坏笑问我,是不是在想什么不该想的东西。
我只好一遍又一遍跟这些人解释,这是我的业务书,我是为了学习知识,提高业务能力。
为了不让其他人再拿走书,我只能把书藏在枕头下面。
就在这时我认识了黄西林。
一次战友又说我的时候,他上来解围,告诉那些嘲笑我的战友,我们学习这个就跟你们扛枪一样,你们的武器是子弹,我们的武器是针头。
“帮人看病,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就是我们医生的战争。”
他大我四岁,早我几年当兵,经验丰富,我直接管他叫哥。
他总开导我,让我不要把妇产科的书当成黄色小说,学这些妇产知识不仅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更能帮助到老百姓,在关键时刻甚至能救人性命。
我也向他请教,比如战友发高烧了应该用什么药,蚊虫叮咬血液不行了应该用什么药,还有接生时遇到的种种状况,他都会一一讲给我听。
后来,我特意和黄西林搬到一个通铺,整天吃穿住行都在一起,相互之间亦师亦友。有时他衣服脏了我还想抢着帮他洗一洗,但他连这点“学费”都不肯收。

罗东钦(右2)在向战友请教医学知识
在老挝,我们常有长时间的行军,有战士体力不支,就会掉队。而环伺在周围的特务,看到落单掉队的战士就会趁机将其暗杀。
有一次,黄西林发现我掉队了,他本已到达目的地,又回来接我,多走了一公里路不说,还把我的背包抢去扛在身上。那一次,是他硬拉着我走回了连队。
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
现在他被敌人炸死了,我在一旁无能为力,就像当年我看着那个发小烧成痴呆,无能为力。我比以往更加急切地希望自己有一种能力,能帮助别人远离痛苦。

从战场到神龛阁有一里多的路,需要跨越刚遭受完轰炸的战场。没来得及清理的战场同样危险,除了随时可能倾倒垮塌的建筑,还很有可能会踩中尚未爆炸的炸弹。
整个寨子除靠山坡的房子幸免,有一半房屋被炸毁,还在冒烟。有的只剩下一堵墙,有的被夷为平地。被炸死的猪、牛、羊随处可见。
我们紧绷着神经穿过弹坑残垣遍布的村寨,好不容易松口气,突然在小路尽头上坡的位置,看到几条朦朦胧胧的人影。
两个穿着老挝民族服饰的男人正远远望着我们,其中一个年轻人腰间还别着一把当地砍柴用的短刀。
我的心又提了起来。
我最先猜测他们是听到我们部队到这里来,所以下山来打探消息的产妇家人。
不过他们不停用躲闪的眼神打量我们,还时不时窃窃私语。他们说的是老挝语,我们走得匆忙,没带翻译,听不懂,也不好上前询问。
这几人的行迹不像普通百姓,鬼鬼祟祟,有些奇怪,但他们仅偷看我们,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动作。
小路很窄,两侧都是树林,如果对面不躲,双方势必相遇。还好我们人数比他们多,战友手里还有枪。
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在我们与对方擦肩而过时,他们中的一个与我对视一眼,立刻低下头。
我们在前面走,树林里又出来三个人,在后面远远跟着,但迟迟没有行动。
在老挝当地,除了与我们敌对的右派,还有左派和中立派别,势力太复杂,不知道他们是哪一派的。
我们现在只有几个人,怕贸然动作会吃亏,况且孕妇生产更紧急,当即决定一鼓作气先把接生的事先做完,再来应对这几个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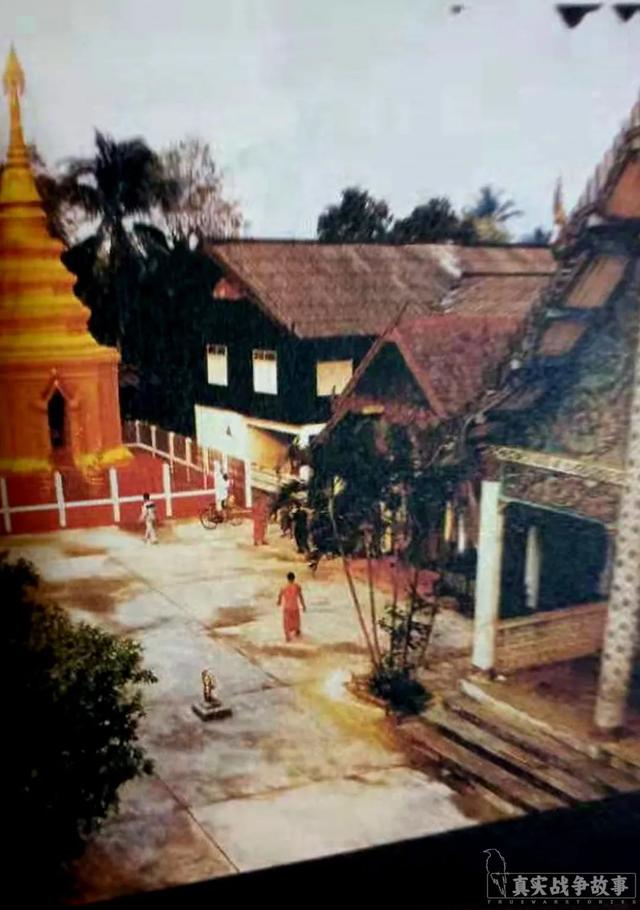
老挝当地的神庙
我们先到达了寨子的聚事厅,映入眼帘的是六具尸体——两个男孩和四个老人——都是轰炸致死的。
其他一些村民围在旁边,打量我们的目光好奇中夹杂着警惕。
我注意到其中坐着两个男人,一个人五十多岁,一个三十岁左右。
五十岁的男人左腿被炸弹炸断,用一块毛巾抱扎着,毛巾浸出了鲜血,伤口已经生疽。他柱着拐杖,望着被炸毁的房屋,木然地坐着,不知所措。
三十岁的男子被炸伤,左手仍在滴血。
我立刻打开药箱,拿出酒精帮他们清理伤口,再在伤口处洒上生肉止血的药粉包扎。男子很配合,我们很快就帮他把伤口包扎好了,周围群众看我们的警惕也稍稍淡了些。
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断腿的男人眼睛在四处张望,不敢正视我们。见我们要去防空洞,他拖住我们,很感谢,但似乎又很着急,让我们不要往下走。
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我们又看到了刚刚跟了我们一路的那三个可疑探子。
语言不通,我们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接生又不能耽误,就走出了聚事大厅,往山上爬。
防空洞在山腰上。一个男人在洞口用小绳子拉着一只大公鸡,大公鸡仰着脖子朝天,这个男人对着公鸡的头,单腿跪地,双手合十,嘴里念叨什么,不停叩首。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祭拜的男人是孕妇的丈夫。我拍了拍红十字药箱,笑了笑。孕妇丈夫明白了,眼睛一亮,不住地朝我们磕头。另一位战友领头,我们立刻钻入防空洞中。
与其叫防空洞,不如说是山体天然形成的石洞更贴切。洞内的面积不大,还有其它一些小洞相连。
此时外面已经天黑了,洞内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家具也简单,只有一张床和一堆柴火,床上躺着痛苦呻吟地女人,柴火上做着热水。
怕洞内有敌人,我让另一位战友在小洞中侦查情况,也许仍对我们有些不放心,一个中年女人也跟了进来,看样子她是产妇的亲戚。
因语言不通,我干脆什么都没说,直接打开药箱,开始接生。
我让孕妇慢慢用力,孩子先出来的是脚。
头先出来是顺产,脚先出来就是难产。这肯定不行,我两只手都伸进去,试图扣着它的肩膀和脖子把它一点点扭翻过来。
在这过程中,孕妇疼得哀嚎不止,在凉爽的防空洞里,我出了一身汗。
如果长时间难产,大人会出血而死,婴儿在孕妇腹中长时间不出来会窒息。
就在两相胶着间,洞外突然传来几声枪响。
我开始以为是守在洞口的战友枪走火,没想到枪声未落,洞外就传来战友的催促声,有敌人摸过来了!
我不停地说快了,但实际上婴儿依旧卡在孕妇腹中,进退不得。
我心里着急却不能说,只能仔细回忆,我所学到的关于分娩的一切知识。

我在国内曾跟随老军医学习,怎么给孕妇接生。
第一次是中午,军队里收到消息,当地少数民族寨子里有一家妇女即将分娩,要军队派军医过去救治。
烈日炎炎下,我还没来及细想,已经跟着老军医到达孕妇家的茅草屋。
孕妇的丈夫婆婆满脸笑容,将我和老军医一起迎进了家里,还早早准备好了脸盆、热水、毛巾。
因天气极热,孕妇躺在宽大的竹床上,大汗淋漓,婆婆不停为她揩汗。由于婴儿的躁动,母子咬紧牙关,忍受疼痛,没有呻吟。她下身没有穿裤子,双腿平直。
我匆匆扫过一眼,整张脸都涨红了。
老军医当即走近孕妇检查,他用手摸了摸凸起的下腹说,还好是顺产。
老军医叫我名字。
我当时站在十多米远的家门口,还没有反应过来。那是我第一次见次见到妇女生小孩,心中胆怯又尴尬,屋子里弥漫着一股与平时不同的气味儿,我下意识地用袖子挡了挡鼻子。
老军医呵斥着催我快过去。
产妇阴部露出了婴儿头发,老军医用左手指伸进了婴儿胎头上部,问我看见了没有,这叫助产。我强忍着将目光移开的冲动,点了点头说,看见了。
“抬起双腿,稍用力。”老军医指导孕妇,边指导还在不停地给我讲,孕妇所抬双腿要适度,说着,他还不停地比划着位置。
我假装自己像平时一样在学习枪伤刀伤的包扎,认真地将步骤记下。
半个小时后,老军医要我用右食指伸入胎头旁,要我用左手轻轻的托住胎头。我照办了。
下午两点,传出婴儿啼哭声,一个男孩诞生了。
我还没看个明白,老医生又现场指导,孕妇生产,分几种情况。因胎儿在腹中头大四肢小,所以头先出来是顺产,脚先出来是难产。
如果头先出来是脑袋朝下,需要拽着他的胳膊帮它转一下让正面朝上,拽着肩膀和脖子把它拉出来。
如果是脚先出来,则需要医生将手伸进会阴,除了防止产妇宫口撕裂,还要帮忙调整婴儿的位置,让它出来一只肩膀,全身斜着出来。
介绍了几种婴儿刚出生后不哭的原因,他告诉我,可以用嘴吸汾泌物,倒提婴儿双脚,轻轻拍……等等。
当时我只是看,背记一些理论,没来得及亲自上手,也想象不出现在的自己居然有勇气闯女人的产房。

夜幕降临,空中飘着一片雾气,月亮被遮住了,连星星也变得很暗。
洞外除了越来越近的枪声,还能听到灌木叶子被掀开的哗啦声,人的说话声,这些都是朝着防空洞来的。
我在洞内能听到洞外的战友卧倒在地时,枪托磕在石头上的声响。
这说明洞外的情况已经非常紧急,来人的距离很近了。
孕妇丈夫很着急,不停地摧我们快走。他告诉我们说:“敌人要抓你们,你们的战友已经全部被飞机炸死,没有人来救你们。”
我已经顾不上这些了。这个婴儿安全出生是黄西林牺牲前最后的心愿,哪怕豁出命,我也要把这件事做完。
洞口处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有人跑上来。
敌人就上来了?
“罗卫生员,罗卫生员……”有人大声喊道。
我骤然松了一口气,是二排长的声音,他带二排来增援我们了。
原来,连队接到情报,敌人以为我们全连已被敌机炸乱,要趁机抓几个活的回去领赏,刚好我们去寨子接生,被敌人跟踪。
我终于从产妇身下抱出了一个女孩。我用纱布把口腔清理干净,提起她的腿,拍了几下,女孩哭起来了。
婴儿的母亲被生产时疼痛折磨得狼狈而憔悴,向我道谢时,脸上带着泪,却止不住笑。
我端详着这个寄托了黄西林遗愿的婴儿,她皮肤是紫红色,脸上长着皱巴巴的纹路,像个小老头,抱起来很小很瘦,只有五斤左右。
这个新生命又让我想起了黄西林。婴儿很轻,他却很重。他在生前救治了很多战友,尤其是对我很好。
我还没来得及为他做什么,他就牺牲了。好在我不负嘱托,完成了他的遗愿。想到这里,我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最后,我又在山洞待了二十分钟,把孕妇的胎盘清理干净,等没有出血后,才告诉产妇,你没事了,母女平安。我说的是中文,也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
母亲抱着孩子,和他丈夫一起,不停地朝我作揖道谢。
其他一些陌生的寨民也在我身边围成一圈,虽然不是他们的孩子,但并不妨碍他们和孩子的父母一样喜气洋洋,朝我们连连感谢。
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从他们的眼神和笑容里,他们想表达的感激,我每一个字都能听懂。
我走到洞外,一抬眼就看到三具尸体,正是刚才跟踪我们的探子。

1979年2月,我又被选入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因为之前的工作表现突出,我升为了军医。
我的医护所设在离阵地八十米处,和其他四个卫生员一起,几乎算是顶着炮火给战友治伤。

在战场上挎着小手枪的罗医生
清晨时分,战斗进行异常激烈。我抢救了十二个伤员后,阵地传来消息,副连长身负重伤,由于敌人火力封锁,无法抢救下来。
我当机立断,顾不上敌人机枪扫射封锁,匍匐前进,爬行四十多米,将副连长抢救下来,背到了救护所。
副连长被敌人的机枪打中脖子主动脉,我心里清楚,即使我是医生,仍然救不了他。
他握住我的手,脱下手表,发出微弱的声音:“谢谢你,罗医生,请将这只表交给我妻子……”话刚落音倒在了我怀里牺牲了。
就在这时,两个战士抬着一个伤员来了。那人躺在担架上,手臂在流血。
也许是看到我衣服上的红十字袖标,伤员用中文大声喊道:“救救我,我不想死……”
我问是怎么回事,战士告诉我,这个人是俘虏,一个越军连长。
见是俘虏,想起刚抬下去牺牲的副连长,我气不打一处来,猛地往担架上踢了两脚。
越南有抓到我们解放军的俘虏,待遇很差,本来伤势不是很重,及时救治就可以康复,但是越南人故意不给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我故意晾那个俘虏几天,也没有人会说什么。
但我转念又想,如果我这么做,我们又与越南人有什么不一样?
况且,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自己的职责。眼下我们在战场下,不是敌人,是伤员和医生的关系,我理应救治。
我让战友把这个人放下来,解开了两个急救包,弯下腰为越军连长包扎了正在流血的伤口。包扎完,我顺势摸了一下,给这个越南人俘虏说,让他放心,他不会死了。
俘虏愣愣地看着我,不说话,眼眶红红的,全是泪水。
我拍拍他肩膀,示意战友将他抬下去。
这时候,突然有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战友大声嘲讽道:“大家都看见了,罗医生抢救我们的伤员算立功,但他现在抢救俘虏,那可什么都不算。”
我想反驳,自己救人根本不是为了立功,但最终没说出口。
此刻,担架员把俘虏放在地上,不肯抬他。俘虏受伤很重,只好央求担架兵,要他们帮忙抬一手,他现在无法走路。
指导员直接走过来啐了一口,拍了拍自己的枪,吓唬他,不走路就把他枪毙。
我赶紧制止指导员,毕竟他是伤员,还是该抬就抬。
担架兵听到我的话,这才不情不愿地把人抬走。

战场上战友们都在奋勇杀敌,我不但没有杀过一人,还接生了八个新生命,甚至包括一个敌人的孩子。
那是一个老挝右派的女间谍,我和战友们俘虏她之后,发现她倒在了地下,地上流出了血水。
我一眼看出来她要生了,立马让战友找干柴烧火,为她保暖。
生完孩子后她很虚弱,我们没再抓她,反而找到了她母亲,让她母亲来照顾她。
这件事我只和连长说了,不敢太声张。在当时的氛围里,敌人就应该被消灭,救助敌人是无法被理解的。
可是接生了这么多孩子后,我越来越明白,不管敌我如何斗争,孩子都是无辜的。
这个道理很少有战友能明白。在他们的意识里,打仗就是杀敌。
但我知道厮杀并不是我们来老挝的目的,我们来老挝付出这么大牺牲,是为了帮助老挝人民抵抗侵略,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
无论是战胜敌人,还是迎接新生命,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连队刚到老挝时老百姓不信任我们,把我们当做反动派军人。
后来他们看我们军纪严明,从不侵犯妇女,甚至传出“中国军人都被骗了才能出国”的谣传。
连队一共有一个军医、一个医生、四个卫生员,我们做了许多好事,帮助当地人治病、接生,这才换来了他们对我们部队的信任,心甘情愿为我们打掩护,提供情报。
在一次治病之后,有村民告诉了我寨子周边反动派驻军窝点的线索。战友们根据线索,端掉了那个窝点,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这让我更加确信,虽然我没有杀敌,但一样是帮助我们赢得最终胜利的因素。
每当战友牺牲在我面前,我都想为他们报仇。但我报仇的方式不是拿起枪,而是更努力地为人治病,治更多的人,哪怕是敌人。
战场上除了杀戮还有一种武器,名叫善意。

1979年,我终于离开战场,回国正赶上部队裁军,被迫选择转业。离开部队那天,我请求领导,将那只跟随我十多年的药箱带回家。
从学医开始,它就跟着我,在我身边十多年,边角处已经有些粗糙破旧了。第一次拿到它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空药箱,现在里面已经被各种急救药品装满。
在战场救治伤员、在部队巡警看病,或者帮在寨子里帮妇女接生,都是带着这只药箱。它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没有它我就好像少了一样东西,整个人空落落的。
领导痛快地答应了我,这个药箱太旧了,部队已经准备换新的。
我有些庆幸自己是医生而不是战士,枪不能带回家,但药箱能。

罗医生至今仍保留的药箱
我乘上了从昆明开往湖南的80次列车。在回家的列车上,正好赶上有妇女生产,我靠着这只药箱,又帮助一个孩子平安降生到世间。
回到家乡几年后,我被调往县卫生局健康局工作,后任副主任纪检组长,直到2010年退休。
不论被调到哪里,我都会让这只从部队带回来的药箱陪伴着自己。不论是上班,还是业余时间,只要老百姓有人叫我看病或接生小孩,我都会义务出诊。
2020年我收到战友聚会的消息,便决定带着这只箱子到文山。
就像当年战友们在那里打靶练枪,而我在树下看书一样,我手上的东西还是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认为我的荣誉不是立功,而是从医五十多年,从参加援老抗美接生婴儿,到为部队家属接生小孩,再到地方,特别是当乡卫生院长,我所接生的婴儿不下一千例。
当新生儿交付在他们父母手中,那一张张灿烂笑脸对我来说,才是我这辈子最喜欢看到的画面。
这些生命,就是我的勋章。

所有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援老抗美同样如此。
而战争最残酷之处在于,无论抱着怎样单纯美好目的而来,只要深陷其中,看着朝夕相处的兄弟一个个倒下,仇恨就会不由自主地蒙蔽双眼,开始想冤冤相报,以杀止杀。
罗医生为只有杀戮的战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罗医生告诉我,他接生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为军人,还有的像他一样当了医生。
死亡是结束,而新生则是生命的开始。战场上的另一种可能性也延续到这些在战地中出生的孩子身上。
他们因此拥有了各种各样的人生。
谢谢你,罗医生。
编辑:赵土司 马修
关注我,看更多真实战争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