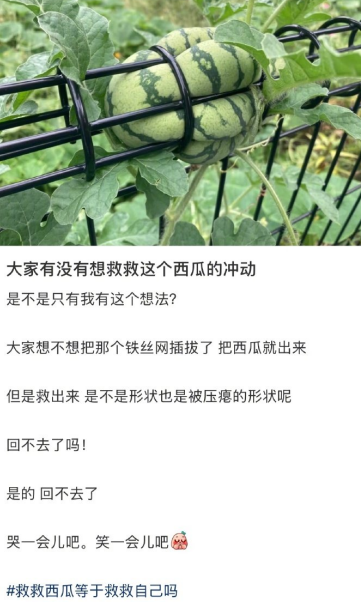单位办公室四个人,每天中午有俩人回家休息,剩下的一男一女就锁上门在屋里午睡。我就是那“剩下的人”之一,另一个是同事老陈。老陈比我大五岁,话不多,平时就坐在工位上埋头写材料,午休时会把折叠床展开,靠在窗边睡;我则趴在桌子上,枕着胳膊眯一会儿。 单位办公室的午休时间总带着点微妙的安静。四个人里,每天中午总有俩回家,剩下我和老陈,锁上门,在这间朝南的屋子里各找各的角落眯瞪。 老陈比我大五岁,是那种典型的“材料人”,平时除了必要的工作交接,话少得像工位上那盆不怎么浇水的绿萝。他有张深蓝色的折叠床,午休时会“咔嗒咔嗒”展开,支在窗边,头朝着墙;我呢,就趴在办公桌上午睡,胳膊当枕头,脸埋在臂弯里,闻着袖口洗不掉的洗衣液味儿。 最初挺不自在的。俩不太熟的异性锁在一间屋里睡觉,总觉得空气都比平时粘稠。我能听见他翻身时床板轻微的“吱呀”声,他大概也能听见我因为趴得不舒服而发出的闷哼——有次我猛地抬起头,正好对上他掀开窗帘一角往外看的目光,俩人都跟触电似的迅速移开视线,尴尬得能听见窗外的蝉鸣。 后来就慢慢习惯了这种“沉默共处”。他每天展开床前,会先把我桌上那盆多肉往窗边挪两寸,怕挡着我的光;我呢,会在他睡熟后,悄悄把他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往他身上盖一点——他睡觉总爱踢被子,尽管那只是件薄外套。 有天我重感冒,趴在桌上咳得浑身发抖,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背,递过来一瓶温水和一包纸巾。睁开眼,老陈站在桌边,手里还拿着他自己的保温杯,眼神里带着点不自在的关切:“喝点水,压一压。”我接过杯子,指尖碰到他的,温温的,像他平时那个人。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好像多了点什么。不是客套的寒暄,也不是刻意的亲近,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他展开床时,我会下意识地把脚往里收一收;我趴着睡觉时,他会把手机调至静音,连翻材料都轻手轻脚。 有时候我会想,成年人的关系是不是都这样?不需要太多言语,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明白对方的需求。就像老陈从不问我为什么不买张折叠床,我也从没问过他为什么总在午休时看窗外——或许,我们都在这短暂的独处时光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天地。 现在,每天中午锁门的那一刻,我不再觉得尴尬,反而有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亲切感。老陈的呼噜声很轻,像小猫的呼吸;我趴着睡觉时,偶尔会流口水,他看见了也从不戳破,只是在我醒后,默默递过一张纸巾。 这种安静的陪伴,像一杯温水,没什么味道,却在不知不觉中滋润了枯燥的工作日常。我们依然很少说话,但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因为这短暂的午休时光,变得有了人情味。 明天中午,我打算带个新的U型枕,或许趴着睡能舒服点——不知道老陈会不会发现,我今天悄悄把他那盆快蔫了的绿萝浇了水。
猜你喜欢
高二暑假的时候,女朋友偷偷带我去她家,说她爸妈去工地上班要两个多星期才回来,我就
2025-12-15
城城谈生
隔壁小伙惊呆了,估计是第一次见这样的事情
2025-12-16
雨韵趣聊小姐姐
这人是又聪明又坏!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子,担心被过往的车刮到,竟用了这个方法,在墙根
2025-12-16
北方小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