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通知我说让他妹妹家的孩子借住我们家,我明确态度,不同意。老公又说他已经答应她小妹一家了,我说,那你小妹家孩子来了,我就走,反正我不会管,你同意的那就是你管。老公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手里的玻璃杯往茶几上一墩,水溅出来打湿了刚买的桌布,"你就不能通融点?小妹一个人带俩娃容易吗?"我盯着桌布上晕开的水痕,像看到去年夏天,小姑子家的双胞胎把冰淇淋抹在沙发上的样子,奶渍渗进布纹里,怎么擦都留着道浅黄的印。 结婚五年,我和老公很少红脸,直到周三晚上。 他换鞋时头也不抬,说小妹家的双胞胎要来借住,至少半年。 我正擦桌子的手顿了顿,目光落在沙发扶手——那块浅黄的印子还在,去年夏天双胞胎把冰淇淋抹上去的,像块怎么也揭不掉的疤。 “不行。”我没回头。 他趿拉着拖鞋走近,“我已经答应小妹了,她一个人带俩娃,最近公司裁员,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那我走。”我把抹布扔进盆里,水声溅起来。 他愣住,“你说什么?” “我说,你同意的,你管。我不会再像去年那样,请假三天收拾满地的蜡笔和打翻的牛奶——你当时在外地出差,电话里只说‘辛苦老婆’,回来连句道歉都没有。” 他脸涨成猪肝色,“你就不能通融点?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我想起去年小妹来道谢,拎着袋快过期的水果,笑着说“孩子小不懂事”,转身却在家族群里发“嫂子就是能干,这点小事不算啥”——好像我收拾残局是天经地义。 他总说小妹难,可难的人就该把难处转嫁吗?去年我腰肌劳损犯了,是自己去医院做理疗的;双胞胎把我收藏的书撕了页,小妹只说“孩子闹着玩”,他还帮腔“小孩不懂事,再买一本就是”。 他手里的玻璃杯“咚”地砸在茶几上,水溅出来,打湿了刚买的桌布——米白色的,我上周才挑的,想着换个新桌布,家里能亮堂点。 现在好了,水痕像条丑陋的蛇,爬在布面上。 或许我该早说的,去年冰淇淋事件后就该说:我的家,不是谁的避难所,我的边界,也不是可以随便踩的路。 他还在吼,说我冷血,说我不顾亲情。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桌布上的水痕慢慢晕开,和沙发上的奶渍在视野里重叠——原来有些伤,不是看不见,是假装看不见;有些边界,碰一次就够了,再碰,就该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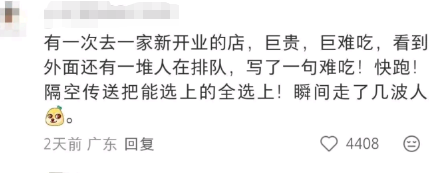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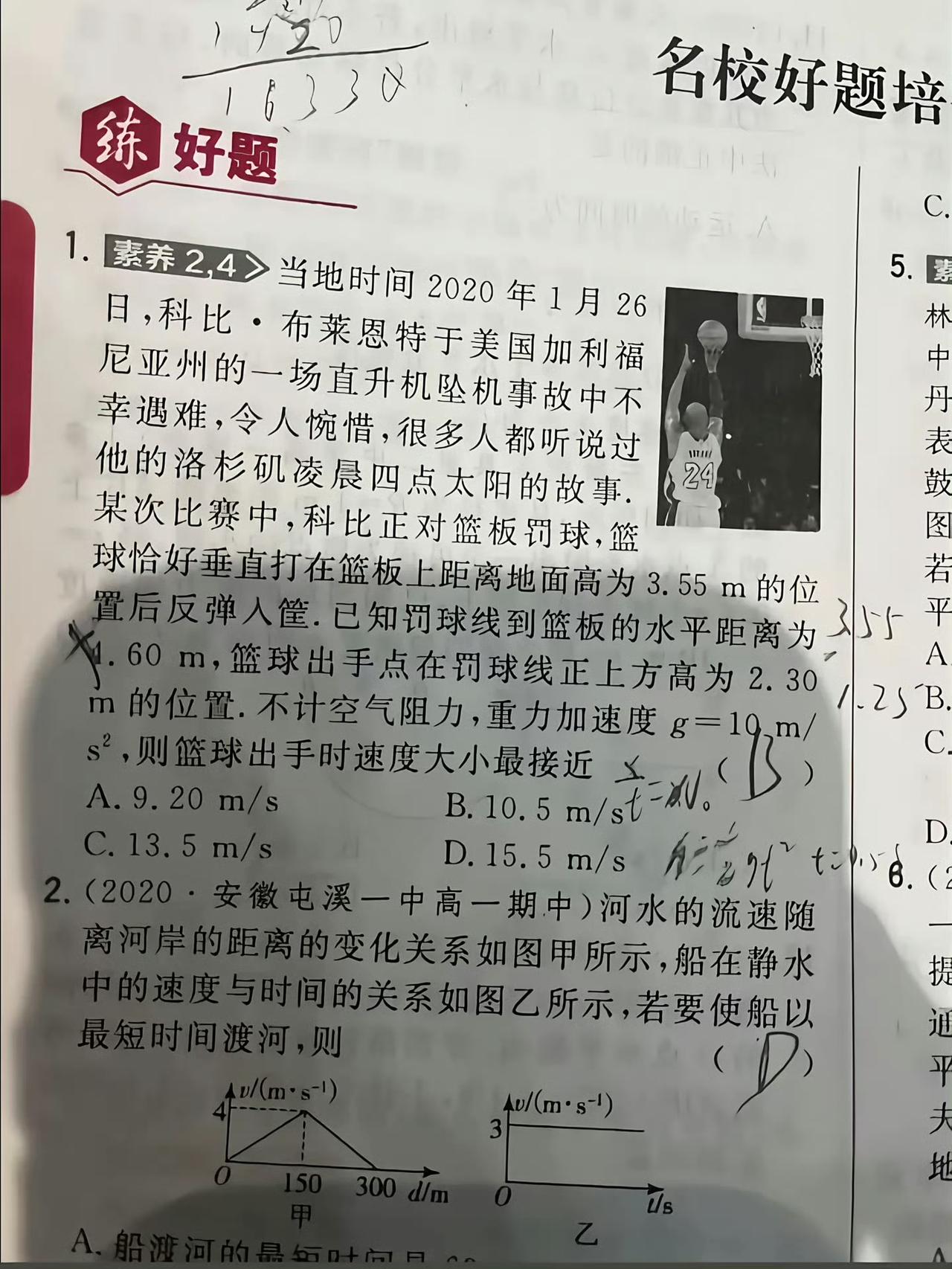
![好家伙,热干面也开始国补了吗[笑着哭]](http://image.uczzd.cn/2119075920130567036.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