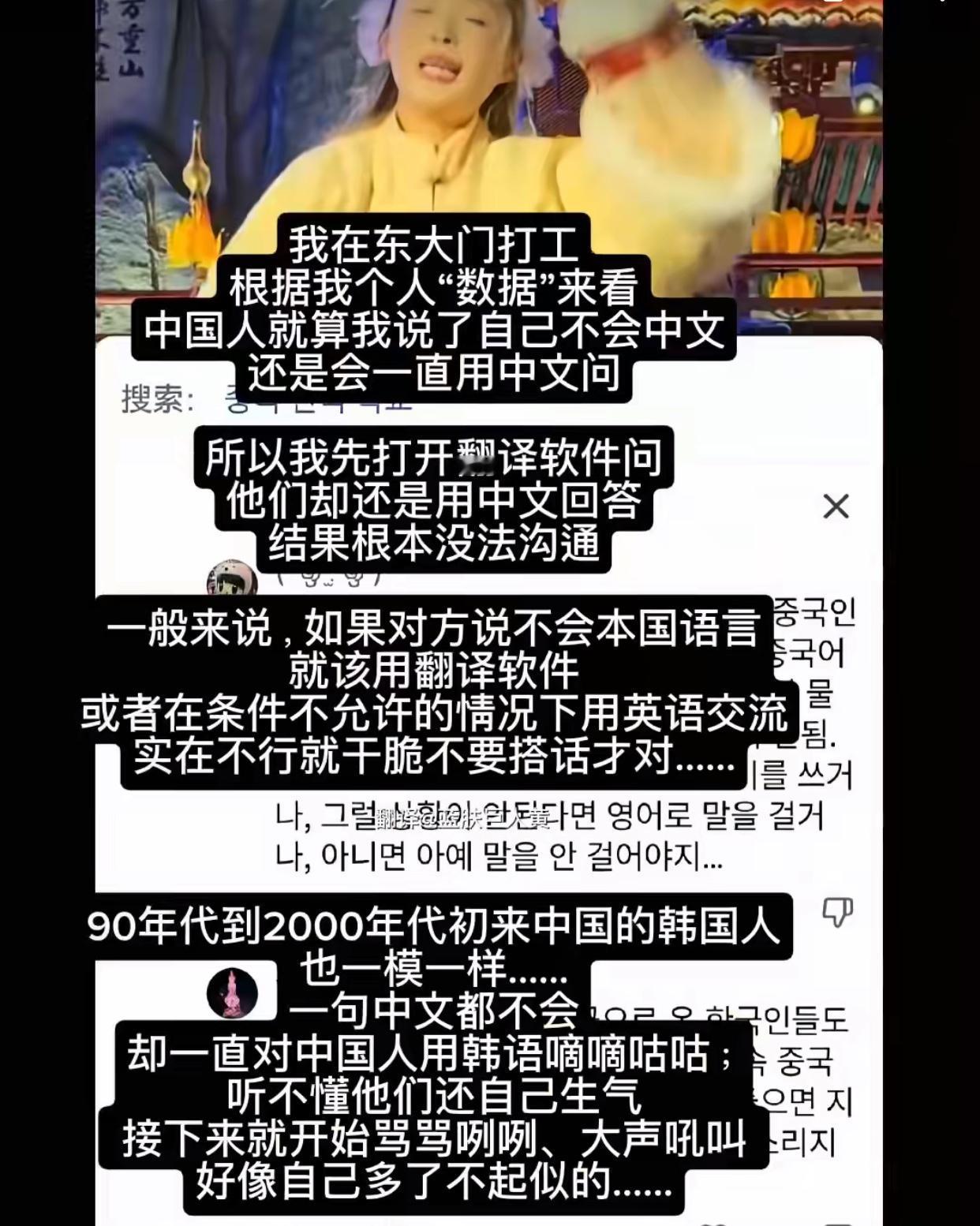今天真过瘾,姐姐终于爆发了! 早上六点半我去她家送包子,看见她把衣柜最顶层的旧皮箱拖了出来,箱角的贴纸还是十年前我陪她去上海玩时买的,当时她说“等退休了再打开”,现在却用剪刀“咔嚓”剪断了捆箱子的麻绳。 皮箱里露出件湖蓝色的旗袍,领口绣着一小朵栀子花,是她二十二岁参加纺织厂技能比赛得的奖品,后来总说“穿这个不像当妈的样”,压在箱底快二十年,旗袍下摆还沾着点当年领奖时蹭到的红地毯绒毛。 九点菜市场门口的早市快散了,她平时都是挎着布兜跟在我妈后面,今天却蹲在卖茉莉花的小摊前,指尖捏着串花苞轻轻晃,花瓣上的露水溅到她手背上,像撒了把碎星星。 摊主王婶用塑料袋装着花递过来,“你上次说想把阳台的旧花盆利用起来,这茉莉好养,晒晒太阳就开花。” 姐姐的手往后缩了缩,我看见她无名指上那枚银戒指——是姐夫刚认识她时送的,后来嫌“干活碍事”,摘下来串在钥匙链上,磨得边缘都发亮了。 “我……我怕养不活,阳台光照好像不太够。”她声音跟蚊子叫似的,眼睛却瞟着旁边摊主手机里的照片,是人家用旧鱼缸改的花盆,里面的茉莉开得正旺。 王婶把花盆塞她怀里,“你当年在厂里管的花圃,哪盆不是枝繁叶茂?上个月张阿姨还说,你给她家病蔫蔫的绿萝换了土,现在都爬满窗台了。” 这话像点了把火,姐姐突然抱着花盆站起来,转身就往家走,路过卖早点的摊子,还特意买了个甜豆浆,是她以前总说“太甜了对牙不好”却偷偷咽口水的那种。 中午我妈来电话,“你姐是不是魔怔了?把阳台的旧洗衣机挪到储藏室,说要腾地方放花架,还翻出你爸那把旧锯子,说要自己改花盆!” 我跑去姐姐家时,她正蹲在阳台地上,戴着姐夫的旧手套锯木板,木屑飞了满脸,她也不擦,嘴里还哼着歌——是当年技能比赛领奖时放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跑调跑得厉害,却比任何时候都好听。 “你不拦着点?回头把楼下邻居吵着了。”我帮她扶着木板,看见她耳朵上别着朵刚摘的茉莉,是她早上买的那串开了的第一朵。 姐姐把锯子往地上一放,拿起块砂纸打磨木板边缘,“楼下李奶奶昨天还说,她年轻时想学拉二胡,怕人笑话没敢学,现在耳朵背了,拉啥都听不清了。” 她突然停下来,指着阳台角落里那盆半死不活的仙人掌,“那是小宇出生时朋友送的,我说‘当妈的人哪有功夫养花’,结果它跟着我受了十年委屈,今天起,我要让它好好活,也让我自己好好活。” 小宇放学回来,看见阳台上堆着的木板和花盆,“妈,你要当木匠啊?” 姐姐把他拉到身边,拿起块画着小兔子的木板,“不是木匠,是给你的兔子窝,以后阳台归我们俩,你负责给茉莉浇水,我负责给你讲故事,就讲当年妈妈怎么得的旗袍,好不好?” 小宇搂着她脖子笑,“好!还要讲妈妈锯木头锯到手指头的故事!” 姐姐低头看了看被木屑蹭脏的手,指尖在旗袍领口的栀子花上摸了摸,突然红了眼眶,却笑得比花还艳,“傻小子,妈妈才不会锯到手呢,妈妈现在啊,什么都敢试,什么都能做好。” 你说,人心里的那点念想,是不是就像这茉莉花苞,只要给点阳光和勇气,就一定能开得热热闹闹? 晚上我帮她把改好的鱼缸花盆摆在阳台,里面的茉莉已经有两朵完全绽开了,香气飘得满屋子都是,姐姐靠在门框上,手里拿着当年技能比赛的奖状,正用手机查“成人旗袍设计班”的招生信息。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湖蓝色的旗袍角上,落在她亮晶晶的眼睛里,也落在小宇画的“妈妈和茉莉花”的画上,画里的妈妈笑得嘴巴都咧到了耳朵根。
![穿旗袍装登上山顶,实属不易[比心]就像登上最高舞台,成为闪耀的女主旗袍](http://image.uczzd.cn/17835986022193209550.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