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神论是华夏传统美学体系中极富民族特色的理论之一,它广泛涉及作品真实、意象构造、创作方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文艺美学问题。本文拟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视角切入,对其作一整体论述。

《形神之辨与六朝诗学精神的建构》

上篇:历史演进中的逻辑展开
追踪华夏艺术文化发展史可知,中国古典美学形神论起步于对“写形”的追求,成型于对“传神”的标举,深化于对“体道”的自觉。
传统美学形神论滥觞于先秦以来的哲学形神论,而形神作为美学问题明确提出于艺术领域,则以绘画为发端。绘画艺术起步于对“形似”的向往,按古人定义,“画,形也”(《尔雅》),“形,象形也”(《说文》)。这颇具原始意味的定义告诉我们,绘画作为造型艺术,是以摹形造象的方式来直观生动地反映现实世界的。
因此,形象塑造跟客观对象在“形”上的似与不似,就天然地成为衡量绘画真实性的第一个也是最起码的标准,尤其在绘画艺术发展的初期是如此。
从艺术实践看,传统绘画中最先发达并受到重视的是“写生”艺术。这从出土的原始陶器和今天发现的原始岩画上所刻画的鱼、羊等动物以及人的形象可以窥知。
由于上古人类审美力和表现力低下,他们只能粗略的区别和表现对象的最基本特征,所谓“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即指此。但这只是初级阶段的形似,随着写真画(人物肖像)继写生画而起,对形似的追求发展到高级阶段。
汉代的人物写真在形似上已达到十分逼真的程度,如《西京杂记》卷二记载:汉元帝时,“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必得其真”。运用笔法技巧,准确反映人物的外部特征,此乃当时写生画和写真画共同的审美要求。
而理论作为实践的反光,当然也未能逸出这时代风尚的轨辙。考察散见于各家著述的文字可知,绘画美学形神论正是肇始于对“形似”的理论自觉。
中国历史上率先借“形”论画的,首推先秦时期思想家韩非。

《韩非子集解》
据《韩非子·外储说》记载:“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见)于前,不可类之(‘可’后当脱‘不’,应为‘不可不类之’——引者),故难”。
这里,对绘画提出的审美要求是“形似”,至于“神似”则末涉及。自先秦而汉至魏晋六朝,这种惟“写形”是重的创作美学观有很大市场,时人每每说“存形莫善于画”(《历代名画记》引陆机语)。
难怪明人李日华有如下断语:“魏晋以前画家,惟贵象形,用为写图,以资考核,故无取烟云变灭之妙。擅其技者,止于笔法见意。”(《竹嬾论画》)
随着形神理论在各艺术门类的拓展,画坛“形似”之风亦吹进了文学领域。自汉大赋以来,文学创作追求形似渐成一种社会风尚。沈约即称赞“(司马)相如巧为形似之言”(《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亦曰:“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体物之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文心雕龙·物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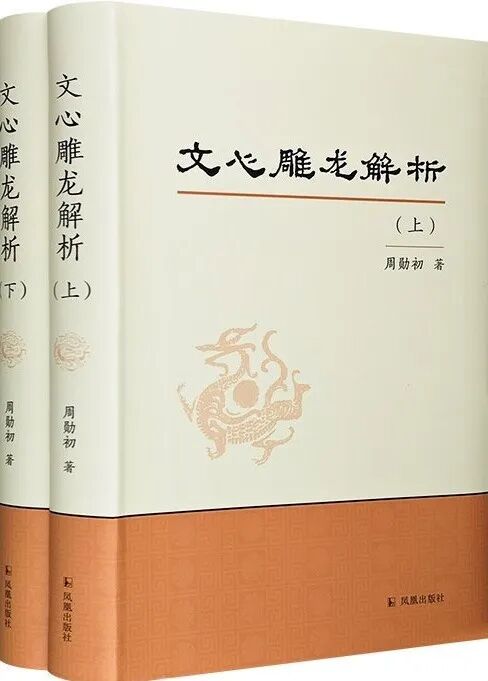
《文心雕龙解析》
诗歌美学家钟嵘对形似之作也大加褒扬,如他评张协“巧构形似之言”并列之入“上品”(《诗品》)。这种崇尚形似的风气,至唐犹存,托名王昌龄的《诗格》中有语曰“了然境象,故得形似”,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所列“十体”亦有“形似体”并释云:“形似体者,谓貌其形而得其似。”
对“形似”的追求为中国美学形神论撩开了登场的帷幕,但其理论思维的成熟,则是基于对“形似”反思之上对“神似”的自觉。
随着时代进步,人们的审美力和表现力日益提高,艺术家在汲汲追求形似于对象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发现一严峻事实,就是“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淮南子·说山训》),对对象外形描绘上刻意求似反招致创作不成功——作品缺乏鲜活的审美吸引力。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画者的失败在于“谨毛而失貌”(《淮南子·说术训》)、“规画人形无有生气”(《淮南子·说山训》),自然主义照相式的摹形妨碍了他们捕捉对象身上那真正感人的“君形者”——统摄一切形与貌的内在精神、内在生命。
实践促使人们在看到“形”乃“生之舍”的同时更悟及“神”乃“生之制”。二者的关系是一主一从,不可易位,“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淮南子·原道训》)。
他们从“神贵于形”的逻辑上推导出“以神制形”的观念,于是汉代萌生出要求传达对象内在“生气”(而不仅仅是外在形貌)的“君形”观念。
这一思想,到东晋画家顾恺之处得以明确和完善,顾以其对艺术创作中形神关系的深刻体悟和卓绝见识,创造性地提出“以形写神”的著名美学命题,从而率先在历史上扬起了中国美学形神论的大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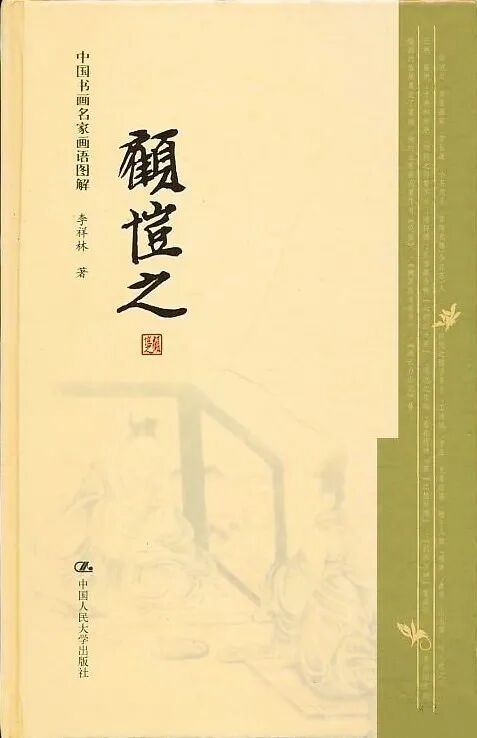
《顾恺之》
学界曾有人认为顾恺之“重神似而轻形似”,其实,仅从顾氏提出的“以形写神”命题即可看出,他是形神并重,主张形神兼备的。他要求在形似的基础上达到神似,认为在写形体貌上稍有闪失,都可能导致所绘对象“神气与之俱变”。
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形神论的创立者,顾恺之不仅首次在绘画艺术领域明确表述了“传神”的要求,而且率先从理论上阐述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从不以“形似”为满足而进一步要求“神似”这点上,不难发现顾氏绘画美学观创新的一面;而在主张“传神”的同时又不舍弃“形似”,视后者为达到前者之不可少的前提、基础这点上,又能看出其理论对传统画学继承的一面。
若说重“神”标志着他对先前崇尚“形似”观念的突破,那么重“形”则意味着他对此绘画传统思想的继承。惟其有继承又有突破,所以顾恺之提出的不是重神轻形而是形神并重的“以形写神”说[1]。

《中国古典绘画美学中的形神论》
这种形神兼备的“传神”美学思想,后来更有人把它概括为“意得神传,笔精形似”(张九龄《宋使君写真图赞并序》)或“形真而圆,神和而全”(白居易《画记》)。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从重形移向形神并重,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不过,由于“以形写神”命题原本就诞生于对艺坛汲汲于形似之风的不满,其本身即隐含着“传神”是目的而“写形”是手段的思想,于是,随着肇自先秦哲学的“得意忘象”、“得鱼忘筌”理论,经魏晋玄学的大力弘扬而盛行,随着“传神”理论由画而书而诗文拓展并经历代艺术家美学家张目,晚唐诗歌美学家司空图继顾恺之之后又提出了“离形得似”这别具独创精神的美学命题。
跟既讲“神和”又讲“形真”、以后者为达到前者之必要途径的顾氏命题有别,“离形得似”是以他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为要旨的。在要求艺术作品务必“得其神似”这根本点上,他俩并无二致,但司空图对“形”的看法则迥然相异。
依他之见,适度的“离形”(变形、移形、略形等)不但不会妨碍反而会有助于更好地“传神”。司空氏理论在宋元时期经苏轼、倪瓒等人发挥,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美学影响甚著,成为传统美学形神论中与顾恺之学说并峙的双峰[2]。
古典美学对形神问题认识上的两次理论飞跃,其结果便是“神似”取代“形似”成为中国美学形神理论的核心,由此华夏古典美学形神论在学说建构上走向成熟。
随着“传神”观念的树立,中国古典美学形神论又在“体道”意识的日益觉醒中得到深化和升华。
“道”是先秦道家哲学美学的核心范畴。老子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作为“天下母”是世间万有的本根本源,它无始无终,往复无穷,生生不已,是主宰并超越一切有限事物的宇宙生命本体。

赵孟頫书《道德经》
标举“离形得似”美学观的司空图对老子之学就情有独钟,尝自称“取训于老氏”(《自戒》),在其所著《二十四诗品》里,与“传神”之“神”一样时见提及的就多处有“道”。从艺术形象塑造角度看。这“道”与“神”的关系如何呢?或者说,古人在讨论“传神”时何以会提出“体道”呢?
欲明乎此,不妨回顾一下庄子学说中的形神论。
庄子弘扬了老子的道论,曾提出“精神生于道,形本于精(神)”(《庄子·知北游》)的哲学命题。其本意尽管是要说“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实际上却在强调“道”、“神”有别的同时向我们宣明了“道”、“神”相通。“道”不同于“神”,乃指宇宙造化的生命本体;“神”有别于“道”,乃指具体事物的精神本质。
不过,从根本上讲,二者又相关相通:“神”作为具体事物的精神本质体现着宇宙造化的生命本体;“道”作为宇宙造化的生命本体又融注于具体事物的精神本质。

《魏晋南北朝形神关系论》
中国美学形神论在提出“传神”时又要求“体道”,正是希望艺术创造者的审美视线从有限穿透到无限(正如从“写形”转向“传神”是从有形超越到无形一样,此乃审美悟性提高和理论思维成熟的标志)。
纵观华夏美学发展史,这种“体道”意识实际上已随美学形神论创立而萌芽。作为深受玄风熏陶的魏晋名士,顾恺之在讨论人物画“传神写照”问题时,便初步涉及“道”之表现问题,其评《北风诗》一画曰:“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论画》)
“玄赏”二字,当是从老子学说中“玄览”脱胎而来的术语。老子常用“玄”指称幽深微妙、高远莫测的“道”,故扬雄释曰:“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太玄》)《道德经》第十章:“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所谓“玄览”,即指对“道”的观照。
“玄赏”与“玄览”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专指从审美角度对“道”的观照(“赏”即审美欣赏,鉴赏)。
顾恺之的本意是说,通过艺术而从审美上去体味“道”。若说顾氏讨论传神问题时对“道”、“神”关系讲得还不够明确,那么,南朝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以神发道”则再清楚不过了。
对此命题,今人解释多歧。其实,将《画山水序》纳入传统文化语境中仔细审读可知,“神”乃指客观对象之神,“道”乃指宇宙造化之道。
宗炳原意当如此:为了表现“道”这宇宙造化之生命本体,艺术家在创造艺术形象时,不只要把握能“媚道”之“形”,更须由此进而捕捉能“发道”之“神”;惟有超越外在有限的“形”去把握对象内在生命的“神”,方能更直接地窥视、发见那作为宇宙造化之生生不息的生命本体——“道”。

《宗炳评传》
顾、宗二人不约而同地在讨论传神问题时提及“道”,这绝非偶然。有人说,传统画学所谓“传神”之“神”不仅指“对象的精神(spirit)”,还应包括“从对象身上所体味出的宇宙的spirit”[3]。此言不无道理。
司空图在讲“离形得似”的《二十四诗品·形容》篇中又提出“俱似大道”,其本意借僧肇语言之,也无非是要说“道与神合,妙契环中”(《肇论·涅槃无名论第四》)。
这位美学家对“道”的重视较前人更胜一筹,这不但从“道”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二十四诗品》可得证,而且从他事实上认定“俱道适往”、“由道返气”能更有助于创造“生气远出”的“精神”之作亦可知。
司空图不单要求通过“传神”而“体道”,而且希望艺术家站在“体道”——把握宇宙造化生命本体的高度上来俯瞰“传神”作品的创造。换言之,他不仅希望作者通过创造作品去由小(神)窥大(道),且希望其能通过由大(道)观小(神)来创造作品。

《司空图诗学渊源考论》
依他之见,作品之能“生气远出”,就因其能“以神发道”——以自身之神体现宇宙之道;其之能“以神发道”,又因它本身是艺术家“体道传神”——在把握宇宙之道前提下创造作品之神的结果。
若说顾、宗二人是从“传神”角度出发去讲“体道”,司空氏则是更进一步从“体道”角度回过头来看待“传神”。从“传神体道”到“体道传神”,这在理论发展轨迹上划出一个圆圈,此乃螺旋式上升的圆圈,意味着一种认识上的深化和理论上的完善。

下篇:逻辑展开中的理论建构
从古代美学家由“写形”而“传神”而“体道”的视界转移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美学形神理论的内在逻辑展开过程,这就是从对象再现到主体表现再到生命体验。
一般说来,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以唐代为分水岭,在审美趣味上发生了从重繁缛浓丽到重平淡简远的嬗变,在艺术观念上出现了从倡导肖物写实向标举抒情写意的转型。
先秦两汉艺术对“形似”的追求,所看重的是客观对象的艺术再现,其发展到极端,则不免迷失于琐碎的外在写实之中,结果,“纤细过度,翻更失真”(谢赫《古画品录》),滑向自然主义泥潭。
惟其如此,这种一味追求照相式再现的“形似”派理论在中国始终影响不大,尤其是唐宋以降,更被艺术家和美学家普遍抨击。杜子美批评同时代画家韩干即云:“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黄山谷批评一位姓徐的画家亦曰:“徐生作鱼,庖中物耳。虽复妙于形似,亦何所赏?但令谗獠生涎耳。”(《题徐巨鱼》)元明诸家则更是大讲什么“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汤显祖《合奇序》)、“形似者,俗子之见也”(汤垕《画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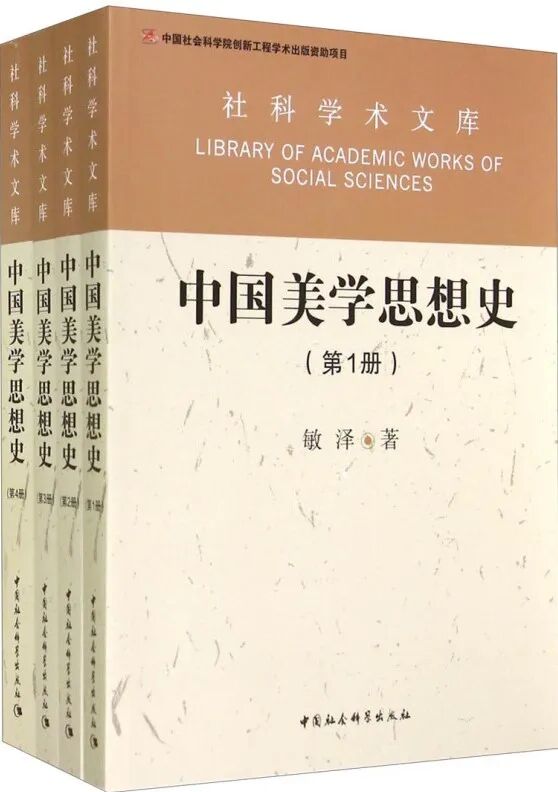
《中国美学思想史》
值得一提的是,唐以前大致是作褒义使用的“形似”术语,在宋元以来的艺术美学论著中则基本变成一个贬义词[4]。
国内美学界有一流行观点认为,中西美学的分野在于西方美学重再现、重写实、重摹仿而中国美学重表现、重写意、重抒情。其实,先秦讲“观物取象”(《周易》),六朝讲“应物象形”(谢赫《古画品录》),五代讲“度物象而取其真”(荆浩《笔法记》),凡此种种,都很难定为艺术中自我表现理论的依据。
虽然任何艺术作品在实践上都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主客观统一的产物,但作为兼具艺术家和理论家双重身份的顾恺之,其理论兴趣始终是放在对象之形、神的绘写再现上的,这从他传世的三篇画论不难看出。

《中国美学史》
即使在唐以后,尽管主宰艺坛的思潮渐由重客观写实转向重主观写意,顾氏主张形神兼备的美学形神观,于后世文论、画论中仍时时得到阐扬、发挥,这只消翻翻明清人的美学论著便可知。
“传神”作为华夏美学形神论的核心,这“神”是指对象之神还是指主体之神抑或二者兼指呢?
我以为是两者兼指。因为实践证明,“传神”之作既为人所创造,就必是黑格尔所谓“诉之于心灵”的精神产品;被艺术家之眼所发现、假艺术家之手所传达出来的对象之“神”,必然会烙上创作主体之“神”的印记,“物之神必以我之神接之”[5],方有艺术中“传神”作品的诞生。
无论在主张“以形写神”的顾恺之时代,还是在标举“离形得似”的司空图时代,或者在高喊“不求形似’的倪云林时代,这都是亘古不移的。
不过,在物我之神的偏重(不是偏废)上,此三阶段又有明显差异:
在顾氏时代,由于客观写实乃是艺坛主潮,主体之神尚隐蔽在对象之神背后,人们在理论上自觉意识到的主要是后者而非前者(理论上未意识到并不等于说前者在创作实际中不存在);在司空氏时代,随着主观写意被提高到与客观写实同样重要层面上(这从唐人喊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口号可知),主体之神亦跃身前台而与对象之神平分秋色,人们始将二者置于同等高度从理论上加以强调;在倪氏时代,由于写意取代写实而居艺坛首座,对象之神渐受冷落而退隐主体之神背后,这时人们在理论上更看重我之神而非物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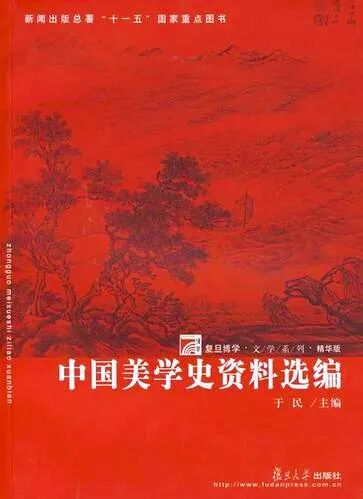
《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
一言以蔽之,“传神”三阶段可概括为:重对象而略主体→兼重对象和主体→重主体而略对象。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洗炼》篇中论及艺术创作时,曾提出“古镜照神”的美学命题。
据我分析,它是司空图著作中与“离形得似”同样重要的涉及形神论的命题,其内涵指称乃是“以心照神”,即“指艺术创作过程中主体以虚静空明之心去鉴明(从直觉上把握)对象那远出不尽之神”[6]。
顾恺之讲“写神”以“形”,司空图讲“照神”以“心”,一偏重创作对象,一偏重创作主体,理论兴趣分野一目了然。从对客观写物写真的注重,到注重主观写心写意的觉醒,正是传统美学形神理论向纵深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
肇自司空图的写意论形神美学观,后来经苏轼、倪瓒等人张目而大成气候。有别于写实论美学形神观,写意论美学形神观为突出主体之神,是以在“形”上对写实的部分牺牲为代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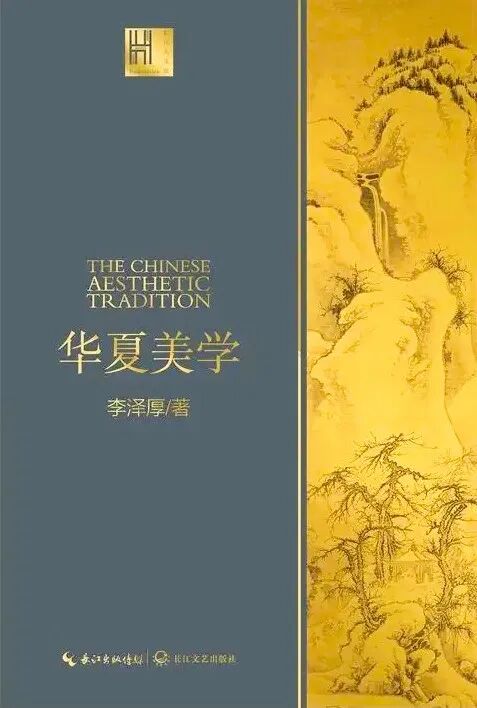
《华夏美学》
以顾恺之为代表的写实论形神观是以主张形、神不可离分之一元论为基础的,其尚未顾及留什么空间给主体之神;以司空图为代表的写意论美学形神观是以主张形、神可以离分之二元论为基础的,其正是从对客观对象之形的汲汲摹写上超越出来后才发现了主体之神自由驰骋的天地。
倪云林作画,之所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答张藻仲书》),为的是“写胸中逸气”(《跋画竹》)。明四家之一沈周讲得更坦率,“写生之道,贵在意到情适,非拘拘于形似之间者,如王右丞之雪蕉亦出一时之兴”(《题画》)。
唐代王维不拘形似绘雪地芭蕉图,正为“离形得似”的美学理论提供了创作实践范例。究其根本,这被宋人誉为“迥得天意”(沈括语)之佳作,乃是艺术家“以心照神”而非“以形写神’的产物。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主张“离形得似”的写意论美学形神观和主张“以形写神”的写实论美学形神观对形、神关系把握上两个重大差异:在“形”上,一方注重,一方看轻;在“神”上,一重客观,一重主观。
作为再现论美学形神观的集大成者和作为表现论美学形神观的开先河者,顾恺之和司空图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学术地位应是无可怀疑的。
再现论美学形神观要求传对象之神,注重对客观对象生命的捕捉;表现论美学形神观要求传主体之神,注重对主体自我生命的展示。但二者在把艺术看作现实个体生命的感性显现并以之为沟通宇宙生命本体的媒介这一根本点上则殊途同归。
对艺术本体的终极追问告诉我们,艺术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艺术源自人对生命意义的深沉体验和反思,它是这种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精神的反思和体验的象征化、符号化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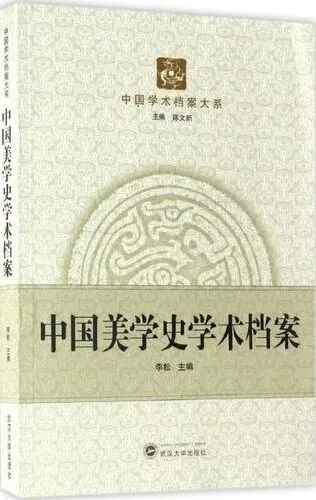
《中国美学史学术档案》
而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在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中,又总是以对现实中物或我之“神”的叩问而以对宇宙造化之“道”的参悟告终的。“艺者,道之形也。”(刘熙载《艺概·自叙》)
华夏古典美学与艺术自先秦以来,就十分注重对宇宙生命本体——造化之“道”的体悟和把握。
历朝历代艺术家和美学家不仅把对“道”的体悟视为人生最高审美境界,同时也把“道”的表现看作艺术最高审美理想。在苍茫浩漫的时间长河里,个体的生命存在转瞬即逝,昙花一现;宇宙的生命洪流生生不息,亘古永存。
也许,正是出于深层的原始的本能的生之忧患意识,人类才学会了审美,创造了艺术,试图借助艺术和审美的双桨驶动人生之舟,冲破个体“小我”生命的有限去观照宇宙“大我”生命的无限,从而获取一种永恒感和不朽感。
我们的祖先孜孜以求“天人合一”,把“道”悬为艺术生命实现的最动人辉煌的澄明之境,又何尝不是基于这样一种对生命永恒感的执着和追求呢?!

《美的历程》
“妙造自然”,此乃中国艺术家美学家高扬的艺术美之理想,而“妙造自然”之“妙”,恰与“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道”息息相通。“传神写照”,这是传统美学形神论安排的至上使命,而在此“传神”使命的表层结构下,又积淀着“体道”意识的深层内容。
由此,我们豁然发现,中国古典美学形神论有一个自成体系而逻辑严谨的理论构造,这就是以“神”为轴心向两极展开,一端为“形”,由“形神关系”组成该理论的表层结构;一端为“道”,由“神道关系”组成该理论的深层结构,而从“形”到“神”至“道”的递进,正是艺术家审美创造步步深化的审美历程,也就是中国艺术家借助审美创造努力摆脱“形而下”之局限朝着“形而上”之澄明实现心理超越的不懈过程。
于是,我们又顿然醒悟,形神论作为华夏美学一大分文,它同样有着与生俱来的那种富有民族特色的以超越为旨归的生命哲学意味。
然而,据笔者所知,迄今已有的美学论著对传统美学形神论的探讨,基本上囿于表层而未及其深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其实,中国美学形神论设定的中心范畴是“神”,而“神”除了作为古代哲学中与“形”相对、指称人之内在生命的概念使用之外,它在先民意识中还有一更原始古老的含义。
追溯历史可知,“形神在春秋各家思想中,未形成对举概念”,此前,“神的涵义偏重于人所崇拜的对象方面”。金文中“神”字屡见,从词源学意义上看,“神,从示申。申,电也。电,变化莫测,故称之曰神……神字周以前无示旁,祗作申,此乃申电神三位一体之证明”[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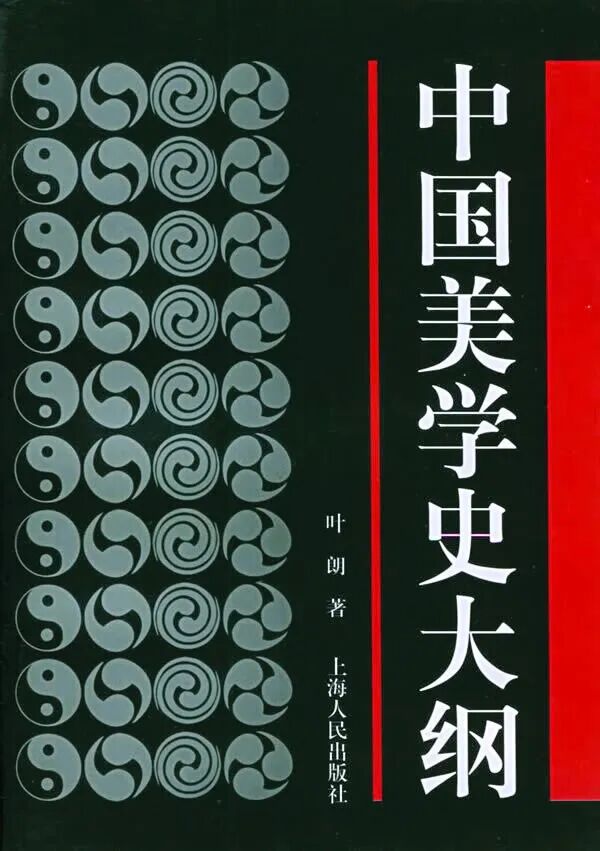
《中国美学史大纲》
在此,“神”的内涵指向不是人的自我生命而是外在于人的自然现象。在认知能力低下的先民眼中,雷电神秘莫测而不可理喻,是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
引申开来,“神”也就被先哲们用作宇宙造化本原及其变化发展原因的解释,如《荀子·天道》所言:“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此即所谓“天下之动,神鼓之也”(《张子正蒙·乾称》)。
但事物变化之终极原因不是“神”而在“道”,“道”作为宇宙万物的生命本源,其变化无穷,故曰“神”(《易·系辞》言“阴阳不测之谓神”,即是此意)。这便是有别于形神论之“精神”的“神”在上古哲学中的又一意指。
正因为“神”在华夏传统哲学中一身兼具二义,所以,作为中国美学形神论之核心范畴的“神”也就自然而然地指向两极:形神关系和神道关系。
当然,这仅仅是词源意义联系上的考究,从更深层更内在的文化原因看,从理论构造上将形神关系和神道关系统摄一体的还是华夏民族那根深蒂固又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意识。
换言之,正是在这主客相契、物我共感的“天人合一”观念统摄下,华夏民族在我之神和物之神、个体生命和宇宙生命之间觅得沟通、悟出同构,并将此得自直觉体悟的洋溢着终极关怀光辉的生命超越感艺术地形诸作品以存之不朽。

《神话·民俗·性别·美学——中国文化的多面考察与深层识读》
结语:
中国古典美学形神论经过从形到神至道的视界转换,完成了它从再现到表现到体验的逻辑展开,从而建构起一个以形神关系为表层结构、以神道关系为深层底蕴的理论体系;它起自于对现实个体生命的追问,成就于对宇宙本体生命的体悟。历来人们对形神论的研究都限于表层而未入其深层,事实上,惟有切入其深层,我们才会发现,中国传统美学形神论的逻辑归属在于它实质是一种生命对有限时空超越的学说,这既是作品艺术生命的超越,更是作者人格生命的超越,前者勿宁说是后者的折射或投影。
而这种生命超越意识正是中华民族奋发不息、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它不仅积淀在传统美学形神论中,也显影在传统美学气韵论、意境论、虚实论、动静论等等之中。它是形神、意境、气韵、虚实、动静等一系列华夏古典美学学说共同的逻辑归属。
注释:
[1]李祥林《试析顾恺之“以形写神”的绘画美学观》,载《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
[2]关于司空图的美学形神观,详见李祥林的硕士论文《司空图“离形得似”说与传统美学形神论》,安徽师范大学1990年4月印制。
[3]洋溟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189页。
[4]李祥林《论“离形得似”说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5]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5页。
[6]李祥林《“古镜照神”新解》,载《江海学刊》1990年第6期。
[7]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62、6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