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俊捉了一个清兵的俘虏,可是这个俘虏还几次三番地要见他,韦俊就感觉到挺奇怪:一个俘虏要见我?莫非其中有什么隐情?
韦俊思虑再三,一挥手:“带上来!”亲兵答应一声,转身退出。韦俊顺手拿起一册兵书,无意地翻弄着。门外一阵脚步声响,六名亲兵把一个人带进书房。
韦俊抬头观看,见此人身高六尺左右,宽肩细腰,一张洁白红润的脸膛,剑眉入鬓,一对大眼,举止安详,气度不俗。与他身上的装束,极不相称。
此人往前大跨一步,躬身拱手道:“小可拜见将军。”韦俊已清楚地发现,这个人绝不是什么普通的俘虏。他马上警觉起来,正色问道:“你是什么人,见本督何事?”
亲兵见主将有了怒色,也跟着吹胡子瞪眼,严肃起来。左宗棠一不着慌,二不着忙,从容地答道:“请问将军,这里说话可方便?”“这……”
韦俊稍微一怔,接着说道:“本督一向光明磊落,从来不做背人的事情,有话你就说吧!”左宗棠道:“实不相瞒,小可乃朝廷的使者。奉曾大帅之命,前来下书。”
这几句话好像一颗炮弹,在韦俊头上炸开了!把他吓得身子一哆嗦,脸色苍白。只见他站起身形,勃然大怒道:“原来是个奸细。本督与清妖仇深似海,没必要书信来往。来人!把他推出去斩了!”
“是!”亲兵一拥而上,将左宗棠捆绑起来,往外便拖。左宗棠哈哈大笑道:“人言韦俊乃顶天立地的英雄,原来却是个胆小如鼠之徒。”
恰在这时,韦俊的心腹谋士何亮光赶到了。他望着被推出去的左宗棠,慌忙来到韦俊面前,低声说道:“大人息怒,此人杀不得!”“为什么?”
何亮光道:“大人,先别杀他,容卑职讲完了再定。”韦俊点点头,传令道:“先把这个奸细押起来,听候发落!”亲兵马上照办,把左宗棠监禁在耳房里。
韦俊与何亮光本是同乡,自幼交厚。韦俊练武,何亮光习文,经常在一起打交道。他们随韦昌辉一起加入太平军,始终都在一处共事。
何亮光深沉老练,韦俊对他十分器重。凡有重大事情,都请他商讨。他每天晚上都要来一次,帮着韦俊决定一些军务。
今天,听说有个俘虏非要求见韦俊,觉着这里边有文章,才急忙赶来。虽然他只听着几句对话,已知来人不俗,这才把韦俊劝住。韦俊道:“有话你就说吧。”
何亮光屏退亲兵,低声说道:“依卑职观察,此人定不是等闲之辈。大人应问个水落石出,然后再发落也不迟。”
韦俊也低声说道:“我的处境非常不利,说话办事,都得格外小心。倘若这个奸细说出坏话,传到上头,可就不好解释了!”
何亮光冷笑道:“大人出生入死,杀人不眨眼睛,有什么可怕的?”韦俊点头称是。二人计议已定,命人把左宗棠押上来,解掉绑绳。韦俊严厉地喝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左宗棠坦然地答道:“大清四品知府衔,署理湘军左翼总兵左宗棠是也!”韦俊与何亮光同时一怔,彼此交换了一下眼光,心里说:果然不是等闲之辈!
韦俊又问道:“你我乃两国仇敌,见我做甚?”左宗棠说:“将军之言差矣!你我有国仇,并无私怨。曾大帅久慕将军大名,爱惜你是当世人才,特命我冒险投书。如将军将我杀了,在下也死而无怨!”韦俊道:“信在何处?”
“在这里。”左宗棠从贴身的衣服里,将信取出。何亮光接过,呈给韦俊。韦俊大咧咧地把信展开,定睛观看。信上写道:大清国钦授兵部尚书、领湘军统帅曾国藩,致书于韦俊将军麾下:
久慕将军大名,无缘相会,深感不安。近闻令叔被害,惨遭毒手,实可悲可痛。虽两国仇敌,然物伤其类也!
洪逆倡邪教,乱纲纪,毁礼义,败伦常,蛊惑人心,倒行逆施,实张角之辈。虽一时一事得逞,岂能望长久远乎,何也?邪不能侵正也。
将军诗礼传家,深明大义。因一念之差,误入歧途。如能幡然悔改,其情可谅也。杨秀清功高被害于前,令叔功重被戮于后,其罪除洪逆者谁?前车之鉴,今人能忘乎?
将军如能识大局,明利害,归顺朝廷,献城立功,本帅当向皇上力谏,确保将军之安全并委以重职,此千载难逢之机也。倘忠言逆耳,一意孤行,祸到临头,悔之晚矣。纸短情深,切望三思。
韦俊把这封信看了两遍,又叫何亮光过目。沉吟半晌,说道:“左宗棠!你们把我韦俊看成了什么人?自古忠臣不保二主,好女不嫁二夫。本将军蒙天王错爱,委以重职。韦某粉身碎骨,难报万一。岂是你等能离间了的?”
左宗棠冷笑道:“将军差矣!洪秀全为什么重用你,就因为你有勇有谋,能给他卖命。重职是你挣来的,而不是他恩赐的。试问,将军与洪秀全的关系,较东、北二王与洪逆的关系如何?”
“他们张口是天父之子,闭口是天兄之弟,到头来还不是落了个被害的下场?你是北王的侄子,洪逆又岂能放过你?不过,他眼下自顾不暇,缺少良将,暂时利用你罢了。”
“以洪逆之阴险,手段之狠毒,疑心之严重,他是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的。曾大帅素有重才之癖,切望将军弃暗投明。于国有利,于将军亦有利呀!”
“胡说!”韦俊拍案喝道,“你纵有苏秦之口、张仪之舌,也休想说动我。”谋土何亮光喊道:“来人!”亲兵们闻声而入。何亮光说:“先把他押下去!”就这样,左宗棠二次被软禁起来。
何亮光看看房中无人,又把曾国藩的信拿起来,反复阅读了几遍,又拧眉,又叹息,又不住地点头。韦俊问道:“你看这件事该如何处置?”
何亮光凑近韦俊,严肃地说道:“大人恕我无罪,卑职才敢讲。”韦俊不耐烦地说:“咱俩不是外人,少来这套!”
何亮光又小心地向外边看了看,凑近韦俊的耳边,说道:“虽然曾国藩使的是离间计,可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什么叫大义?什么叫伦常?都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依卑职之见,天王多疑寡恩,是不能放过你的。一旦形势好转,将大祸临头矣!曾国藩急于攻占武昌,不惜一切代价收买大人,机会难得!且不管他是何居心,只要对大人有利,我们就应该认真对待。常言说‘坐失良机,追悔莫及’呀!”
韦俊低下脑袋,不住地沉吟。何亮光又说道:“大人不必多虑了。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柔而不决,势必毁了自己!”韦俊说:“你说得倒是有理。不过,我觉得对名誉似乎有碍!”
何亮光大笑道:“大人何必存书生之见!名誉有什么用?只有痴人才抱着不放!秦桧、赵高、严嵩、魏忠贤,哪一个名誉好?还不是吃尽穿绝,位极人臣!再看看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又是什么下场?大人的处境与他们不同,这叫逼上梁山。是非曲直,当有公论。”
“嗯!”韦俊连连点头,“说得好!容我再认真想想。”何亮光着急地说:“大人,拖延不得!别忘了,迟则生变,夜长梦多呀!倘若消息败露出去,传到罗大纲和石祥祯耳里,可就前功尽弃了。”
“对!”韦俊以拳击案,说道:“就这样定了。”为了慎重起见,韦俊把几名心腹军官请来,说明了一切经过。众人齐声说道:“官逼民反,我等愿随大人左右!”
韦俊大喜,命人把左宗棠请来,拱手道:“在下乃一介武夫,对大人多有失礼之处,还望恕罪。”左宗棠笑道:“不打不相交嘛!我倒喜爱将军的爽直。”
韦俊大笑,急忙让座,又给众人一一引见。接着,又拱手说道:“承蒙曾大帅错爱,使韦俊茅塞顿开。经再三考虑,我等愿献城归顺朝廷,以赎前罪。”
左宗棠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将军深明大义,必然受到皇上的重用。封妻荫子,前途无量。”韦俊谢过,设宴款待左宗棠。在酒宴前,他又部署了献城方法。四更过后,才退席休息。
第二天,韦俊以出城扫荡为名,把左宗棠送出武昌。当晚,他把不信任的军旅调开。汉阳门一带,都换成自己的部队。三更天,城头上燃起五堆篝火。
接着,城门大开。左宗棠统率数万清军一拥而人,顺利占领了东门和南门,控制了武昌。有人感到形势不对,飞报副都督罗大纲和石祥祯。
原来,罗大纲的人马驻扎在西门和北门一带,石祥祯的人马驻在长江沿岸。罗大纲听到禀报,半信半疑。马上披挂整齐,点兵一千,来找韦俊。
刚走到鼓楼,迎面正遇上大队清兵。罗大纲大吼一声,催马挺矛,奔清军扑去。一千名太平军好像下山的猛虎,与清军展开激战。
罗大纲正在酣战之时,忽见清军往左右一闪,迎面一马飞来。借灯光观看,正是韦俊。罗大纲圆睁二目,喝问道:“韦俊,这是怎么回事?”
韦俊冷笑道:“实不相瞒,韦某已归顺大清了。念你我共处多年,韦某在曾大帅面前,替你说了不少好话。曾大帅法外施仁,命我前来劝降。请你认清形势,赶快投降了吧!不然,死路一条!”
罗大纲大骂道:“背主之徒,有何脸面见人?罗某乃顶天立地的英雄,不像你贪生怕死,卖主求荣!”韦俊恼羞成怒,也骂道:“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不识抬举,我就成全你了!”
说罢,用刀一指,埋伏在鼓楼四周的弓箭手一齐出动,对着罗大纲,就是一阵狂射。罗大纲身中数箭,自知难活,便拔剑在手,自刎而亡。他手下的一千军兵,也光荣战死。
韦俊把罗大纲的人头砍下,派人给曾国藩送去。然后,又领着清军,捉拿石样祯。石祥祯见孤掌难鸣,急忙退出武昌。没有几天的工夫,汉口、汉阳、黄州,相继失陷。石祥祯无奈,只好退兵九江,向天京告急。
韦俊倒反武昌,立了大功。经曾国藩保荐,被清政府封为二品副将,在曾国藩帐下效力。这小子被感动得涕泪横流,死心塌地为清政府卖命,成了太平军的死敌。
且说义王石达开,接到武昌失守的战报,心如火焚。连夜给天王送去本章,要求洪秀全降旨,派他率重兵夺回武汉三镇。谁知一连三日,不见动静,石达开更是焦躁不安。
第四天,正是天王朝会的日子。石达开早膳已毕,急忙赶到天王府。卯时三刻,钟鼓齐鸣,天朝门大开,洪秀全在乐声中升坐金龙殿。石达开率领满朝文武,朝贺已毕,分立两厢。洪秀全问道:“兄弟们,可有本上奏?”
石达开出班奏道:“四日前,小弟的本章,二哥可曾见到?”洪秀全道:“朕看到了。”义王道:“不知哥哥做何打算?”洪秀全道:“收复武汉固属重要,可是,天京初定、百废待兴,朕看不宜动兵。”
石达开分辩道:“二哥所见差矣!武昌乃自古必争之地,西通巴蜀,东连吴会,九省中枢,水陆要塞。我们需要的粮米、物资,都要靠那里运转。武昌落到清妖手里,就好似扼住了我们的咽喉,摘掉了西方的大门,对天朝的威胁太大了!曾妖早已看到这点,才不惜一切手段而力争之。现在,乘清妖站脚未稳,我们派出大兵,还可以把它夺回来。夺武昌就是保天京,保天京就要夺武昌。请二哥不必犹豫,否则,将造成千古遗恨。”
豫天侯陈玉成也出班奏道:“五千岁所奏,切中要害,请天王火速降旨才是。”洪秀全把脸一沉,不悦道:“朕何尝不知道武昌的重要?可眼下兵、粮两缺,库府空虚。岂是出重兵的时候?”
石达开道:“弟请旨率本部人马西征,粮饷自筹,无须二哥操心!”洪秀全道:“天京刚刚中兴,你怎能离开?”陈玉成道:“如天王信任,臣弟愿替五千岁一行!”洪秀全摇头道:“你有你的事做,不要再争了。”
众人与洪秀全共事多年,都了解他的为人。凡是他确定的事情,是万难改变的。石达开怀着沉重的心情退在一旁,陈玉成也默默地归班站立。洪秀全简单地问了问朝政,拂袖退殿。
义王回到府里,面沉似水,反复思考着眼前的一切。他不明白:洪秀全为什么不肯发兵,是粮饷困难吗?不是。即使再困难,该打的仗也是要打的。自己再三要求出兵,他却不予理睬,反说京里离不开自己,这难道是真的?也不是。满朝文武,能做事的很多,像李秀成、陈玉成、赖汉英等人,哪个不行?而他偏偏要把自己拴在天京,这到底是为什么?他愁肠百转,摘下宝剑,到庭院中舞剑分忧。
宁静的夜晚,声息皆无。石达开舞了一阵又一阵,只舞得精疲力竭,通身是汗,才进屋休息。一直守候在旁边的曾锦谦,也悄悄跟进房中。义王擦擦汗水,问道:“你怎么还不去休息?”
曾锦谦道:“殿下忧虑,卑职何以安寝?”石达开望着爱将,心里倍感郁闷。于是,二人对坐,促膝谈起心来。曾锦谦道:“殿下整日为国操劳,也该为自己着想着想了!”
石达开知道,他是指婚姻而言。连日来,不断有人到府中提媒,劝他续立王妃。结果,都被他拒绝了。曾锦谦接着说道:“殿下日理万机,没有个贤内助怎么能行?再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
石达开苦笑道;“还劝我呢!你不也光身一人吗?”曾锦谦道:“卑职与殿下的身份不同,不能相提并论。”
石达开笑道:“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可是泛指的,并无尊卑之分哪!锦谦,你心疼我,为我着想,我领情就是了。不过,眼下还不是成亲的时候。”
曾锦谦道:“殿下公忠体国,废寝忘食,反倒遭人猜忌。哼,卑职实在不平。”石达开问道:“谁猜忌我?”“这个……”曾锦谦欲言又止,不敢往下说了。
石达开不悦:“锦谦,你对我说话还有顾忌不成?”“不!”曾锦谦忙解释道:“殿下对我恩深似海,卑职粉身碎骨,也难报答。我知道您心情不好,不愿给您增加负担。所以,憋着一肚子话不敢说。”
石达开道:“今晚我很痛快,你就说吧!”曾锦谦说道:“据我所知,天王听了别人的谗言,对殿下心生疑忌。故此,不让你离京,也不想叫你领兵带队了。”“这是真的?”
曾锦谦道:“卑职有几个脑袋,怎敢信口胡言?”石达开问道:“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回殿下,是西王妃向女营军师苏三娘透露出来的,苏三娘要我密报五千岁。”
石达开又问道:“你可知什么人说我的坏话?”“卑职已调查清楚,是洪仁发、洪仁达,还有蒙德恩。”“他们是怎样说的?”“详情还没摸准,只知道他们要天王削掉你的兵权。”
石达开不往下问了。他把许多事情连在一起,仔细分析了一遍,可以断定,曾锦谦说的都是实情。不过,在没有证据之前,他是不愿暴露自己观点的。
想罢多时,他对曾锦谦道:“过口之言,不可轻信,也不可对旁人乱讲。”“卑职记住了。”曾锦谦说罢,便朝内宅退去。他刚走到院里,就觉着眼前有个黑影。一转眼,没了。曾锦谦揉揉眼睛,再一细找,还是没有。
心里说:难道有人偷听我们谈话?他立刻警觉起来,走出庭院。来到无人之处,抽出防身宝剑,蹑足潜踪,又偷偷地返了回来,藏在内庭的花墙边上,屏息宁神,观察着周围的变化。
这阵儿,义王屋里的灯还没止灭。石达开那高大的身影,还在窗户上晃动。突然,一道黑影,从配房上飘落到院中。
曾锦谦定睛观瞧:只见此人身穿一套黑衣服,腰束丝带,斜挎皮囊,手提钢刀,面罩青纱,五官貌相看不清楚。只见他走到窗前,小心翼翼地往四处查看了一遍,单手提刀,点破窗纸,便往房中窥探。
曾锦谦火往上撞,心里说:胆大的贼子!竟敢夜探王府。哼,我看你往哪里走?曾锦谦双脚点地,蹿到此人身后,低声呵斥道:“不许动!”说罢,剑尖指到刺客的左肋上。
这个刺客毫无准备,急忙使了个“黄龙转身”,“噌!”跳到配房下,扭身便逃。曾锦谦单手横剑,拦住去路:“站住!你跑不了啦!”刺客见势不妙,摆刀便砍。曾锦谦以剑相格,二人战在一处。
石达开刚要就寝,忽听院中有搏斗的声音,忙提剑出来观看。这时,曾锦谦与刺客已交手三四个回合。石达开飞身加人战群,双战刺客。两柄宝剑上下翻飞,刺客招架不住,抽刀便走。
义王迎面拦住,刺客捧刀奔义王胸部刺来。石达开把刀闪过,一翻腕子,宝剑奔刺客的脖项扫来。刺客躲闪不及,闭目等死。石达开将剑锋收住,抬起右腿,踢到刺客的大腿根上。
刺客站立不稳,甩手扔刀,摔倒在地。曾锦谦明白义王的意思,把他生擒活拿。这时,前院的参护们也闻声赶来,把刺客绑上。
义王回到寝室,宝剑还匣,刚坐到安乐椅上,曾锦谦便进来问道:“刺客如何发落?”义王道:“把他带进来!”
先进来两名参护,把灯点燃,垂手站在两旁。另外几名参护,连推带拖,把刺客带进房中。石达开一摆手,参护们退在门边。
石达开借着灯光仔细观看:但见这个刺客身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青纱绢帕包头,身穿青缎夜行衣,寸排骨头纽,腰系丝带,背背一把空刀鞘,斜背百宝囊,脚踏一双软底快靴。因他低着脑袋,五官貌相看不真切。
石达开看罢,威严地问道:“你是什么人,叫何名字,嗯?”刺客低着头,一言不发。曾锦谦急了,揪住他的头发,往上一提:“你听见了没有?”
刺客被迫仰起头来。就在这一刹那,石达开看清了他的五官相貌:瓜子脸,细弯眉,鼻如悬胆,明眸皓齿,点点朱唇,面皮细嫩,长得十分俊秀。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女人。“住手!”
石达开屏退曾锦谦,盯着这个女刺客,吃惊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女刺客把脸一甩,说道:“要杀便杀,何必多问?”
参护们怒喝道:“你敢顶撞五千岁,撕烂你的嘴!”“打她!”说着就要动手。石达开喝喊道:“不准胡来,把她的捆绳去掉。”
参护们不敢不听,忙给刺客松了绑。石达开又说道:“你不必害怕,只管把实情讲来,本王不会处死你的。”女刺客偷看了义王一眼,又把头低下了。
石达开站起身来,倒背双手,边踱步边平和地说道:“本王以为,你偷听也罢,行刺也罢,都不是出于本心,而是受人主使。我石某扪心自问,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情。所以,主使你的人是不公道的。也许你不明真相,受了利用;也许你贪图利禄,另有居心。总之,你这样做也是不对的。我不杀你,也不扣留你。只要你讲出真情,也就行了。”
女刺客低着头,还是一言不发。曾锦谦实在忍不住了,高声怒喝道:“你是聋子,还是哑巴?”女刺客好像没听见似的,还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石达开回归座位,说道:“既然你不肯回答,本王也不勉强。锦谦,把东西还给她,放她逃命去吧!”“这……”参护们都愣住了。石达开又说:“还愣着干什么?放她去吧!”
一名参护把刀和面纱递过去,嘟囔着说道:“给你!五千岁叫你逃命,还不快走!”说着话,把门口闪开。女刺客看看自己的东西,又看看周围的情况,突然,双腿一软,跪在义王面前,二目垂泪道:“五千岁,我对不起您。我不能走,请您处置我吧!”
屋里的紧张空气缓和了。石达开道:“我说话向来算数,放你走就是放你走,还处置什么?”
女刺客道:“人都有七情六欲,哪有不知好歹之理?罪犯受人主使,犯下不赦之罪,自认为必死无疑,没想到五千岁宽宏海量。罪犯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愿将实情供出,任凭五千岁发落。”
石达开点点头,命参护给她搬来一把椅子,又说道:“也好,那你就坐着说吧!”“不不不,吓死罪犯也不敢在殿下驾前就座,我就跪着说吧。”义王说:“叫你坐,你就坐,何必推辞。”
女刺客说什么也不敢坐,最后答应站着答话。石达开也不勉强,仔细地听着她的供词。原来,这个女人叫褚慧娘,金陵人,现年二十二岁。父亲褚振远,哥哥褚尽忠,在南京保镖为生。
太平军攻占南京时,褚氏一家均死在炮火之中。只剩下了褚慧娘。太平军进城后,建立男馆女馆,慧娘被编入女馆之中。后来,天王府选官女,慧娘中选,送进天王府,充当内宫杂役。
日久天长,人们才发现她会武艺。后来被洪秀全知道了,叫褚慧娘表演武艺。慧娘不敢抗旨,把父兄传授给她的武艺练了一遍。洪秀全大喜,封她为二品王官,负责教练天王府的女兵。
几年来,慧娘兢兢业业地供职,很受洪秀全的赏识。有时,天王还让慧娘担任他的警卫。所以慧娘得以靠近天王,了解到许多秘闻和朝堂秘事。
半月前的一个夜晚,褚慧娘奉旨在御书房给天王警卫。突然,国宗洪仁发和洪仁达来了,说有机密大事,要向天王禀奏。洪秀全让他俩进来,赐座赏茶。
洪仁发拍着圆鼓鼓的肚子,晃着肉乎乎的脑袋,说道:“你是太平天国的君王,应该亲自过问朝政。别总在宫里待着,什么也不管。杨秀清、韦昌辉的苦头,你还没吃够吗?”
洪秀全不耐烦地皱起眉头,好半天才问道:“你又听见什么闲话了?”洪仁发不服气地说道:“都是事实,哪来的闲话。你说石达开这个人可靠吗?我看他一点儿也不可靠。”
洪秀全一怔,往四外看了几眼。站在他身后的褚慧娘会意,忙施礼退出御书房。因没有天王的诏旨,又不敢回去休息,也不敢离开,就站在御书房廊檐下候旨。
夜深人静,屋里说话的声音,她听得一清二楚。由于话题关系到义王,所以,褚慧娘也就用心地听着。就听洪秀全说道:“捉贼要赃,捉奸要双。你说石达开不可靠,有什么凭证?”
洪仁发道:“就拿你封官这件事来说吧,你封他电师通军主将他不应,当众说什么德微才薄啦,不堪重任啦,显得多么谦虚!可是背后呢,他早就自封电师通军主将了。天京的老百姓都称他主将,老四,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人前一面,人后一面,两面三刀吗?”
洪仁达往前凑了凑,龇着满嘴黄板牙,也说道:“石达开到处笼络人心,动不动就到军营去讲话,要不就对老百姓讲道理。成千上万的人围着他,又叩头,又烧香,简直把他当成活神仙了!”“对!”
洪仁发插话道:“很多人都称他为万岁,万万岁,他也高兴地接受了。”洪秀全默默地听着。表面上声色不露,可心里却在不住地翻腾。
洪仁达接着说:“咱大哥说得对。你是天王,是太平天国的君主。不能啥也不问,啥也不管。照这样下去,老洪家的江山,就变成姓石的了。”
洪秀全的心猛烈一震,站起身来,在御书房转了两圈,不耐烦地说道:“够了,够了!为人处世要光明磊落,脏心烂肺要不得。朕对达胞不薄,他不会对不起朕的。”
洪仁发也站了起来,腆着大肚子分辩道:“老四呀,你吃亏就吃到犟上了。试问,你对杨秀清如何,对韦昌辉又如何?恨不能把心都掏给他们吃了。可是,到头来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要夺你的江山,逼你退位?”
洪仁达也插话道:“归根结底一句话,别人的肉再好,也贴不到自己身上。不是二哥说你,你太重用外人了,把自己的骨肉甩得远远的,一无兵权,二无政权,都让外人说了算。你呀,早晚要吃大亏的!"
洪仁发道:“咱们还说石达开吧!你想没想过,他现在的权力有多大?除天京一部分军队外,外围几乎都是他的军队,他手里光精兵就有三四十万哪!倘若他坏了良心,只要轻轻一歪嘴,咱们就得粉身碎骨。不是当哥哥的吓唬你,满朝文武、军兵百姓,几乎都是他的人了!”
洪仁达又说道:“石达开善于收买人心,比杨秀清、韦昌辉高明得多。老四,你该清醒一点儿。祸到临头,可就没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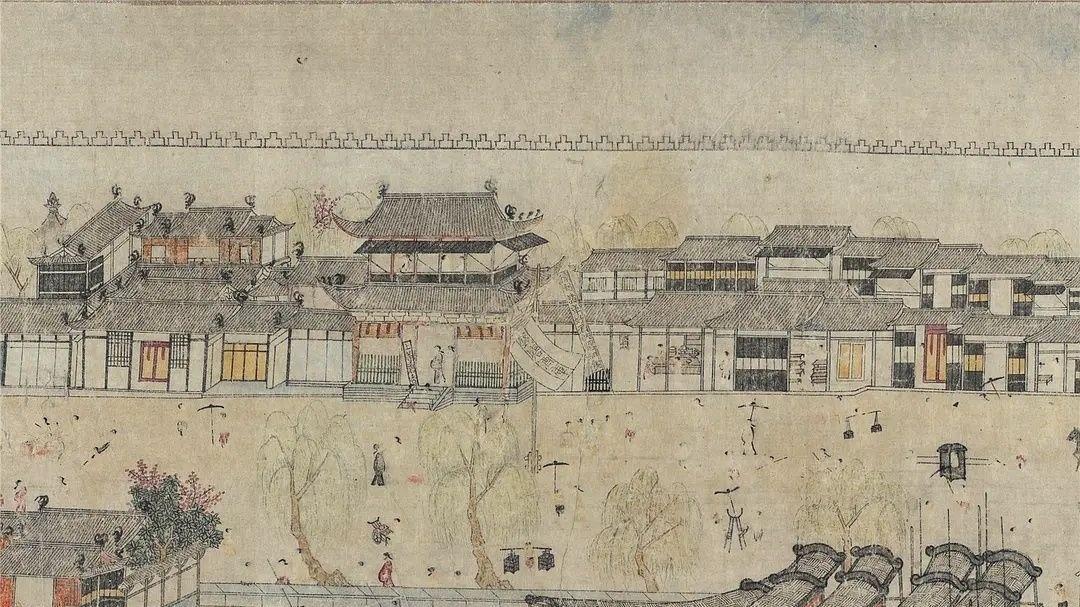

完全靠瞎编,韦俊是韦昌辉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