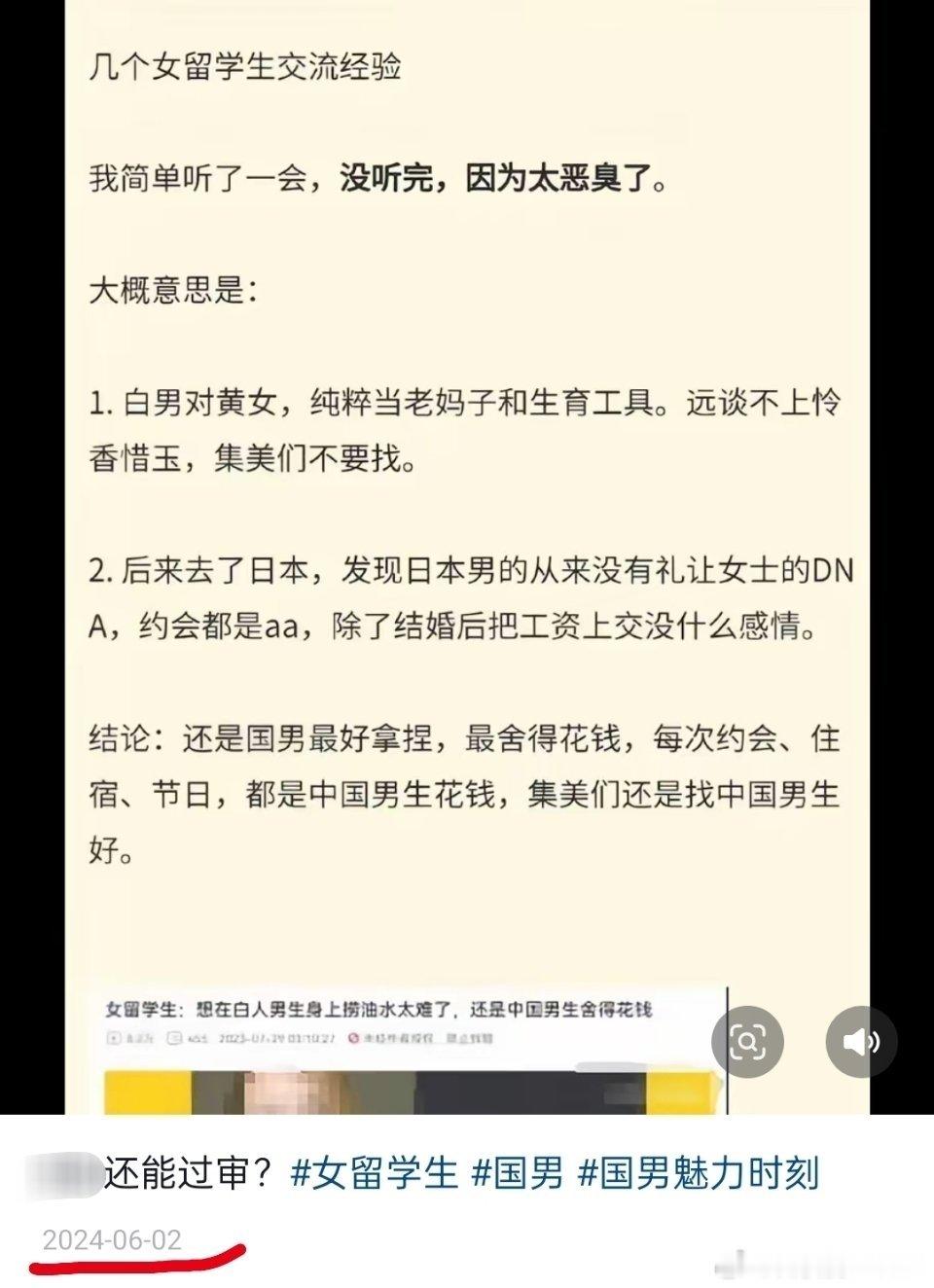一九七五年,公社突然叫我去公社农场当场长。农场里有一个人是右派,国字脸,五官分布得周正,因为常在太阳底下,和风雨中劳动,脸庞呈现出酱紫色。戴着眼镜,身体不胖不瘦,很是得体。 我去了没几天,就注意到他。别人歇晌,他蹲在田埂边上看稻叶子,一看就是老半天。有回我凑过去,他指着叶子上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纹说:“场长,你看,这是病,得趁早治。”我说你懂这个?他推推眼镜,点点头,又摇摇头,不再多说。 后来我才从别人零碎的闲话里拼凑出来,他以前是省里农校的老师,专门研究种子的。不知怎么就成了右派。他话极少,除了必要应答,几乎不开口。傍晚收工,别人聚在窝棚前抽烟扯闲篇,他总是一个人走到农场最西头那片荒废的洼地边,站着看,有时蹲下抓把土。 有一天黄昏,我溜达过去。他正用树枝在地上划拉什么,见我来了,有点慌,想用脚抹掉。我说:“画啥呢?给我瞧瞧。”他犹豫了一下,指着那片洼地:“这场长,这片地要是拾掇出来,引后山水渠的水,能当一块好试验田。土质我看了,不一样。”风从田埂上卷过去,吹得他洗得发白的褂子贴在身上。我问他:“你想试啥?”他眼睛在镜片后亮了一下,又黯下去:“没……没啥,就瞎想。” 我心里动了动。过了几天,我跟公社打了报告,说想把西头洼地整出来增产。批了。我把这事交给他牵头,他愣了好一会儿,才憋出一句:“谢谢场长。”从此他整个人像被点着了,带着几个肯干的人,没日没夜地泡在那片地里。整地、修渠、下肥,他一边干,一边在小本子上记。夜里我查岗,总看见他那间小土屋的窗户亮着煤油灯的光,人影映在窗纸上,久久不动。 那年夏天,旱得厉害。试验田的秧苗刚抽穗,最要水的时候,水渠却断了流。他急得嘴角起泡,带着人连夜去查,发现是上游一段沟渠被塌方的土石堵死了。他二话不说,第一个跳进齐腰深的泥水里挖。那一夜,他们硬是用手和铁锹,把水道给抢通了。天亮时,他一身泥水回来,脸色白得吓人,却咧着嘴笑:“水通了,苗保住了。” 秋天,试验田的收成格外好,谷穗沉甸甸的。打谷那天,他捧着金黄的稻谷,手有点抖。他挑出一把最饱满的,小心地装进一个布袋里,递给我:“场长,这个……您留着。” 没多久,平反的通知下来了。他走的那天清晨,雾很大。他把那个装稻种的布袋子,又仔细塞进我的手里。“这品种,耐旱,”他说,“叫它‘洼地金’吧。”我送他到农场路口,雾渐渐散了,他的背影在土路尽头越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 后来,农场里一直种着“洼地金”。每当有人问起这名字的来历,我就指指西头那片如今已郁郁葱葱的田地:“一个戴眼镜的先生给取的。”
猜你喜欢
一眨眼20多年就这么过去了。
2026-01-22
老蒋聊商业
小子悟性不错啊,才130块就理解了
2026-01-22
房厂评科技长
袖侧的文笔真的特别好,如果不是三观炸裂的话我一定会喜欢她的文
2026-01-21
高轩谈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