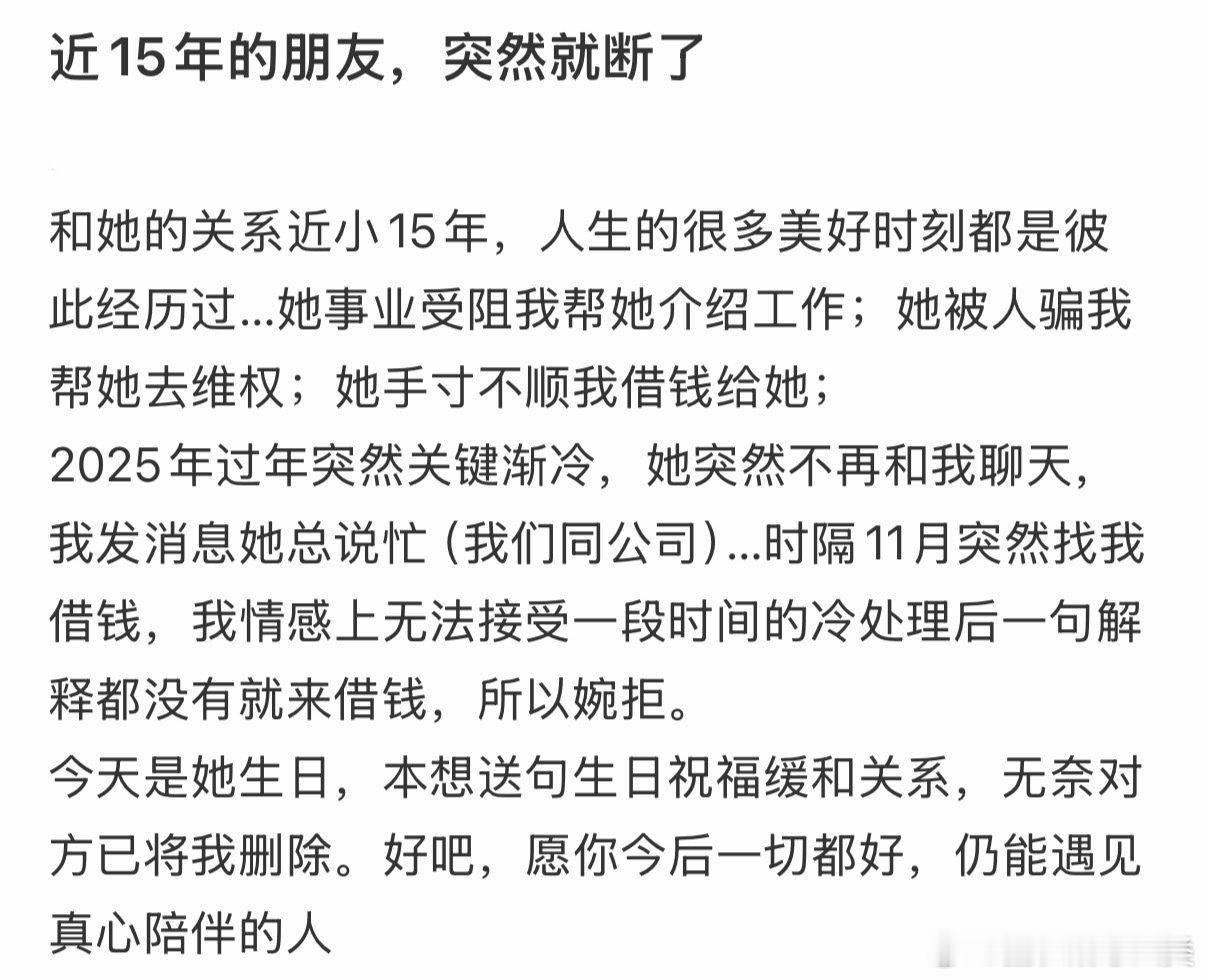1941年,山西盂县的一个小山村,18岁的侯冬娥正忙着给地里干活的家人准备午饭,村口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 铁锅里的玉米糊糊噗噗响着,侯冬娥撂下勺子就往院门口冲。土墙外,人影乱晃,哭喊声和日本话混在一起,越来越近。她回头看了眼灶台,火还没熄,烟囱冒着细细的烟。 她本来该往村后山洞跑的,可脚却钉在地上。隔壁刘奶奶家静悄悄的——刘奶奶瘫在炕上大半年了,儿子前几天刚被拉去修炮楼。枪声这会儿已经到了巷子口。 侯冬娥咬了咬嘴唇,扭头就冲进了刘奶奶家。屋里黑乎乎的,刘奶奶正撑着身子想往炕下挪,见着她,眼泪就下来了:“娥子,你快跑,别管我……” “别说话!”侯冬娥瘦,力气却不小,连拖带拽地把老人弄下炕,搀着她往自家后院挪。后院墙角堆着高高的玉米秆,她扒开一个窟窿,把刘奶奶塞进去,又飞快地把秆子复原。刚弄完,前院门就被踹开了。 两个日本兵端着枪进来,刺刀明晃晃的。侯冬娥站在院子当中,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你的,看见八路没有?”一个兵问。 侯冬娥摇摇头,指指灶房:“做饭呢,太君。”她心跳得像打鼓,脸上却木木的。另一个兵用刺刀挑开屋门帘,往里瞅了瞅。炕上被子凌乱,灶台的火还温着,案板上放着半个没切完的南瓜。屋里确实不像藏人的样子。 日本兵又转到后院,刺刀在玉米秆堆里捅了两下。侯冬娥觉得嗓子眼发干。就在刀尖快要捅到深处时,村东头突然传来爆炸声,两个兵对视一眼,骂咧咧地转身跑了。 侯冬娥腿一软,扶着水缸才站稳。等脚步声彻底消失,她才跑到玉米秆堆前,轻轻扒开秆子。刘奶奶蜷在里面,脸煞白,手里紧紧攥着个小布包。 “没事了,奶奶。”侯冬娥把她扶出来,发现那布包是个褪了色的荷包,里面装着几张发黄的纸,隐约能看见“地契”两个字。刘奶奶把荷包按在侯冬娥手里,手抖得厉害:“娥子,这个……这个你替我收着。我要是没了,你交给我儿……” 侯冬娥没接,她把荷包仔细塞回刘奶奶怀里,搀着老人往屋里走:“您好好活着,自己交给儿子。”灶上的玉米糊糊已经糊了底,她刮了刮锅,盛出两碗稠的。 那天傍晚,侯冬娥的父母从山里回来,听说村里被抓走了三个人。刘奶奶的儿子后来逃了回来,看见老娘完好无损,这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蹲在侯冬娥家院门口哭了一场。 很多年后,侯冬娥还记得那锅糊了的玉米糊,记得刘奶奶塞过来的荷包。她说那天自己根本没想太多,就是觉得,不能让一个动不了的老人在自家炕上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