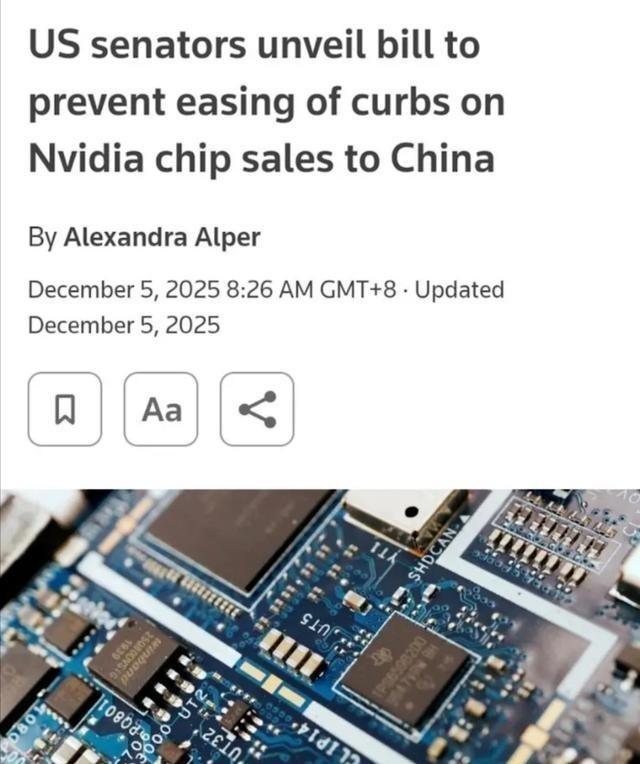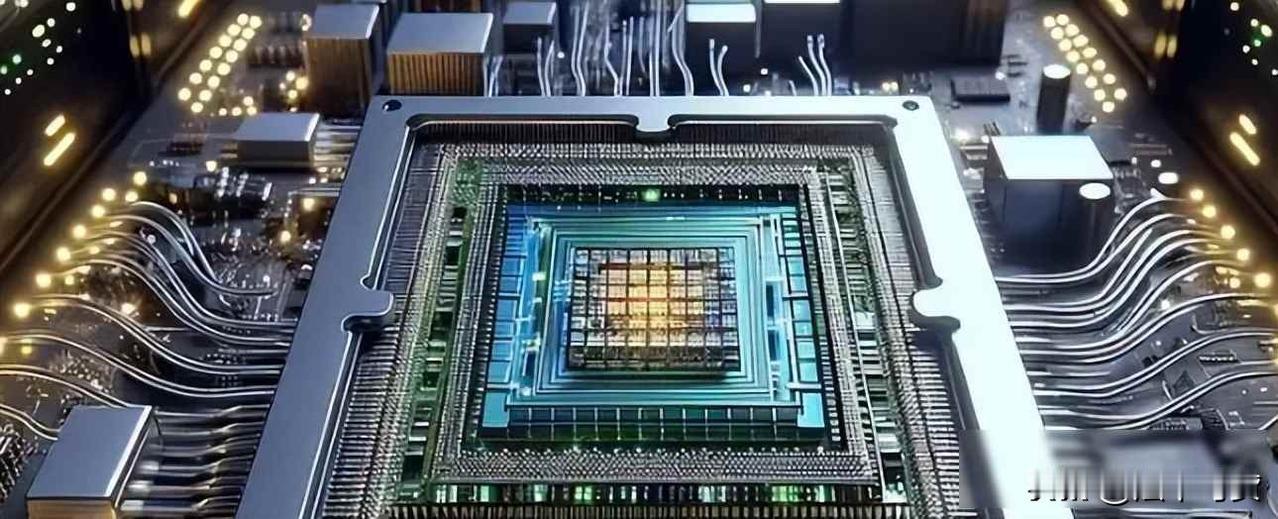“当时台下鸦雀无声,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全世界没人想要它,一张订单都没有——除了埃隆。”
2016年,硅谷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礼物交换”悄然发生。
黄仁勋将世界上第一台AI超级计算机DGX-1亲手交给埃隆·马斯克,这台定价30万美元的设备后来成为OpenAI早期研究的算力基石。
九年后,同样的算力被压缩进一本精装书大小的机箱,价格降至4000美元。
而黄仁勋领导的英伟达,已从一家几次濒临倒闭的图形芯片公司,蜕变为全球AI竞赛中最核心的基础设施供应商,此前更是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成为半导体行业的现象级存在。
在最近的一期访谈中,这位硅谷任期最长的CEO罕见地袒露了内心:“驱动我的,与其说是对成功的渴望,不如说是对失败的恐惧。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公司离倒闭不远了。”
第一次濒死:技术路线全错后的绝地求生1995年的英伟达站在悬崖边缘。这家创立仅两年的公司面临一个残酷现实:他们的三个核心技术选择全部错误。
在3D图形芯片的早期战场上,行业正朝着“三角形渲染、反向纹理映射、Z缓冲器”的技术范式收敛,而英伟达却押注在“曲面、正向纹理映射、无Z缓冲器”的替代路径上。
更致命的是竞争格局。当时硅谷涌现出超过100家图形芯片初创公司,包括后来著名的3DFX、Rendition等,而英伟达作为最早入场的玩家之一,却发现自己选择了最不可能成功的路线。
“我们三个主要技术选择全都选错了。”黄仁勋回忆这段经历时依然清晰,“我们是第一批起步的公司,却发现自己早已落后,并且选了错误的答案。”
公司内部爆发激烈争论:是立即转向主流技术成为市场最后一名,还是继续在错误路径上寻找突围机会?抑或是彻底转型做其他产品?
黄仁勋当时的决策展现了其独特的战略思维:“我们虽然不知道正确的战略是什么,但我们非常清楚什么是错误的技术。那就让我们先停止在错误的方向上努力,这样才有机会去找到正确的战略。”
这一“先破后立”的思路后来成为英伟达危机应对的模板——承认错误不是弱点,而是重新寻找正确方向的前提。
真正的生死考验来自与世嘉的合作。英伟达已花费大量资金为世嘉开发游戏主机芯片,但黄仁勋逐渐意识到,依照现有技术路线,最终产品很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他做出了一个违背商业直觉的决定:向世嘉CEO坦白真相。
“我告诉他,首先,我们承诺给您的技术是行不通的。其次,我们不应该继续履行这份合同,因为那只会浪费掉您所有的钱。第三,我请求您允许我们中止合同,但我仍然需要您支付合同尾款,因为如果您不支付这笔钱,我们公司会立刻倒闭。”
这位33岁的创始人甚至更进一步,请求世嘉将500万美元合同尾款转为对英伟达的投资——尽管从任何财务模型看,这笔投资收回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他做出这个决定,仅仅是因为觉得我这个年轻人还不错。”黄仁勋坦言。
这一决定不仅让英伟达获得了救命资金,更在日后被视为科技史上最具远见的“种子投资”之一。
第二次危机:无测试投产改写行业规则当英伟达终于确定正确技术方向,开发出Riva 128芯片时,公司陷入了更深的财务困境。
传统芯片开发流程需要经过设计、流片、测试、修正、再流片的多次循环,每次流片成本高达数十万美元,耗时数月。英伟达的现金储备根本无法支撑这样的试错循环。
黄仁勋发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芯片模拟技术。一家名为Icus的公司开发了一台能够模拟芯片功能的机器,可以在流片前虚拟测试设计。然而这家公司已经倒闭,只剩最后一台库存设备。
英伟达用银行账户里一半的资金——约50万美元——买下这台“孤品”。
更大的赌博在后面。基于模拟测试的信心,黄仁勋要求台积电在未见到实体芯片样品的情况下直接投产。
“历史上没有哪家公司的芯片能一次流片就成功,更没有人会在没见到样品之前就直接投产。”
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最终决定支持这位年轻人的疯狂请求,承担了芯片可能完全失败的全部风险。
这次豪赌成功了。Riva 128芯片一次流片成功,性能远超竞争对手,英伟达不仅活了下来,更成为当时从零到十亿美元增长最快的科技公司。
“我们为了拯救公司而开发的这套方法论,如今已被全世界采用。”黄仁勋不无自豪地说。
这场危机催生的“模拟验证+一次流片”模式,最终演变为现代芯片设计的标准流程,极大缩短了芯片开发周期。
第三次低谷:CUDA与十年黑暗中的坚持
2006年,当黄仁勋在发布会上展示CUDA(统一计算设备架构)时,迎接他的是全场的沉默。
这项让GPU能够执行通用计算任务的技术,在当时看来既昂贵又无用。芯片成本因此翻倍,而市场需求为零。英伟达股价从约120亿美元市值暴跌至二三十亿。
“我把一切都搞砸了。”黄仁勋回忆那段时期,“但我们问自己:我们到底信不信?如果我们的信念是建立在第一性原理之上,而不是道听途说,那我们就该全力以赴。”
CUDA的核心洞见在于:图形处理所需的并行计算能力,恰好也是科学计算和数据处理所需要的。GPU中成千上万个小型处理核心,比CPU更适合处理大规模并行任务。
但在AI革命爆发前,这一洞察显得过于超前。英伟达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持续投入研发CUDA生态,尽管市场反应冷淡。
转机来自2012年多伦多大学的一项突破。研究人员利用两块英伟达GTX 580显卡训练出AlexNet神经网络,在ImageNet图像识别竞赛中以远超传统方法的准确率获胜。
“这不仅仅用于计算机视觉。”黄仁勋团队立即意识到,“深度学习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所有有趣的问题,只要我们有输入和输出数据。”
CUDA架构突然成为深度学习研究的理想平台。黄仁勋将这次机遇比作《星际迷航》中的“第一次接触”:
“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个瞬间——那个短暂闪现的火花,谁知道未来会怎样。”
AI 竞赛的本质:一场没有终点线的马拉松访谈中,被问及AI竞赛的终点时,黄仁勋给出了令人深思的回答:“我想,没人真正知道答案。”
在他看来,AI发展将呈现渐进式特征,而非突然的“奇点”突破。
“当AI性能再提升一千倍时,其中大部分算力将被用于更多的反思、更多的研究,以及对答案更深层次的思考。”黄仁勋解释,技术进步的轨迹并非单一维度的能力扩张,而是能力增长与安全边界同步扩展的双重过程。
他以汽车发展类比道:“今天控制汽车牵引力的电脑,比当年阿波罗11号登月用的电脑还要强大。很多动力都用在了提升操控性上。”
同样,AI计算能力的提升将主要用于增强可靠性、准确性和安全性。
对于普遍存在的AI安全担忧,黄仁勋借用了网络安全领域的经验。“一旦某个系统被攻破,这些信息都会被所有人共享,相应的补丁也会共享给所有人。”这种威胁情报共享机制形成了有效的集体防御。
“人工智能领域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我认为我们都必须做出决定,共同努力以规避风险,这是我们最好的防御机会。”在黄仁勋看来,开放协作的防御生态比封闭的单点防御更具韧性。
能源瓶颈的突破:分布式发电与效率革命AI 算力增长的物理极限在哪里?
黄仁勋指向能源约束。“没有能源增长,就没有工业增长;没有工业增长,就没有就业增长。”
他预测未来六七年将出现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的普及,这些反应堆可能直接建在数据中心园区内。“我们都将成为发电商,你可以按需建设,减轻电网负担。”
但更根本的解决方案来自计算效率的革命。黄仁勋指出两个关键趋势:摩尔定律带来的计算成本指数下降,以及英伟达加速计算架构带来的性能跃迁。
“仅在过去十年,我们就将计算性能提高了一百万倍。”黄仁勋将这种超越摩尔定律的进步称为“英伟达定律”,“十年之内,人工智能对大多数人而言,其能耗将变得微不足道。”
这一预测基于双重优化:芯片能效的持续提升,以及算法效率的指数级改进。当AI推理可以在手机端高效运行时,集中式大规模计算的需求将部分转移至边缘设备。
脆弱领导力:恐惧如何驱动持续创新“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公司离倒闭不远了。”
黄仁勋坦言,这种生存焦虑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对失败的恐惧,远比贪婪或其他任何东西更能驱动我。”
这种危机意识驱动的管理哲学塑造了英伟达独特的组织文化。在黄仁勋看来,领导者的适当脆弱性非但不是弱点,反而成为组织学习与适应的催化剂。
“作为领导者,展现脆弱和维持领导力并不矛盾。公司不需要一个永远正确、对自己的想法和决策百分百确信的天才。”
他解释,当领导者承认自身局限和不确定性时,团队更愿意提出不同意见,组织能够更灵活地调整方向。
“调整的前提,是承认自己可能犯错。”
黄仁勋将这种状态描述为“有益的挫败感”——一种推动持续改进和创新的心理动力。
在这种文化下,英伟达形成了快速试错、快速学习的能力,这在技术快速迭代的AI领域成为关键竞争优势。
移民的韧性:从肯塔基寄宿学校到硅谷之巅
黄仁勋9岁时,父母将他与哥哥从泰国送到美国肯塔基州一所寄宿学校——奥尼达浸信会学院,那里当时是美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我九岁,负责打扫一百个男孩宿舍的厕所。”在这所资源匮乏的学校,学生们需要从事各种劳动来维持学校运转。
每月一次,兄弟俩通过录音带与远在泰国的父母交流。“我们会把录音带邮寄给父母。他们听完后,会在上面录下他们想说的话,再寄回来。”这种延迟的亲情连接持续了整整两年。
这段经历锻造了黄仁勋的韧性,也塑造了他对美国梦的理解。
“我是移民。我的父母抛弃了一切,只带着几个行李箱和口袋里的一点钱就来到了美国。而我,就是美国梦的第一代亲历者。”
多年后,当黄仁勋在硅谷建立起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他依然保持着每天清晨4点起床工作的习惯,依然感受着“公司离倒闭不远了”的生存焦虑。
这种移民的忧患意识与奋斗精神,或许正是英伟达文化中最底层的代码。
工作的重新定义:当AI成为能力放大器而非替代者面对AI可能取代人类工作的普遍担忧,黄仁勋提出了一个更有深度的视角:技术变革本质上是工作内容的重新定义,而非简单的岗位替代。
他以放射科医生为例进行说明。五年前,深度学习先驱杰弗里·辛顿曾预测AI将在五年内取代放射科医生。
现实是,AI确实极大改变了放射学工作流程,但放射科医生的数量却不降反增。
“原因在于,放射科医生的终极目标是诊断疾病,而不仅仅是阅片。阅片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其中一个环节。”AI承担了初步的图像分析任务,让医生能够专注于更复杂的诊断决策,同时处理更多病例。
黄仁勋认为,这一模式将在许多专业领域重现。“你必须回归到工作的根本目的去思考。律师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根本目的改变了吗?”
在他看来,AI 的真正价值在于放大人类的专业能力,而非简单替代。
就像计算机没有让数学家失业,而是让他们能够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就像CAD软件没有让建筑师失业,而是让他们能够设计更精妙的建筑。
“如果你的工作就只是切菜,那么一台料理机就能取代你。你的工作价值必须超越任务本身。”
结语硅谷的发展史上,从不缺少技术前瞻与商业现实错位的案例。
而黄仁勋执掌下的英伟达,它成功穿越了从图形处理到通用计算,再到人工智能计算这两次深刻的产业范式迁移,而每一次跨越都曾伴随公司濒临绝境的危机。
访谈最后,黄仁勋道出了创新的残酷真相:“许多成功都源于极其艰苦的奋斗。其间伴随着漫长的痛苦、孤独、迷茫、恐惧、尴尬和羞辱——所有我们最不愿体验的情感。”
或许正是这种对失败的深切恐惧与对生存的极致渴望,才让黄仁勋,在三十年里始终保持着对技术趋势的敏锐嗅觉,在每次计算革命的前夜完成关键布局。
这对每一位面临不确定性决策的企业掌舵人而言,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管理哲学:
真正的战略定力,不在于永远正确,而在于拥有从错误中快速修正并发现新方向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