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人类学家》作者:奈吉尔•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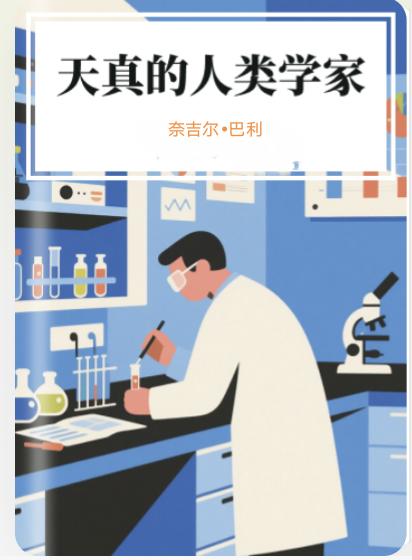
今天我们要讲一部非常有意思的书,书名叫作《天真的人类学家》。
听到书名,可能有人会问:什么是人类学家?他们是干什么的呢?
顾名思义,人类学家就是研究人类的学者,但他们研究的并不是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而是那些住在深山老林或者孤岛上,仍保留着很多民族传统的原始部落族群。
那人类学为什么要研究这些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族群呢?这并非为了猎奇,而是通过研究这类与现代工业文明差异显著的文化模式,了解人类早期的生存状态,并以之为镜,照见我们已经步入工业文明的人类的来时路,寻找我们的文化之根。
那么,人类学家是怎么展开研究工作的呢?其中最神秘的一种工作方法就叫田野调查,英文叫fieldwork,据说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第一次发明并践行的。卢梭在写《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时,为了体验原始人的生活,特地去乡下隐居了一段时间。此后的人类学家都要向他学习,去乡野(field)里做他们的调查工作(work)。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就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于1977年到1979年,在非洲的原始部落多瓦悠兰进行乡野工作时的笔记。但因为这趟研究之旅过于曲折,因此被戏称为西非版的“人在囧途”,并以英国人特有的幽默和自嘲文风,这本书也被列入了读者们的“快乐书单”“治愈系名单”。
奈吉尔·巴利,1947 年出生于英国,在牛津大学获得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大英博物馆人类博物馆馆长,因为《天真的人类学家》一书而成功“破圈”,在读者间获得巨大反响,被誉为“人类学界的卓别林”。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这位人类学家中的喜剧大师,开启这趟西非版的“人在囧途”。
踏入古老神秘的多瓦悠兰
巴利拿到博士学位后,曾在高校里任教。在这个很小众的专业中,田野调查是最核心的研究手段之一,而且学界精英们已经达成共识,只有有过田野调查经验,才能在学术界站稳脚跟,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说自己是一位人类学家。
为学术前程着想,巴利也想申请类似的项目,但该去哪里调查呢?一开始他想去东南亚的东帝汶,不巧当地发生了暴乱,无法保障白人的人身安全。接着他把目光投向非洲的一处海岛,但当地实施独裁统治,签证审查非常苛刻,很难通过。
这时有位同事提醒说,在西非的喀麦隆有个被忽略的山地部落,叫多瓦悠兰。巴利查看文献,发现资料并不多,但提到那里有头颅崇拜、割礼等民俗,且以野蛮而闻名,看起来有些研究意义。就这样他像个弹球机里的球,被弹向了多瓦悠兰。
巴利先搭乘飞机抵达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一下飞机,他就感受到湿热的雨滴迎面而来,空气中融合着麝香、热气、芬芳与粗野的味道。刚出海关,他就看到有双手伸过来,抓起了他的箱子。巴利愣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遇到了小偷。他紧追不放,成功地救下了自己的箱子,鼻梁上却挨了小偷重重的一拳,涕泪交加。
巴利花了比正常价高四倍的价格,才打上了出租车。他在街道上闲逛,意识到在小商贩眼里,自己就是个天真的白痴。他们开出的价格往往是合理价的20倍,巴利骂他们是土匪,他们咯咯笑着表示同意,然后跟他以正常价格的五倍成交。
为了拿到居留许可证,巴利跟有关部门进行了一番痛苦且冗长的交涉。接着他乘坐火车前往下一站,北方城市恩冈代雷。列车时刻表说这段旅程只需要3个小时,但巴利在嘈杂闷热的火车上足足待了17个小时,才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之后巴利买了一辆老爷车,开到波利小镇。他要调查的目的地,就在距镇子九英里之外的孔里村。因为不懂当地语言,巴利需要找个助理。镇上的牧师连夜召来了他的12个兄弟,巴利选中了马修,一个会读写法语,但烧菜很糟的土著男孩。
巴利带着马修来到了孔里,村民们诚惶诚恐地把这位白人“先生”让进酋长的庭院。一个赤裸上身的女人跪在门口迎接,前后摇晃着身子,用当地土语低吟着欢迎词。有人搬来把折叠椅,让巴利堂而皇之地孤坐在庭院中央,其他人远远躲开。
院落里静得令人窒息,巴利觉得自己有义务说点什么。他大喊道:“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领!”马修如实翻译,村民们说酋长还在田里,马上回来。很快酋长来了,他叫祖帝保,四十出头的年纪,有点发福,身着华丽的长袍,腰间配剑,戴着太阳镜。巴利敢打赌他肯定不是从田里赶来的,因为没有人耕田时会穿得如此体面。
之后巴利住进了孔里村,开始学习当地语言。他先学的是问候语,就像我们平日里经常说的“吃过了吗?”“吃过了”一样,多瓦悠人也有自己的问候语,叫:“今日,你的天空可晴朗?”“非常晴朗,你呢?”“我的天空也很晴朗。”熟能生巧,巴利很快就会问候了。
但在其它口语学习上,巴利的进展颇为不顺。这是因为多瓦悠语和大多数欧洲语言不同,它是一种音调语言,就是说一个字的音调高低可以完全改变字义;而且当地人还将音串连,形成了滑音,一个字的音调会受到相邻字的影响,很难学。
所以两个星期过去了,巴利还是这门语言的门外汉。而本地人对自己的母语评价极低,认为只比动物鸣叫高明一点点,因此他们不懂为什么有人学不会。他们问马修:“这个白人都来这么久了,怎么还是不会说我们的话?”
还有一次,有个小女孩指着巴利哭闹说:“我要看他脱下皮肤!”马修尴尬地解释说,村民们觉得来部落的白人都是多瓦悠巫师转世,白皮肤只是掩饰,底下的皮肤是黑色的。所以有的村民怀疑,巴利这个转世巫师是在假装自己听不懂本地话。
还有村民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曾亲眼看到巴利晚上睡觉前,把脱下来的白皮肤挂在了墙上。还有人八卦,说巴利和教会的白人神父晚上见面时,会锁上房门、拉上窗帘,然后一起脱下皮肤欢聚。讲到这些谣言,马修嗤之以鼻,但骨碌碌乱转的眼睛出卖了他。他的眼神在巴利身上瞟来瞟去,深恐主人会当场变成黑色。
因为一开始分不清音调,巴利闹出了很多笑话。一次他去拜访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巫师,临行前他礼貌地跟主人握手,并解释道:“对不起,我要回家煮肉去了!”结果因音调错误,主人听到的却是:“对不起,我要去和铁匠的老婆亲密了。”这让巴利哭笑不得。
不过,很快巴利就找到了更有效的学习方法。他用录音机把村民们的访谈内容录下来,一边听一边用英文、法文和拼音音调在笔记本上作注释,形成了一部多瓦悠字典。他的方言讲得越来越好,赢得了当地人的接纳,被亲切地称为“我们的白人”。
时刻遭遇困境,时刻不确定
巴利在多瓦悠兰待了一年多,整整瘦了36斤,主要是吃得不习惯。多瓦悠人主食吃小米,搭配一种野生植物提炼的胶状酸酱。几顿下来巴利就受不了了,味同嚼蜡,只能吃点燕麦、饼干,搭配巧克力、花生酱、马铃薯泥罐头和罐装牛奶。
对于当地的其它美食,巴利也无福消受。当地人爱吃山羊肉,尤其是炒得油乎乎的公山羊内脏,但他只觉得骚臭难闻;当地人爱啃食一种扇椰子,巴利的门牙受过伤啃不动,有人端给他一盘松软的,竟然是人家好心地帮他嚼了一遍;他喝到了美味的鲜奶,别人却告诉他为了防止牛奶凝结,挤奶的人会往桶里撒尿……
当地人为了消解田中劳作的乏味,会用小米酿酒,举行大型酒宴。巴利也参加了,但见这种啤酒浓稠似豌豆汤,怪味像煤油。当地村民为了表示对这位贵客的尊重,特地叫来一只秃毛狗把酒瓢舔干净,这才添满啤酒递过来,看他一大口喝下去。
幸好当地人养鸡,这让巴利燃起了新的希望,自己可以作美味的英式炒蛋。但在多瓦悠部落,鸡蛋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孵小鸡的,用本地人的话说:“你难道不知道鸡蛋是从哪里掉出来的吗?”语气中充满了对鸡蛋浓浓的嫌弃。
不过巴利还是想办法搞到了几颗鸡蛋,但因为已经在酷热中暴晒了好多天,里面已经变成了蓝绿色,散发着可怕的臭味。巴利干脆自己买了些小鸡,精心饲养,终于等到母鸡下蛋了,马修却把那些鸡杀掉了,理由是下蛋会让它们的精力流失!
因为营养不良再加上水土不服,巴利患上了疟疾。在镇上教堂养病期间,上吐下泻、高烧不退的他还饱受蝙蝠的侵扰。这些怪物从天花板的洞穴里飞下,撞到墙上后又落在他脸上。牧师建议他用网球拍迎战满屋蝙蝠,可尽显毁天灭地之效果。
还有一次,巴利开的“老爷车”竟因转向轴失灵,冲下悬崖,幸好被崖底一棵大树托住。他一头撞在方向盘上,门牙受伤,发炎化脓。他去城里看病,刚走进牙科诊室就被一个穿白大褂的大块头按在手术椅上,直接拔下那两颗摇摇欲坠的大门牙。
然后大块头就开始开单子,说诊疗已结束,去护士台付钱。巴利惊呆了,只见鲜血从嘴里涌出,染红了胸前的衬衫。他口齿不清地辩解说自己需要进一步的治疗。但大块头却说,巴利要是再吵下去,自己就要叫真正的牙医来了。原来这人是个技工,也是个钟表匠。
巴利终于等来了真正的牙医。又是经过一番艰难谈判后,对方终于答应给他做套塑料假牙。牙医还说巴利作为“高贵的病人”,配得上打针麻醉剂,便往他的牙床上打了一针。拔完牙后才打麻药,这实在很怪,但是巴利已经痛到毫不在乎了。
趁着做假牙的空当儿,巴利来到街上溜达,门牙漏风、嘴巴发麻,脸颊青肿如狼人,衬衫沾血如刚逃离凶案现场。面对警察的盘问,他只能含糊不清作答。回到诊室,牙医在他的牙床上安了两个摇摇晃晃的小塑料片,收费超过法定标准十倍。
更悲催的是,因为打麻醉剂的针头没有消毒,巴利患上了病毒性肝炎。初步治疗后,医生建议他补充维生素,于是他决定种点蔬菜。但多瓦悠人认为种地是卑贱之事,巴利不得不雇了个园丁,但对方拒绝事先商定工钱,而是等收获后让巴利评估自己的工作再决定支付金额。这是一种谈判技巧,迫使雇主多出钱。
巴利给了他番茄、小黄瓜、洋葱、莴苣、红萝卜等菜籽,让他每样都种一点。几个月后,园丁告诉他可以收获了。虽然有些菜被蝗虫吃了,有些被牛羊踩坏了,但莴笋获得了大丰收,足足有三千颗。巴利吃惊地说不出话来,他一个人怎么吃得了这么多的莴笋呢?于是,他拿着莴笋四处送人,并赢得了“莴笋大王”的美誉。
最后巴利和园丁因为工钱起了争执。巴利说自己只想开辟一小块菜园子,吃各种蔬菜补充营养,自己的目的显然没达到,因此只能支付5000中非法郎,自己吃不完的莴笋园丁可以拿到城里卖;但园丁要巴利支付两万法郎工钱,毫不让步。
最后双方闹上了村落法庭,经过激烈争辩后,祖帝保酋长裁定巴利支付一万法郎。巴利没有二话;有趣的是园丁虽然接受了这一结果,却说为了表示感激巴利的慷慨,自己只要五千法郎就够了。就这样双方都保住了自己的尊严,皆大欢喜。
我们再说回巴利那两颗假牙,因为安得不牢靠,很容易在吃饭或聊天时飞出去,于是他去大城市里“巩固”了一下。不幸的是,后来因为吃香蕉这两颗假牙被折断了,这次巴利自己用烤箱、电吹风和树脂就把假牙粘回去了。这次“手术”效果很好,唯一的后遗症就是假牙很快变绿了,他一张嘴就露出如莴笋般翠绿的微笑。
重返多瓦悠兰,却无功而返
尽管遭遇了重重困境,但巴利还是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田野调查项目。就像玩拼图一样,他慢慢地把多瓦悠兰的头颅崇拜、祈雨仪式、丰收祭等嵌入拼图,梳理出这一部落独有的生死观、繁育观。但整幅拼图还缺最后一块,那就是割礼仪式。
在多瓦悠兰,年分为阴年和阳年,割礼仪式只能在阳年进行。巴利第一次来刚好赶上了阴年,他的研究签证也不允许他待更久,因此他只能带着遗憾返程。但回国后不久当地朋友就通知他,说一个月后孔里要举行割礼仪式。
朋友说祈雨酋长已经占卜过了,结果是上上吉。占卜方式是由祈雨酋长把葫芦装满特殊的药草,然后放在祈雨石旁边的河流里,一段时间后再查看这个葫芦的状况。这次这个葫芦毫发无伤地漂到了山谷,这是个好兆头,可以举行重大的仪式。
巴利顾不上申请科研许可,直接办了个旅游签证,赶在旱季结束前返回多瓦悠兰。这是因为按照当地的传统,仪式要在雨季第一场大雨降落时举行,然后被割礼的男孩会离开村落入丛林生活,直到九个月后伤口痊愈返回,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马修还找来了两个割礼打扮的男孩,巴利送给他们几条豹纹图案的装饰彩带,替他们装扮上,看他们跳舞。这是多瓦悠人特有的缔约仪式,意味着巴利成为他们的“丈夫”,等他死后这两个“老婆”要在他的葬礼上跳舞,送他的灵魂归天。
在等待割礼仪式举行前,巴利偶尔会去镇上,找朋友喝喝酒,聊聊天,听听新闻,感受这个“世外桃源”之外的变化。一天傍晚,他跟朋友在酒吧喝酒时,一只野猴子不知从哪里蹿了进来,双手绕住巴利的脖子,坐在了他的大腿上。
巴利想要甩开,换来的是猴子一顿狂暴的吼叫。原本巴利计划晚上去看电影,现在甩不脱这只猴子,怎么办呢?朋友建议他把猴子藏在身上,用外套挡着顺进去。结果在售票口排队买票时,猴子睡着了,很多人奇怪地看向他鼾声作响的肚皮。令人失望的是,售票小姐发现了猴子,巴利只好掏钱给它买了张儿童票。但电影屏幕刚亮起来,这只猴子就醒了,探出头来,瞄上了后排一只红色手提包。它伸手去够,但包的主人拒绝放手,猴子怒不可遏地吱吱乱叫。
巴利赶紧叫住在影院里来回穿梭的小商贩,买了只红色芒果,给猴子玩。没想到猴子不感兴趣,还把芒果撕咬成一条条的,往观众身上喷吐。观众们也以牙还牙,撕咬芒果的果肉,对着猴子喷吐。可怜的巴利,也成了这场大战的受害者。
无奈之下,巴利只好丢下朋友,带着猴子先行逃离。他刚走进宾馆大门,猴子就从他身上矫捷地跳下来,摇晃着穿过庭院,荡到树上,然后不知所踪。那天晚上,巴利没有睡好,并不是因为兴奋,而是因为床上出现了虱子,来自那只猴子。
雨季的第一场雨终于来了,但多瓦悠的割礼仪式并没有按计划举行。巴利找到两位“老婆”,只见男孩们满脸的不开心,蹲在树下发呆。他们的衣服上满是污渍,原本帅气竖立、羽状散开的马尾装饰变得湿哒哒的,豹纹装饰也脏得一塌糊涂。
巴利去找祈雨酋长探求真相。老人叹着气摇头,说出了一个就连马修都不知道怎么翻译的术语。看到两人茫然不解的样子,老人把他们拉到田中,只见一群黑色的、肥胖的毛毛虫趴在小米植株上,正在疯狂地啃食嫩叶,把整块稻田都淹没了。
巴利明白了:因为这场黑色的毛毛虫瘟疫,孔里今年注定不会有小米收成;因为没有收成,村民们就没法酿造小米啤酒;因为没有仪式所需的啤酒,割礼仪式就注定无法举行;没有这场仪式,男孩们就无法成长为男人,多瓦悠兰注定要蒙羞。
变化就在一夜之间发生,那些割礼男孩悄悄地摘掉了马尾装饰,撕下了身上的豹纹饰带。巴利的两个“老婆”也开始躲着他,极力避免和他见面,因为割礼仪式没有完成,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位“丈夫”:亲昵还是尊重,抑或如面对陌生人?
而且正如祈雨酋长所言,这场毛毛虫瘟疫只是开始,恶兆往往会结伴而来,引来更多的恶兆。很快恶兆席卷多瓦悠兰,牛儿失足跌落井里,老鼠出现在谷仓里,山路上出现一群红色昆虫……村民们变得越发的不安,且日益沉默。
巴利意识到,自己该回去了。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离开,是否也会被村民们视为恶兆?但正像这个古老部落相信的那样,时间终究能解决所有的恶兆,只要耐心等待,只要熬过这段艰难,好兆头总会姗姗而来。
好,讲到这里,《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我们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尽管这是一本人类学调查,却被读者们当作“治愈类”读物,用以抚平自己的孤独、失落和抑郁。那为什么它能有这样的治愈效果呢?答案是因为“天真”。
或许很多人认为,“天真”是个贬义词,对应的是心智不成熟,就像巴利那样,容易上当受骗,容易被人占小便宜。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天真”更是一种心态,是历经世事磨砺后仍能保持心地单纯、性情真诚,是不虚伪、不做作、不世故。
“天真”是如蔚蓝天空、灿烂千阳般的晴朗,不带一丝阴云,不染一丝尘埃。或许只有这样的心态,才能让人感受到友好与真诚,才能穿越各种困境和不确定,保持初心、抵达彼岸。就像多瓦悠人每天的问候语:“今日,你的天空可晴朗?”晴朗的岂止是天气,更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一片“上下天光、春和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