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一个很小气的女人,她不允许我在八点后和别的小朋友一起出去玩,也不给我买喜欢的玩具,我讨厌小气的妈妈。
五岁的我气鼓鼓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这段话。
我的妈妈是一个很市井的女人,他会为了五毛钱在菜市场上和老板争论一个小时,即使我拉了她那么多次,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她也不肯让步,我讨厌市井的妈妈。
十二岁的我悄悄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这段话。
“诺诺,该吃饭了。”女人朝着房门的方向喊着,忙碌的身影倒映在窗上。
“知道了知道了,马上来。”我急忙把日记本放起来,往餐厅走去。
说是餐厅,把它叫做一个吃饭的地方更合适,一个刚好能坐下两个人的小房间里,放着一张破破旧旧的方桌,两个凳子摇摇晃晃,随着陈诺夹菜的动作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头顶上昏暗的灯光一闪一闪,看起来下一秒就要灭掉了,桌子上摆着一盘青菜和一盘红烧肉,与这个破败的房间格格不入。
“多吃点,你还在长身体呢。”女人絮絮叨叨地说着,边说边向女孩碗里夹菜。
“知道了知道了。”我不耐烦的拨弄着碗里的菜,回答道。
从我记事以来,就一直住在这个破旧的家里,不对,这并不能称之为一个“家”,它只是一个用铁皮搭建起来的铁盒子,是我的妈妈自己捡回来废旧的铁皮,一片一片搭建起来的。
我有一下没一下的戳着碗里的饭菜,没有丝毫胃口。
破旧泛黄的桌子,一只桌脚长,一只桌脚短,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凳子。都昭示了这个家庭生活的窘迫。
从我出生起,我那个赌鬼老爸就天天不着家,每天半夜醉醺醺的回来。本来在我出生前,我们家还能凭着他跑出租的收入,维持一个不错的生计。
但好景不长,在我出生后,一切都变了。他的那些“朋友”,在看到了我是个女孩后,幸灾乐祸地说道,他赚钱也没用,以后老了也没有个依靠。听人劝吃饱饭,他被说服了,从那以后,就再也不去工作,沉迷于赌博,享受当下。每次看到妈妈来催他,只会骂骂咧咧的让她滚开。
妈妈那时候只是个刚入社会的小女孩,从农村到城市打工,外公和外婆就给她十二块钱,让她自己出来闯荡。
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只怀揣着勇气和单纯的妈妈就这样在别人的介绍下,进了食堂打工,而爸爸每天中午跑出租,会固定在那里吃饭,就这样一来二去,他们看对了眼,也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没过多久,妈妈就怀上了我,爸爸上门议亲的时候被怒不可遏的外婆用扫帚打了出来,但没有人能阻止,生米已经煮成白饭了,在无人的祝福下,他们结了婚。

之后我出生了,我的出生好像是妈妈不幸的开始,原本完整的家一落千丈。
爸爸在外面赌博欠了很多钱,大冬天,妈妈抱着我被要债的堵在家门口,她看起来难堪又无措,要债人的声音吵到了附近的邻居们,知道一点实情的用怜悯的眼神看着妈妈,不知道实情的则不耐烦的看着。
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妈妈脸红的好像能滴下血来,她抱着尚在襁褓中的我,不停的道着歉,希望要债人能再宽限几天。要债人眼见着要不出钱,几个人冷哼一声,撞开妈妈闯进了当时的家里,妈妈紧紧的抱着我,看着他们把稍微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
眼见着这些人的动作,终于有人看不下眼出来说道:“大过年的积点德吧,你把东西都搬走了他们娘俩吃什么啊。”
听到那位大妈的话,妈妈的眼圈一下子就红起来了,她的声音变得哽咽,情绪在崩溃的边缘。
但那几个要债的人并没有管大妈的话,自顾自的搬着东西,终于,在这个家徒四壁的家里,只剩了我和母亲
妈妈站在房门口,看着汽车的飞驰而去,身后是空荡荡的房间,围观群众早早的离去,冷冽的风刮在她的脸上,她好像感受不到冷一样,直愣愣的站在门前,任由雪落在她的身上。
直到听到我的哭喊声,她才回过神来,焦急的轻拍着襁褓,试图哄好我,但她并不熟练的动作及恶劣的环境,我并没有停下哭喊,而是更加大声。
漂泊的大雪,婴儿的哭喊,重重的债务,像是大山一样压着她,彼时她也只是才二十岁。
从那以后,妈妈好像对爸爸死心了,再也不去棋牌室门口等他,也不劝他。而是自己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白天她就拜托邻居大妈照顾我,自己去食堂打工,晚上回家照顾我。
就这样,在她一份份微薄的收入中,我成长到了三岁,意外发生了。
本不会回家的爸爸不知道哪根搭错了,大半夜喝醉了回家,后面听别人说是好不容易赢了钱,一高兴就多喝了点,也有人说是想通了,想回归家庭了,总之关于这件事众说纷纭,现在也没办法知道了,真相只有他自己了解。
在经过小河旁的时候,他一个没站稳,一头栽了进去,就没能再出来。
随着他的离去,给母亲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痛苦与压力,他生前欠下的债全都得让母亲来还。母亲只能每天打三份工,一边养家一边还债。
我记得在父亲欠下的最后一笔债还清的那一天,母亲因常年劳作而弯曲的腰板好像都挺直了,空气里好像弥漫着轻松的意思,她愁苦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家里的饭菜也格外丰盛。彼时年幼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模糊的感受到这应该是不同寻常的一天。
母亲看着狼吞虎咽的我,慈爱的笑着。
我十五岁那年,母亲凭着自己的努力盖了一间破房子,这勉强可以称之为一个家了。而十五岁,正是青春懵懂的时候,同学们间家庭的阶级不同逐渐显露了出来。
我一直没有敏锐的感受到差距,直到当她们看到我正在捡破烂的母亲时露出的怜悯的眼神,我明白了我家庭条件的糟糕。
洗的发白的校服和校裤都昭示着我的窘迫。从那以后,除了在家里碰面,我尽力的避免与母亲的相见,即使碰到了,也会装作不认识。
母亲好像感受到了我的躲避,在家门外遇到我的时候会主动避让,即使无法避让也会低下头装作不认识。每次我看到母亲的动作,心里总会堵得慌,但和青春期的面子相比,这点情绪不值一提。
有一天,我回家早了点,看到了一个男人在家门口和母亲谈着天,那个男人戴着一顶毡帽,皮肤黝黑,看起来很老实,但我心里就是喜欢不上他。
看到我的那一刻,男人的眼神亮了起来,他好像想主动和我打招呼,正打算叫我的时候,我径直穿过他们,走进了房间。男人无措的双手插在了口袋里,眼神看起来很可怜。
晚上,果不其然,我在餐桌上看到了那个男人,他像白天一样讨好的对着我笑,想得到我的一些回应,但我在看到他的那一刻,本就不好的脸色阴沉了下来,让他想说的话梗在了喉口。

餐桌上。母亲向我介绍了那个男人,是对面摆摊的,白天卖早餐,晚上卖夜宵。他的厨艺很好,母亲一直在夸他。
本来应该很美味的食物,吃进嘴里好像泛着苦味,味同嚼蜡。
看着他俩在餐桌上的交谈,我的心中有股无名的怒火在燃烧。
母亲问道:“好吃吗?”
我看到了她眼中的小心翼翼,也看到了那个男人眼中的希冀。
但我并没有说出他们想听到的话,冷硬的吐出了:“难吃死了,我吃好了。”
说完了这句话,我就起身离开了餐桌,转身走向了自己的房间,嘭的一声把房门关上,再也没出去了。整个房间陷入了寂静。
我趴在床上,心里胡思乱想着,我的心里很明白,她今天把那个男人带回家的意思,但同时也意识到,我并不想要他们组成一个家庭。
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晚上的时候,母亲轻轻的敲开了我的门,问道:“诺诺,你睡了吗?”
回答她的是一片安静。
“我知道你没睡,妈妈只是想告诉你,我已经拒绝他了。你安心学习。”母亲疲惫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听到她的话,我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而是一种很复杂情绪在我的心中交织着。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个男人。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应该是母亲从十九岁以后唯一一天没有自己做饭。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母亲的忙碌使我疏于管教,在身边人的耳濡目染下,我越来越厌恶这个家庭,它给我带来的只有无尽的嘲笑和自卑。
我一定要逃离这个家,十七岁的我在日记上坚定的写下这句话。
十七岁,我凭自己的努力考进了一个不错的分数,想要逃离那个家的念头一直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所以我选了一个离那个家很远的学校。
我马上就要逃离这个家。十七岁的我在日记上高兴的写下这句话。
“上了大学也要好好读书啊,不能放松警惕啊,按时吃饭,好好睡觉……”在我临走前,母亲不停的唠叨着。
听厌了这些话,但一想到马上要离开这里,我敷衍的说道:“知道了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个小孩。”母亲看着我,认真的说,伸出手想要摸我的头,我下意识的躲开了她的触摸。她的手就尴尬的悬在半空中。
其实在躲开的那一刻,一种名为后悔的情绪就蔓延在我的身体里,但为了面子,我拉不下脸道歉,只能生硬的转移话题:“我要走了。”
“好好,慢点,路上当心点。”母亲放下了想触摸我的手,两只粗糙的手交叉在一起搓了搓,又不知道该摆在哪里。
她常年劳作的脸上劳作的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不停地对着我笑。
我看着她小心翼翼的样子,一股不知名的意味向我袭来。
就这样,她送我到了大巴站,坐在大巴车的座位上,透过窗户,我看到了母亲紧跟着我的眼神,她看起来还有话想要对我说。
她的嘴皮上下动了动,隔着玻璃,我听不到她在说什么,就把目光转向了前方,带上了耳机,隔绝了外界的所有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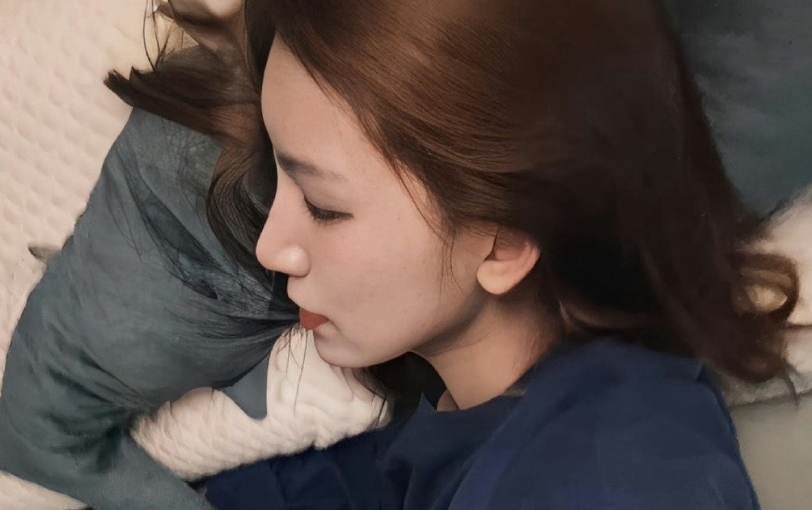
她看到我的样子,放弃了再说一遍,只是挥了挥手做告别,我也象征性的挥了挥,离开了那个我一直想逃离的家庭。
母亲想说什么,现在回想,应该是常回来看看吧。
上了大学,我逐渐忘却了远在家乡的母亲,沉浸于这个我从未进入过的大城市,这里的人衣着时尚,举止大方。从小地方来的我就像一个丑小鸭一样混入其中,无地自容。
我学着与别人交往,做兼职,化妆,穿搭,学习。在学校里接触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而又有趣。我也慢慢融入了这个城市,成为了其中无名的一员。
时间不停的流逝着,直到有一天,在我在和室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这是一个佝偻着身子的女人,她站在拐弯口,偷偷的看着我们,室友敏锐的感受到了她的视线,害怕的拉了拉我的衣角问我:“你认识那个女人吗,她好像一直在看你哎。”,当我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的时,轰地一声,脑子一片空白,全身发冷,满脑子只有一句话———不能让他们知道这是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