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有没有发现,无论在哪个单位,最后混得好的,往往不是那个最有才的。
汉武帝的朝堂,就是最好的观察样本。那里有两个极端:一个是才华横溢、金句频出的东方朔,另一个是看起来温吞水一样的公孙弘。
结果呢?那个最有趣的灵魂东方朔,一辈子被当成笑话。而那个看似无趣的公孙弘,却官至丞相,善终。
凭什么?这事儿,两千年后看,依然扎心。
第一回合:一个人的正确,毫无力量
汉武帝初登位之时,下诏求贤能之士,欲破常规,东方朔登场颇具戏剧性,《史记·滑稽列传》记载:
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
三千片竹简,需两个壮汉方可抬动,武帝惜才,不辞劳苦陆续用了两个月才读完,此乃一场天才的营销,东方朔成功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爆款”。
但“爆红”之后的路,他走歪了。
汉武帝喜欢“射覆”。也就是将东西扣在碗底让别人去猜的游戏,与现在的“盲盒猜物”差不多。
汉武帝让术数家将壁虎藏在盂下,众人皆不能猜中。东方朔自告奋勇,以《易经》占卜后断言,《汉书・东方朔传》记下了他射覆壁虎的表演:
“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
汉武帝喜好方术,东方朔就利用《易经》来占卜,把普通的常识弄成了“上天启示”一样的东西,一下子就让答案变得很神秘且权威起来。
汉武帝大悦。在人才辈出的汉武帝时代,他以这般颇为引人注目的方式,成功吸引了皇帝的目光,为自身争取到了生存与进言的机会。
但从此,他的角色便被定位,一个解闷的“俳优”,他的智慧成了取悦君王的戏法。
他并非没有治国之志。当汉武帝欲扩建上林苑(即皇家猎场),需侵占千倾民田时,满朝文武噤声,唯有东方朔挺身谏阻。
他陈说三大危害,层层递进:
先用天人感应讲道理,说君主要是谦逊沉稳,上天会赐福;要是骄纵奢侈,上天就会用异常现象警告。
次从实际利益说起,点出扩建的危害,占用百姓的利益,会招致百姓不满。
三以历史为鉴,强调奢侈亡国的教训,引用殷、楚、秦三国的案例为警示。
结果呢?《史记》记载:
“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皇帝赏了他,夸了他,然后上林苑扩建工程照旧。

为什么?
一个人认为对的事,要是没法让大家达成共识,在领导眼里,那也只是他个人的“对”。
朝堂之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附议。在一个讲求“共识”的系统里,单一个人的正确,那在领导眼里,就只是“个人的偏执”。
反观公孙弘,他玩的是另一个游戏。他的崛起,正逢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孙弘不显山露水,却做了一件极高明的事: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平台”。
据《汉书·儒林传》载,他为丞相后,“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 这等于建立了官办的“儒生管培生计划”而 他自己就是首席导师。这些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官场,时间一长,朝堂上自然多了不少他的人。
他极力向朝廷举荐儒生为官,每回上奏疏时必定言:“此臣素知其贤,可任以事。”
像严助、朱买臣这类人,渐渐地儒生群体便成为朝堂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于是到了商议征讨西南夷之时,公孙弘认为此举劳民伤财,应予以停止,他先私下统一意见,在朝会中刚一提及,被他举荐的儒生严助、朱买臣等便立刻一同响应,营造出颇为强大的舆论态势。
汉武帝听到的,不再是公孙弘一人的声音,而是一个“儒生集团”的共同意志。结果,征伐之事遂罢。
你看,东方朔是单打独斗的“孤狼”,而公孙弘是“狼群”的领袖。才华需要载体,一个人的声音,永远大不过一个群体的合唱。
第二回合:“有趣”,是职场最大的陷阱
东方朔的第二个致命伤,是他太想“有趣”了,以至于透支了最宝贵的资产,信任。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一次著名的“割肉事件”:三伏赐肉,分肉官未至,东方朔等不及,拔剑自作主张割肉而去,还对同僚说:“伏日当早归,请受赐。”
事后汉武帝问他为何无诏割肉,东方朔张口就来:
“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妻子),又何仁也!” 《史记・滑稽列传》
汉武帝被逗得哈哈大笑,反而再赐他百斤肉、百石酒。
是不是颇具画面感:机智有时也被称作耍小聪明,“割肉遗妻”看似幽默之举,实则是在朝堂上做私人事,汉武帝的笑并非是夸赞他有才能,而是觉得他滑稽,随后更将他归入俳优一类了。
更致命的是私德,东方朔每年都换老婆,拿着皇帝赏赐的钱去娶新的抛弃旧的。长安的郎官私下都称他狂人,连普通官员都不把他当“国士”。
《史记》载:“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即弃去。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 在“孝廉”为选官标准的汉代,这种“岁更其妇”的行为,彻底击穿了其人格信誉。同僚们私下称他“狂人”,谁还把他当回事?
在特别注重伦理道德的汉朝,这种行为跟大臣应有的品德完全不相符,把他自诩“自己有王佐之才”这件事变成了一个大笑话,也说明了为什么汉武帝虽然欣赏他的才华,却不敢把重要的事务托付给他的原因了。
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公孙弘这人可不一样,他当丞相,却盖着粗布被子,吃的是糙米饭(脱粟之饭)。
御史大夫汲黯都看不过去了,认为他装穷,在朝堂上弹劾他:
“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
【译文】公孙弘职位在三公之列,俸禄十分丰厚,却盖着布做的被子,这是欺骗啊!
《史记》记载了他的反应:他不争辩,反而对武帝说:
“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
他承认自己或许在沽名钓誉,并称赞了指责他的人。这一下,反而在汉武帝心中坐实了其“节俭忠厚”的长者形象。

汉武帝想招揽人才,找来公孙弘问计。
公孙弘颇为聪智,他未直接向皇上言明“陛下我们应如何去做”,而是建议在现有制度之上进行一番“补充”,提出于原先的“举孝廉”基础之上再设置一个考儒家经典的环节。
这个办法还挺巧妙,表面上看,主意是皇上亲自定的,决策权还在皇上手里,这么着就稳稳保住了领导的面子;实际上是暗中给天下读书人开了条往上晋升的路。
司马迁称公孙弘为人有心机(为人意忌,外宽内深),但他确实成功塑造了一个令人信任、懂分寸的公众形象。
所以呢,专业信誉,是你最宝贵的资产。一旦为了短期关注而牺牲它,便再难赢得长久的重任。
第三回合:理想主义的黄昏
到最后,其实是两种活法的冲撞。
东方朔提出“朝隐”,说大隐隐于朝。这本身就是一种撕裂。直到暮年病重,他望着前来探病的汉武帝,用不再戏谑的语气恳切进言:
“《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史记・滑稽列传》
【译文】《诗经》里说“嗡嗡叫的苍蝇停在篱笆上,温和宽厚的君主,别相信谗言。谗言没底线,会搅乱天下。 希望陛下远离奸猾谄媚的人,摒弃谗言。”
汉武帝的反应是:“今顾东方朔多善言?”,意思是:今天东方朔怎么说起正经话了?
汉武帝感慨中,暗藏着东方朔大半辈子被忽视的境遇,此时直言已无作用,也印证了他在系统里保留自我的失败:平常不敢言说,想说话时却已无机会。
而公孙弘,则把系统的规则玩到了极致。以主父偃一案为例:
主父偃曾是汉武帝跟前的大红人,他靠着“推恩令”削弱诸侯的势力,让皇权变得空前集中,因而在一年里头四次升官,那可是相当风光。

主父偃出身贫寒,早年游学各地,受尽了诸侯王和儒生们的白眼及排挤,他怀才不遇,对权贵阶层积怨已久。
当他终于得到汉武帝的信任后,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尽报复当年轻视他的人。他揭发燕王刘定国的丑事,导致燕王自杀;又以齐王刘次昌与姐姐通Jan为由,前往查办,逼得齐王也自杀了。
结果得罪了一大半宗室诸侯;再加上他不愿意融入公孙弘带头的儒生那伙,就这么着,树了不少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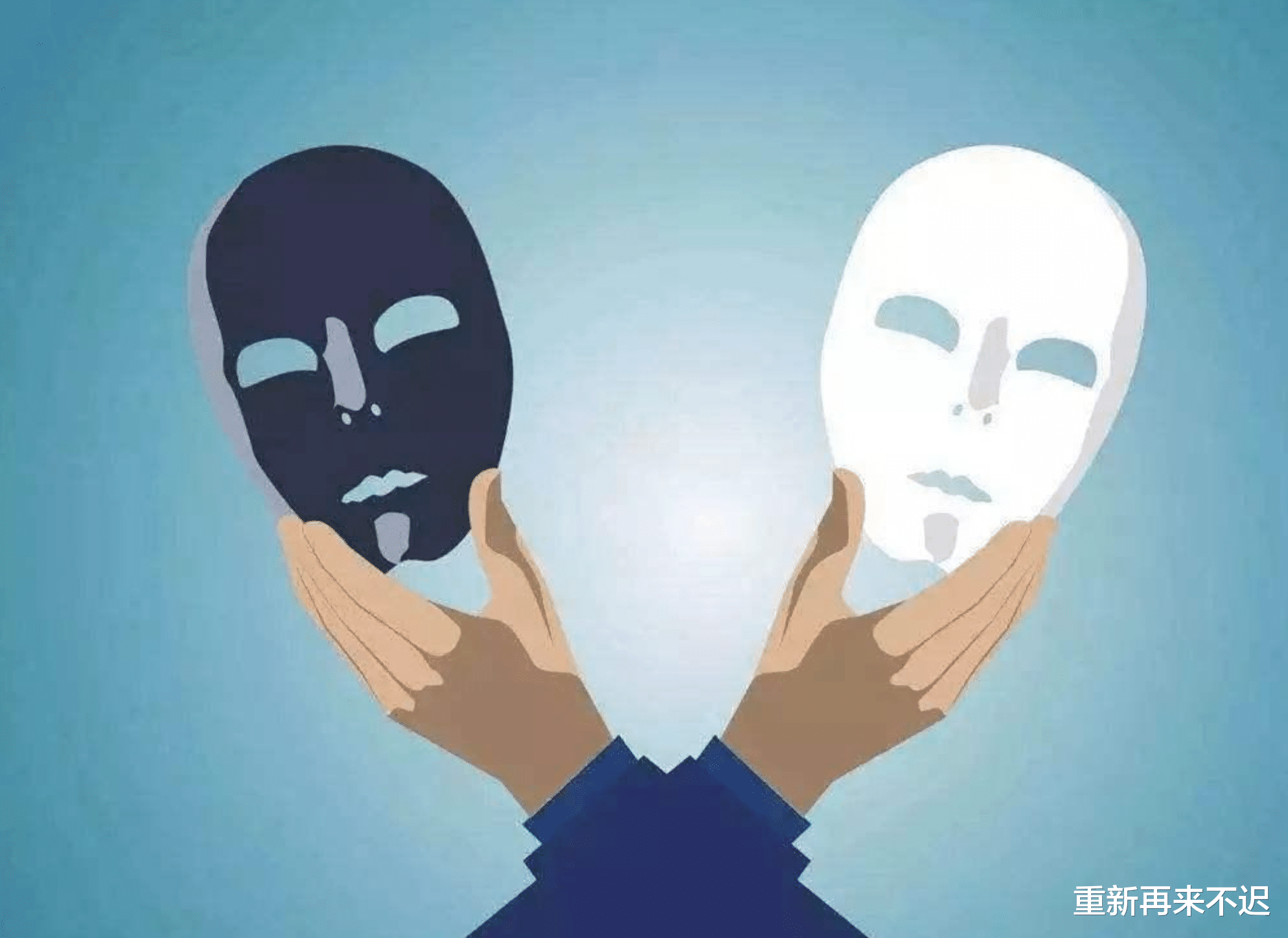
齐王自戕后,因无子嗣,封国归中央,这本是汉武帝乐见之事,但诸侯联合弹劾主父偃“逼死宗室”,令武帝骤然处于舆论风口浪尖。
武帝本想从轻发落,毕竟主父偃的才干实在难得。
但公孙弘在朝堂上轻飘飘一句话:
“齐王自杀,国除。不诛偃,无以谢天下。”
公孙弘精准地命中了汉武帝最在意“仁君”形象,所以用“无以谢天下”戳中武帝的痛点,既除掉了傲慢无礼、不融入儒生集团的主父偃,又示好了诸侯和儒生,这也许就是司马来老先生口中的“外宽内深”的处世哲学吧。
《史记》记载:“上遂诛偃。” 他用规则借力,自己手上还不沾血。
一个是想在系统里做自己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彻底弄懂系统并为我所用的现实主义者。结局,早已注定。
结尾
东方朔晚年的《答客难》早已参透了这一切。
他借客人之口问出“为何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的困惑。
随后自己长叹一声作答:“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战国时“得士者强”,可如今天下一统,领导“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纵有才华又能如何?
“用之时为虎,不用之时为鼠”,此寥寥十字,蕴藏着二千多年的几多不甘与通透。
无需惋惜东方朔,若他也学得公孙弘的圆滑,历史上便少了那篇振聋发聩的《答客难》,少了这种专门抒发怀才不遇的“客难体”,后世无数不得志的文人,恐怕连个发牢骚的范本都找不到。
也没必要全然效仿公孙弘的那类机巧,要知晓在职场中,“有趣”可不能当作生计依靠,“会办事”才是至关重要的要点。
多元化的社会,成功的定义早已不同。真正的智慧从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
读懂你身处的游戏规则,守住你心里最在意的东西,便已是难得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