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小县的夏日午后,空气燥热得发闷。院子里,两个女人扭打在一起,尘土飞扬。
个子高挑结实的母亲,正对着瘦弱矮小的女人拳打脚踢,嘴里骂骂咧咧:
“想把她带走?没门!除非你把钱留下,我养她这么大,凭什么白给你?”
被打的女人是我的姑姑,她头发凌乱,嘴角破了皮,却死死攥着我的手腕,眼神凶狠的像一头护崽的母兽:
“她是你女儿!不是你换钱的物件!你拿着她爹的命换来的钱改嫁,还要卖了她,你不配当妈!”
姑姑猛地发力,将母亲推倒在地,趁她没爬起来,拉着我就往外跑。
我回头望去,母亲坐在地上哭喊,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沓崭新的钞票,那是父亲用命换来的赔偿款。
那一刻,我唇间的疤痕仿佛在发烫,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丝暖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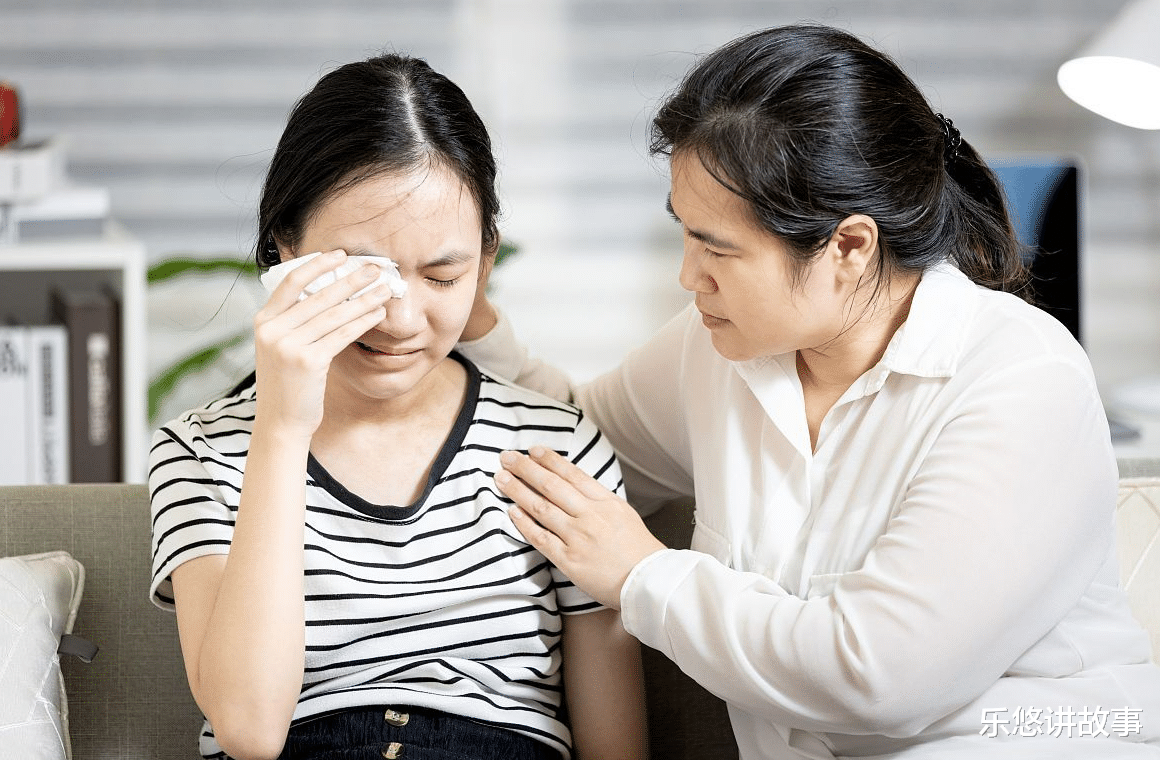
我叫林念,天生唇裂。
自记事起,母亲看我的眼神基本就是厌恶与不耐烦。
“当初生下来吓我一跳,怎么会长成这样?”
“早让你爹把她送出去,他偏不听,现在就是个累赘!”
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伴随了我整个童年。
家里穷,父亲是农民工,母亲是环卫工,爷爷奶奶早逝,日子过得紧巴巴。
母亲总说我费钱,衣服是捡来的旧款,书包缝了又缝,而她对我最大的“关照”,就是从不带我走亲戚,怕我给她“丢人”。
好在还有父亲。
他话不多,却总偷偷把工地上发的牛奶攒下来给我,夜里会用温热的手轻轻拍我的后背,说:“念念不怕,爹在呢。”
他还会给我讲远在外地的姑姑,说姑姑是教师,知书达理,是家里最疼他的妹妹。
而姑姑也确实一直记挂着我。
每年都会寄来合身的衣服,款式总是高领的或者连帽的,方便我想遮住唇间的缺陷;
偶尔会寄童话书,扉页上用娟秀的字写着“念念要开心”。
我把那些书翻得卷边,偷偷模仿上面的句子写日记,盼着有一天能见到姑姑。
虽然有这样好的爸爸和姑姑,可我还是自卑。
上课不敢举手发言,走路总低着头,怕别人看到我唇间的疤。
有一次,同学无意模仿我的样子笑,我躲在厕所里哭了一下午,回家后母亲看到我红肿的眼睛,只冷冷地说:
“自己长那样,还怪别人笑?”

十六岁那年,噩耗传来。
父亲在工地干活时出了意外,永远地离开了。
我跟着母亲和亲戚们去工地讨说法,老板最终赔了十万块。
母亲抱着那沓钱,脸上没有太多悲伤,眼睛里反而透出一丝“解脱”的光亮。
父亲的葬礼刚过半年,母亲就开始收拾行李,说要改嫁,对方是邻村的一个男人。
我看着她忙碌的身影,心里空落落的,却还抱着一丝期待:她会不会带我一起走?
答案很快揭晓。
那天,一个陌生女人出现在家门口,她眉眼间和父亲有几分相似,轻声说:
“念念,我是姑姑。”
姑姑得知父亲去世、母亲要改嫁的消息,连夜赶了回来。
当姑姑提出要带我走时,母亲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她是我女儿,凭什么你说带就带?”
母亲叉着腰,语气刻薄,“除非你给我一笔钱,就当是这些年的抚养费,不然免谈。”
姑姑气得浑身发抖:“那是她爹的命钱!你拿着钱改嫁,还要卖了她,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争执瞬间升级,母亲率先动手推了姑姑一把。姑姑虽瘦弱,却像被激怒的狮子,扑了上去。
母亲个子高、身体壮,起初占了上风,可姑姑拼了命似的,抓着母亲的胳膊不肯松手,嘴里嘶吼着:“我今天非要带她走!”
周围的邻居围了过来,却没人敢上前拉架。
我站在一旁,吓得浑身发抖,看着姑姑嘴角流血,却依旧不肯放手,心里对母亲最后一丝期待彻底崩塌。
最终,姑姑拉着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我生活了十六年的家。
走出村口时,姑姑停下脚步,蹲下来,用袖子擦了擦我的眼泪:
“念念,以后姑姑家就是你的家,姑姑会护着你。”

姑姑是一名初中教师,姑父是服装厂的设计师,他们没有孩子,待我视如己出。
刚到姑姑家的第一个月,他们就带我去了大城市的医院,商量唇裂修复手术。
“念念,别怕,手术之后,你会和其他姑娘一样好看。”
姑姑握着我的手,温柔地说。
手术很成功,术后姑姑寸步不离地照顾我,帮我涂抹药膏,教我慢慢练习发音。
姑父则特意为我设计宽松舒适的衣服,还笑着说:
“我们念念怎样都好看,衣服只是锦上添花。”
在他们的关爱下,我慢慢抬起了头。
以前不敢在课堂上发言,现在能自信地回答老师的问题;以前躲着别人的目光,现在能坦然和同学说笑。
我努力学习,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还遇到了一个温柔的男孩。
他知道我的过往,却从未在意我唇间淡淡的疤痕,只说:“这是你独一无二的印记,很珍贵。”
可我心里始终有个结。
母亲拿着父亲的赔偿款改嫁,甚至想把我当成商品卖掉,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很多年。
在姑姑的鼓励下,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那个小县。
按姑姑打听来的地址,我找到了母亲改嫁后的住所。那是一间破旧的平房,门口长满了杂草。
邻居们看到我,认出了我是母亲的大女儿,纷纷叹气。
“你妈啊,五年前就没了。”一位老奶奶轻声说。
我愣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邻居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我,母亲改嫁后,生了一个儿子,老来得子的她和丈夫把孩子宠上了天。
孩子从小就无法无天,十六岁就辍学在家,跟着一群人瞎混,染上了不良嗜好,还总偷家里的钱。
十八岁那年,他回家向母亲要钱,母亲没给,他竟趁母亲午睡时,下了狠手。
“造孽啊,太溺爱孩子,最后害了自己。”老奶奶摇着头,眼里满是惋惜。
我站在破旧的屋前,阳光刺眼,唇间的疤痕似乎又在隐隐作痛。
我以为自己会怨恨,会解气,可心里只剩下满满的悲悯。
母亲的一生,或许也是苦难的,她嫌弃我的缺陷,渴望更好的生活,却最终被自己的执念和溺爱反噬。
离开小县时,我在母亲的屋前放了一束白菊。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像一场无声的告别。
我想起姑姑说的话:“念念,苦难会过去,仇恨也会,唯有爱能治愈一切。”
是啊,我何其幸运,被姑姑的爱救赎,从一个自卑的女孩,长成了如今自信开朗的模样。
唇间的疤痕还在,却早已不再是我的枷锁,而是提醒我珍惜当下的印记。
那些曾经的伤害,终究在岁月的长河里,被爱与悲悯抚平。
人间百态,各有因果,唯有向阳而生,才能不负那些守护我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