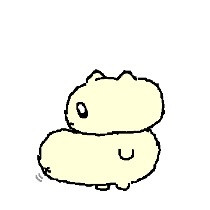58岁的婆婆守活寡15年后,被公公无情抛弃。
3年后,他带着现任妻子上门看婆婆笑话,推开门后现任妻子说:怎么是你?
......
一
门铃响了。
叮咚——叮咚——叮咚——
那声音,急切的像催命似的。
我和婆婆都知道是谁来了。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会用这种不容拒绝的、带着某种审判意味的力道按响门铃的人,只有一个。
我的前公公,江博文。
婆婆放下水瓢,没说话,只是用围裙擦了擦手,转身朝屋里走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单薄,却挺得笔直。
我知道,她不是去开门,她是去换一件更体面的衣服,去戴上那对小小的珍珠耳钉。
她在为一场迟到了三年的,无声的战役,做着最后的准备。
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栀子花的香气,似乎也带上了一丝紧张。
我走过去,拉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门外,站着两个人。
江博文,还有他身边那位,年轻貌美的,新任妻子。
江博文比三年前胖了些,头发染得乌黑,但掩盖不住眼角的疲态和微微下垂的嘴角。
他穿着一身价格不菲的名牌休闲装,手腕上的金表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像是在炫耀他如今的春风得意。
他身边的女人,妆容精致,一头栗色的大波浪卷发,姿态优雅地挽着他的胳膊。
她的目光像精准的扫描仪,快速地掠过我们这个有些陈旧但生机勃勃的小院,最后,落在我身上,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轻蔑。
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审视。
她今天来,就是来看失败者的。
“人呢?”江博文开口了,语气和他按门铃的力道一样,带着居高临下的意味。
“在屋里。”我侧过身,让他们进来。
那个女人脚上的高跟鞋,踩在院里的青石板上,发出“嗒、嗒、嗒”的声响,与这个小院里虫鸣鸟叫的宁静,格格不入。
他们是闯入者,带着一身都市的浮华与喧嚣,闯进了这片用三年时间,才好不容易凝结出来的,世外桃源。
我看着他们,看着他们脸上那副写满了优越感的表情,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三年前的那个下午。
那栋空旷、冰冷的别墅里,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名贵木材和皮革护理剂的味道。
江博文也是这样,像丢一件垃圾一样,把一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丢在婆婆面前。
“签了吧,我们之间,早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时候的婆婆,是什么样子的呢?
她像一尊沉默的影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家居服,瘦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她在那张巨大的红木沙发上,陷在柔软的真皮里,显得愈发瘦小。
她守着那个名叫“婚姻”的空壳,守了整整十五年。
十五年的无性婚姻,十五年的相敬如“冰”。
她就像那栋别墅里的一件旧家具,安静,沉默,没有存在感。
她的脚步总是很轻,说话的声音总是很低,连咳嗽,都像是怕惊扰了谁。
而现在,她从里屋走了出来。
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藕荷色棉麻衬衫,戴着那对温润的珍珠耳钉,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她脸上没有表情,眼神平静无波。
她看着江博文,就像在看一个,不怎么熟悉的,远房亲戚。
“来了?”她说,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压过了院子里的蝉鸣。
江博文的目光,在婆婆身上停顿了片刻,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诧异。
他大概是没想到,他眼中那个,一辈子都活在他阴影下的,懦弱的,逆来顺受的女人,如今,竟然能有这般,不卑不亢的,平静的姿态。
“这位就是……姐姐吧?”他身边那个女人,娇笑着开了口,声音甜得发腻,“博文经常跟我提起您,说您是个很……贤惠的人。”
她特意在“贤惠”两个字上,加重了读音。
像一把包裹着糖衣的,软刀子。
我站在一旁,几乎能感觉到,那股无形的,冰冷的刀锋,正朝婆婆刺去。
可婆婆,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她只是径直走到餐厅,拉开椅子坐下,对着我们说:
“都站着干什么?饭菜刚做好,坐下吃吧。”
桌上,摆着四菜一汤。
红烧肉,油焖虾,清炒芦笋,凉拌黄瓜。
还有一锅,用老母鸡慢炖了三个小时的,菌菇汤。
香气,温暖而踏实。
这是家的味道。
也是江博文,已经阔别了三年的味道。
他看着那满满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家常菜,眼神里,是片刻的失神和恍惚。
我知道,婆婆的每一道菜,都是做给他看的。
她在用她最擅長的方式,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宣战。
她在告诉他:你所抛弃的,正是你再也无法拥有的。
二
那个女人,显然对这些充满烟火气的菜肴,没什么兴趣。
她的目光,带着一丝嫌弃,在那些泛着油光的红烧肉上,一扫而过。
“博文现在,口味变得很清淡了。”
她体贴地为江博文拉开椅子,自己也挨着他坐下,声音娇嗲,“医生说,他血脂高,这些油腻的东西,都不能吃了。”
说完,她还示威似的,看了婆婆一眼。
那眼神里,充满了炫耀。
仿佛在说:看,现在,只有我,才最了解他,最关心他。
“是吗?”婆婆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人老了,身体是不比从前了。”
江博文的脸色,沉了一下。
“谁老了?”他像是被踩到了痛处,“我身体好得很!”
他说着,自己夹了一块红燒肉,像是赌气一般,塞进了嘴里。
咀嚼的动作,有些用力。
不知道是在品尝味道,还是在发泄什么。
我看着眼前这滑稽的一幕,想起了三年前,我们刚搬进这个小院时的情景。
那时候,婆婆比现在还要瘦,脸色蜡黄,眼神空洞,整个人,都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
她常常一个人,在院子里,一坐就是一下午,不说话,也不动。
像一株在阴暗角落里,快要枯萎的植物。
我丈夫江驰,还有我,都担心得不得了。
我们怕她想不开,怕她走不出来。
可她,却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活了过来。
她开始整理院子,翻土,播种。
起初,她的动作很生疏,常常把自己弄得一身泥。
但慢慢地,院子里的那片荒地,就在她的手里,变成了一片绿意盎然的菜畦。
番茄红了,黄瓜顶着小黄花,豆角也悄悄地探出了头。
然后,她把压在箱底几十年的画笔和颜料,重新找了出来,在阳台上支起了画架。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的婆婆,年轻时,是美院的高材生。
如果不是因为嫁给了江博文,被他以“女人家就该相夫教子”为由,折断了梦想的翅膀,她或许,会成为一名,很出色的画家。
她画山水,画花鸟,画我们这个小院的,春夏秋冬。
她的画,和她的人一样,淡雅,宁静,却又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
再后来,她学会了上网。
江驰教她用智能手机,用电脑。
她学得很快。
她开了一家小小的网店,卖她亲手做的刺绣和手工艺品。
一尾锦鲤的香包,一幅荷花的团扇,一件绣着兰草的旗袍……
她的手很巧,审美也极好。
小店的生意,竟然出乎意料地,越来越红火。
她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她会跟我聊,今天菜市场的哪家青菜最新鲜。
她会跟我讨论,新出的电视剧,哪个男主角更好看。
她甚至会戴着老花镜,研究我的化妆品,问我哪个色号的口红会让人看起来更明艳。
她像一个缓慢拆开的礼物,一天比一天,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她用三年的时间,把自己,从那个名叫“江太太”的,沉重的,枷锁里,解救了出来。
她活成了,她自己。
林晚晴。
而眼前这个,试图用“血脂高”来打败她的女人,又怎么会懂呢?
她所以为的胜利,不过是捡起了婆婆,早已不屑一顾的,垃圾。
“姐姐这几年,就住在这里吗?”那个女人,见一计不成,又换了个话题。
她环顾了一下四周,目光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怜悯,“这地方,是小了点,也旧了点。
博文一直都很挂念您,总说您一个人在外面,过得太清苦了。”
“要是您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博文说了,他会负责到底的。”
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
既彰显了她的“大度”,又炫耀了江博文的“有情有义”。
同时,也把婆婆,牢牢地钉在了那个,需要被同情,被施舍的,弱者的位置上。
我放在桌下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
指甲,深深地陷进了掌心里。
婆婆却像是没有听出她话里的机锋。
她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汤,然后才抬起眼,看向那个女人。
“我过得很好,不劳你们挂心。”
“房子虽然小,但很安静。邻居们也都很好,大家平时,会互相送一些自己种的瓜果蔬菜。”
“我每天,种种花,养养草,画几笔画,做点自己喜欢的手工,日子过得很充实。”
她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意。
“这种清净日子,说起来,还得多谢你们。”
“要不是你们,我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原来不当那个‘江太太’,日子可以过得,这么舒心。”
她的声音,很轻,很柔。
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根细细的针,精准地,扎在了对面两个人的心上。
那个女人的脸上,那副完美的笑容,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
江博文的脸,更是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林晚晴!”他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巨响,“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好心好意,带人回来看你,你就是这么说话的吗!”
“看来,这几年没我在身边管着,你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他还是老样子。
习惯了发号令,习惯了用这种咆哮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权威。
可他忘了,这里,早已不是他的王国。
而他眼前的这个女人,也早已不是那个,对他唯唯诺诺的,臣民。
三
“规矩?”
婆婆轻轻地,重复着这个词,语气里,带着一丝,淡淡的嘲讽。
“江博文,你大概是忘了,我们已经离婚三年了。”
“我不再是你的妻子,你也不再是我的丈夫。”
“这里,是我的家,不是你的。”
“在我的家里,我用什么态度说话,还轮不到你,来教我‘规矩’。”
婆婆的声音,依旧平静。
但那份平静之下,所蕴含的力量,却像一把锋利的,无形的剑,瞬间,斩断了江博文所有的,嚣张气焰。
他的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的脸,憋得通红,额头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地爆起。
像是被人当众,狠狠地,扇了一记无形的耳光。
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显然也没料到,这个看起来温顺无害的老太太,竟然有如此“伶牙俐齿”的一面。
她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精彩得像个调色盘。
“姐姐,话不能这么说吧?”她终于忍不住,帮腔道,“就算你们离婚了,夫妻一场,情分总还在的吧?博文他也是一番好意,关心你,你怎么能……”
“情分?”
婆婆打断了她,目光,第一次,正眼落在了她的脸上。
那目光,很冷,像深冬的湖水。
“这位女士,我跟我前夫之间的事,就不劳你一个外人,来置喙了。”
“你如果真的想关心他,不如多提醒提醒他,按时吃降压药,少在外面,动不动就发脾气。”
“毕竟,气大伤身。他这个年纪,可经不起什么折腾了。”
说完,婆婆不再看他们,低下头,自顾自地,吃起了饭。
那姿态,优雅而从容。
仿佛刚才那场唇枪舌剑,跟她没有半点关系。
江博文彻底被激怒了。
他猛地站起身,因为动作太大,膝盖撞到了桌角,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桌上的碗碟,都跟着跳了一下。
“林晚晴!你……”
他指着婆婆,气得浑身发抖。
他大概是想骂出些什么更难听的话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直沉默着,扮演着“背景板”角色的我,终于,缓缓地,抬起了头。
我的目光,越过婆婆,越过江博文,定定地,落在了那个年轻女人的脸上。
从她进门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她有些眼熟。
但因为她化了浓妆,又隔了几年,我一时,没有想起来。
直到刚刚,她情绪激动,脸上的肌肉,做出某些特定的表情时,一个深埋在我记忆深处的,模糊的轮廓,才终于,和眼前的这张脸,重合了起来。
是她。
竟然是她。
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小。
小到,你以为早已被冲进下水道的,那些令人不快的过往,会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转角,重新,浮现在你面前。
并且,是以一种,如此滑稽而荒诞的方式。
那个女人,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注视。
她下意识地,朝我看了过来。
当我们的视线,在空中交汇的那一刻。
我看到,她脸上的那份嚣张和得意,瞬间,凝固了。
取而代之的,是震惊,是错愕,是难以置信。
她的瞳孔,在急剧地收缩。
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想说什么,却又发不出任何声音。
她的脸色,在一瞬间,褪尽了所有的血色,变得,惨白如纸。
然后,我听见,她用一种,几乎是梦呓般的,带着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吐出了三个字。
“怎么……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