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仍是少年:杨振宁传》作者:林开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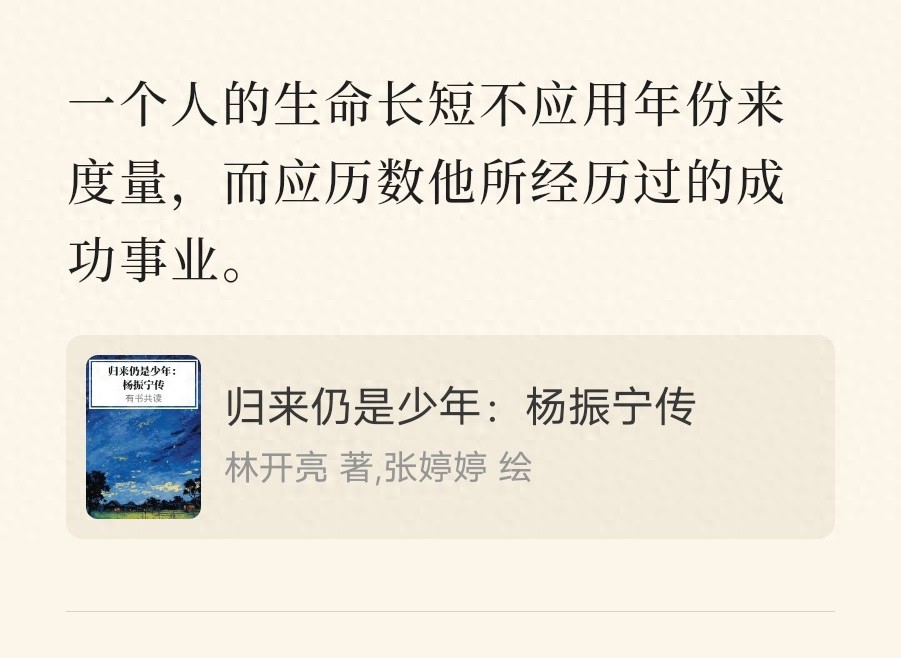
上一节,我们讲到了杨振宁离开普林斯顿,到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开辟了一番新天地,并多次回国,搭建起中美间了解和友谊的桥梁。
杨振宁在石溪分校工作到1999年,之后回到北京清华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杨振宁回到清华园的故事。
开创新事业——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其实早在1999年正式退休前,杨振宁就已经开始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的筹办事宜四处奔走了。那是1996年,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邀请杨振宁回清华,一起创办一所高等研究院。清华园——那是杨振宁童年时的乐园,因此他欣然答应。
但当时杨振宁还没有退休,只能先在美国和香港地区募集资金。1997年6月2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正式宣告成立,并于2009年更名为高等研究院。在这个过程中,杨振宁发起建立基金会,带头捐款100万美金,很多朋友也纷纷效仿。
其中有一位捐助者非常值得一提。他叫詹姆斯·赛蒙斯,数学家,量化投资大师。赛蒙斯23岁就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博士学位,后来与我国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共同提出“陈—赛蒙斯理论”,对量子场论和弦理论有突出贡献。
与此同时,赛蒙斯也是一个神一般存在的量化投资高手。1982年他凭借着自己的数学天赋在华尔街创办文艺复兴技术公司,旗下的投资基金业绩常年碾压“股神”巴菲特、“金融大鳄”索罗斯等投资界的顶流大腕。
从1988年开始,赛蒙斯掌管的“大奖章基金”年均回报率高达34%,即便是在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该基金的回报率不降反升。接到杨振宁的邀约后,这位量化投资大师慷慨解囊,给清华园里投资了三栋楼,这就是“陈赛蒙斯楼”。
资金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要招揽顶级人才加盟。正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杨振宁本人身先士卒,在高等研究院担任名誉教授,带博士生。之后他又列出了一张拟聘大师的名单。
从1997年成立以来,研究院聘任了多位顶级学者。比如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姚期智,2004 年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辞职,到高等研究院任全职教授。2021 年他获得了日本京都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
还有密码学家王小云,被高等研究院聘为 “杨振宁讲座教授”,2005年入职。王小云于 2017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9 年获未来科学大奖 ——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2025 年获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其实1999年从石溪分校退休后,杨振宁就想立刻归国。之所以耽搁下来,是因为他的夫人杜致礼罹患软组织肿瘤,需要动手术。但手术并没有挽救她的生命,2003年10月19日,杜致礼病逝;当年年底,杨振宁孤身一人回到了清华。
杨振宁将自己的新居命名为归根居,取叶落归根之意。他还做了一首《归根》诗,抒发自己的心志:
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
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
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
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
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这首诗的首联取自唐代诗人骆宾王的《浮槎》,意思是说当年我自恃有才,抱负远大。后面讲到的“千古三旋律” 则是指他在 2002 年的一篇演讲中,总结出二十世纪理论物理学发展的三个主旋律,分别是量子化、对称和相位因子。
而在诗的尾联,杨振宁体现出一种“不服老”的心境,即使已是年过八十的耄耋之年,自己也要以“东篱归根翁”的身份,开启一番新事业。其中的豪气,颇有几分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浑气势。
2004年9月,杨振宁应邀为新入学的物理系新生上了一个学期的普通物理课。工作这么多年来,他极少给本科生上课,之前他在石溪分校曾给本科生上过两次,这是第三次。200多名大一新生挤满教室,后排则站着慕名而来的外校教师。
杨振宁一共讲了30次,每次两堂课,大约讲了课本内容的一半。在最后一讲,他没有讲教材的内容,而是跟莘莘学子们分享了几位大物理学家的故事。有学生回忆这些课:“杨先生的板书工整,推导公式时手指微颤,却坚持站满90分钟。”
杨振宁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央视记者采访他时,提到了《归根》那首诗里的一句“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问他给本科生授课,是不是在“当指路松”?以后还会继续给本科生上课吗,还是把精力转移到研究生身上?
杨振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解释说到了自己这个年纪,已经很难再带着学生们在某个领域冲锋陷阵了,但自己可以给他们一些方向上的指引,就是“指路”。作为一名老师,最值得得意的事是让学生们能学到一些真东西,能走到某个领域里。
2012年,杨振宁 90 岁寿辰之际,清华大学召开了专门的学术纪念会,并赠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那是一块精巧的黑水晶立方体,顶部是他最喜爱的杜甫的诗句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四个侧面则镌刻着他的13项科学成就。
杨振宁高兴地说,这是自己收到的一件极重要的礼物。因为这是独属于他自己的荣耀,是他在粒子物理、场论、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四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每一项都具有开创性。它们如同13颗璀璨星辰,照亮了现代物理学的天空。
对建造大型对撞机说“不”
虽然杨振宁已经站在了学术“金字塔”的塔尖之上,但他绝不只是圈内闻名,而是经常“出圈”。2016年发生的一件事,让这位90多岁的老人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这一年8月底,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杨振宁。
这篇跟高能对撞机有关的文章写道:“每一次实验的突破,都代表着人类进一步地了解有史以来最想知道的事:天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些实验背后的基础理论都用到杨先生的学说,因此每一次突破,我们对杨先生的学问会有更进一步的景仰!所以说杨先生反对高能物理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使人费解!”
杨振宁认为这篇文章对他有所误解,因为他绝不反对高能物理继续发展,他反对的是中国要建造超大对撞机。因此2016年9月4日,他在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撰文进行澄清,这篇文章的标题很直白,叫《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杨振宁的反对理由有七条,我们着重讲前三条,主要是分析建造超大对撞机的性价比。在第一条,他指出美国在建造大对撞机时有过痛苦的经验。早在1989年美国就开始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一开始预算 30 亿美金,但30亿美金用完后显然不够,又要追加到80亿美金,最后在社会的一片反对中不得不终止,白白浪费了30 亿美金。他担心中国的超大对撞机项目,也会步美国的后尘。
这里补充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在欧洲,坐落于瑞士和法国的交界地带,在日内瓦的侏罗山地下100米深,总长约27公里的隧道内。这个对撞机的建造前后用了很多年,建造费再加上探测器费等,不少于100亿美金。
杨振宁在文章中估算,中国要建超大型对撞机,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金。虽然这笔费用可以由很多国家分摊,但中国要占的份额仍然相当可观。尽管我国GDP已经跃居第二,但人均GDP还很低,还有数亿收入更低的农民和农民工,所以杨振宁建议,这笔资金应该要用来解决环保、教育、医保等燃眉之急的问题。
这是杨振宁反对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即便中国能拿出这笔钱来发展科技,那为什么不用在一些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呢?比如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天文物理,等等,也需要突破。一旦上超大对撞机项目,这些项目的经费势必被挤压。
或许是因为杨振宁的反对,这个项目当时并没有上马。事实上,这并不是杨振宁第一次反对建造对撞机,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曾反对过两次。第一次是1972年他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高等物理发展与展望”的座谈时。
当时与会的学者有三十多人,有人提出要建造高能加速器,其它人都表示赞同,只有杨振宁明确反对。他说:“造贵的加速器与目前中国的需要不符合”。他还说:“我的想法也许是错误的,但据我观察,我相信,我的想法是对的。”
在那场座谈会上,杨振宁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制约高能物理发展的瓶颈不是建造加速器,而是要先实现物理观念的突破,而这个突破要来自理论物理领域。就像他和李政道先提出来“宇称不守恒定律”,然后吴健雄才取得实验突破的。
他提的第二个理由还是跟性价比有关。1972年,中国还处在一穷二白的特殊时期,很多人连肚子都填不饱。杨振宁建议应该把宝贵的资金花在刀刃上,先发展计算机、生物、化学等容易出成果、成果更容易给民众带来福祉的项目。
那次座谈会让国内物理界的同行们,第一次见识到了杨振宁的坦率、直接,也给他赢得了“杨振宁舌战群儒”的美誉。最后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表示赞同,说目前的研究方向应集中在花钱不多、设备不复杂而有意义的工作上。
等到1978年春,中国科学界再次考虑重启加速器建设工作,杨振宁再次表示反对。当时海内外重要的物理学家中,大概只有他仍持反对意见。不过一两年后反对的声音变多了,因为其它领域的研究者担心,这个项目会吸光所有的经费。
1980年1月,广州从化召开了一个高能物理理论讨论会,有一百多人参加,杨振宁和李政道被安排为会议发起人,其中有个议题就是讨论高能物理的发展。杨振宁清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希望这些专家签名,支持建造加速器。
杨振宁最终没有参会,其他人不但参加了会议,还在支持文件上签了名。他的“不配合”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杨振宁只好写了一封公开信进行澄清。他写道:“……我不能够无愧于心地去签署这个文件,因为我认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的签名,而是中国人民的签名。”
这就是杨振宁,有着儒家士大夫的风范,那是源自少年时读的《孟子》中的理念——虽千万人,吾往矣。
好了,本节的内容我们就先聊到这。下一节,让我们暂时离开科学,走进杨振宁的情感世界。让我们下节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