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诸说质疑
在曹雪芹的《红楼梦》[1]中,第五十二回薛宝琴所述“真真国女孩诗”有些另类。第一,这是小说中唯一一首外国人的中国诗;第二,这是小说中唯一没有题目的代言人物诗;第三,这是小说中唯一由他人转述而非本人即时写作的诗;第四,这是一首内容“写汉”但解说纷纭且歧义甚大的诗。所有这些,都使得此诗蒙上一层迷雾。

改琦绘薛宝琴
拨开迷雾的唯一方法,是走近此诗的真正作者曹雪芹,而不是转述者迷雾般的薛宝琴。薛宝琴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写实与隐喻二重性的人物,笔者此处不拟讨论。“真真国女孩诗”全文如下:
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708页)
这首诗解读纷纭。主要有以下诸说:
1,“思故明”说;2,“自况未来”说;3,感叹飘零羁旅说;4,隐括全书说。
“思故明说”云:“朱楼影明。水国影清,‘岛云’句疑谓朱成功(按:即郑成功)在台湾,‘岚气’疑指吴三桂入湘。五句疑谓江山依旧,六句疑为忧乐不同。末二句感时怀古,说出心事。疑国初有藩属思故明者,故下文有‘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之语。”[2]
“自况未来说”云:“全诗说自己憔悴流落于云雾山岚笼罩着的海岛水国,昨日红楼生活已成梦境,眼前只能独自对月吟唱,忆昔抚今,不胜伤悼。这客观上就是宝琴将来的自况。”[3]
“飘零羁旅说”云:“这首诗分明充满对背井离乡、飘零羁旅生活的感叹和对昔日繁华荣耀的怀念,实际当是宝琴假托真真国女孩在吐露自己的心迹,隐寓她自己未来的命运。”[4]

《新批校注红楼梦》
“隐括全书”说谓:“此诗辞旨沉郁,境界宏丽,有唐人诗风。乃借西洋女子之口隐括全书,感慨红楼一梦转瞬即醒也。”[5]
《红楼梦》的诗作,除了第一回“石头”题诗和“曹雪芹题诗”为作者自言,以及个别“有诗为证”实为作者所写以外,其他几乎都是在小说情节中曹雪芹为人物代言诗。
但不论书中的诗作者为谁,都要遵循“诗言志”的写作原则,即是表达人物情志的文学形式,因而必须合乎情感抒发的“事体情理”。
即使在以后的情节发展中,有些诗句可能被应验,似乎是对未来的预言,也应该符合现实或幻想逻辑,如《葬花吟》“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之类“似谶似真”的诗句。
在小说第五十二回情节里,宝琴此诗,并非己作,而是她转述真真国女孩之作,也就是曹雪芹代真真国女孩之作,应该表达的是真真国女孩的情志。

《从曹学到红学》,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说宝琴此诗“自况未来”,或者“隐括全书”,显然都不符合“诗言志”的规定性原理。宝琴未来归宿情节中并无任何暗示,也不是她自己的诗,怎么能够“自况未来”呢?明明是在众人聚集的写实场景里,宝琴转述真真国女孩的诗,怎么能够“借西洋女子之口隐括全书”呢?两说似可否定。
“思故明”说和“羁旅飘零”说的共同点都是怀旧,多少能够在诗境中找到依据。但“思故明”说,每句都落实鼎革时期史事,过于粘滞,而且曹雪芹写作时已经入清百年,说还有“藩属思故明者”,也不符现实事理。何况作者是一位黄发西洋女子,她凭什么要“思故明”?
“感叹飘零羁旅”说似乎符合诗境,但宝琴所叙的真真国女孩子服饰“镶金嵌宝”,一派富贵气象,又有什么背井离乡的凄凉,有什么“昨夜朱楼梦”值得怀念呢?可见,此说也不能成立。
上述诸说的问题,是都离开了所代言作者“诗言志”的事理。要寻求正确解读,必须回到“言志”的路上来。

二、从语境到语义
要准确把握诗歌语义,必须从写作语境出发。这首诗的写作语境,宝琴说得很清楚:
我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戴的都是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棉袄袖,戴着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儿上的也没他好看。
有人说他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作诗填词,因此我父亲央了一位通事官,烦他写了一张纸,就写的是他做的诗。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
明末清初,随着贸易增长和传教士东来,中西文化交流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曹雪芹的祖辈曹寅李煦都参与其中。《红楼梦》中对此也有反映,如贾府的西洋器物,以及王熙凤自述王家管理所谓“进贡”来往等。
薛宝琴则是年轻一代中因跟随父亲经商在沿海和国内有较丰富阅历的唯一女性。十首怀古诗,可见在内地的足迹;真真国女孩,则是沿海所见。她的叙述,折射出了当时的中西海外贸易状况。
从康熙收复台湾后(1684)开放海禁,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严厉管控,八十余年,海外贸易得到一定发展。其间因担心汉人聚集南洋反清,曾发布《南洋禁海令》,但未禁中西,这可能也是宝琴不提南洋而只说“西海沿子”“西洋美人”的原因。

《曹寅与曹雪芹》(增订本),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对于“假语村言”,当然没有考证落实的必要。王蒙先生认为:“宝琴的出现给读者打开了一面窗子,令读者想到大观园外还有广阔的世界。”
关于西洋美人装饰,他推测为印象与想象的集合:
披着黄头发,像欧洲尤其是北欧,头发打着联垂,像非洲;满头珠宝,像是中东中亚;反正我们从这个真真国的女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外国,可以看到世界,看到一种叫做西洋景的东西。[6]
宝琴的描叙显然有夸饰,但有真实内核。她见过“西洋画”即油画,惊异于油画对女性美精细描写的水平,惊异于洋女的美丽可能是真实的,因为传统中国人物画很难写实;最重要的是,她告诉大家,这是一位热爱仰慕中华文化的外国女子。她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包括以诗书五经为代表的汉文化传统,以作诗填词为代表的汉文学传统,薛宝琴还得到了她手写的汉语五言律诗。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标志。能写汉语近体诗,可见对汉文化的掌握熟悉程度。应该说,这首诗就是表现真真国女孩对中华文化的真诚情感的。这才是宝琴所叙西洋女子的“诗言志”,也是曹雪芹用“真真国”命名其国并为之代言的原因。
这首西洋女子手写的五律没有标题。这是《红楼梦》中唯一无标题代言诗。
早期古诗原无标题,如《诗经》、《古诗十九首》,但成熟的格律诗都是有题的,《无题》诗也是题。点题切题都是写诗基本要求。此诗为何无题,也不用《无题》,曹雪芹是否有意留白,不能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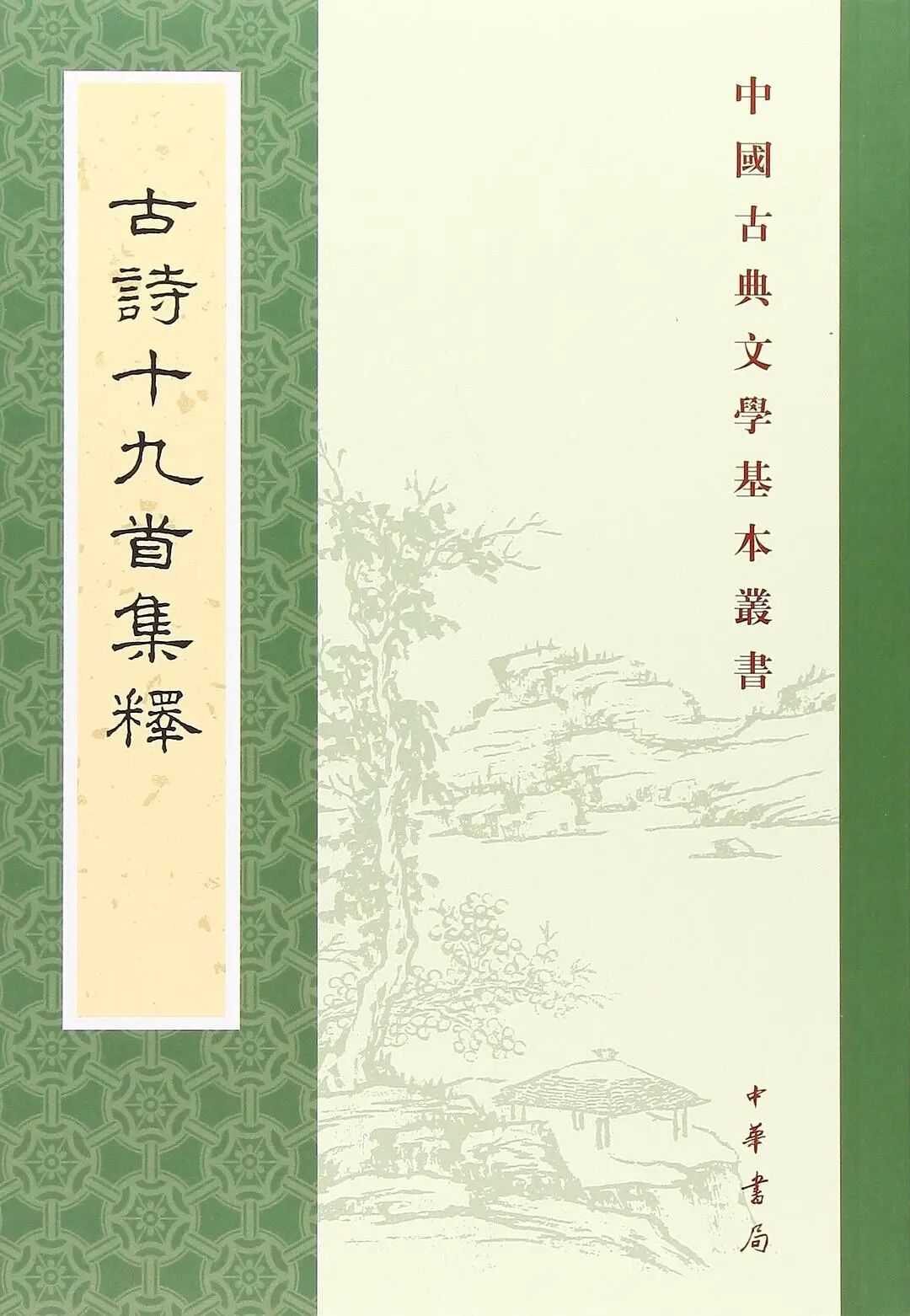
《古诗十九首集释》
不过,构思完整,意境宏阔,确实写得不错。首联“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似乎写旅途,实际隐含明(朱楼)清(水国)兴亡历史,但并无凄怆情感,这就否定了“悼明”说。
颔联“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分写海陆之景,似乎承曹操《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耸峙”而来,但曹操是陆地视角,“岛云”却是海中视角,确实有海上气象。有人视此“岛”为“台湾”,不为无理,不过未必与郑氏据台有关。
颈联“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是议论景情,实际上涉及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境界十分超脱开阔。可以说,前六句分写中华历史(亡、兴),地域(海、陆),文化(天、人),具有高度概括性,但情感含而不露,尾联才画龙点睛,直接表达她对这块所热爱的土地命运的关注:“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

《庾子山集注》
这里借用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所用典故是东晋桓温故事,《世说新语·言语》载:“桓公北伐,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金城”其实在江南,并不在汉南。[7]“春历历”是春天美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崔颢)此诗却是以景喻人喻事,以“汉南”代指中华大地,表达对中国美好生活的关切愿望。尾联结意,这应该就是“真真国女孩”诗的主旨。
真真国女子虽然穿戴民族服饰,却没有用诗描写自己的民族国家,也没有写异国风光,而是从历史地域文化的宏阔视野真诚“关心”中国大地的命运。正是这种感情的表达,引起了共鸣,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竟比我们中国人的还强。”

三、代言与自言
从性质说,“真真国女孩诗”如同《葬花吟》等一样,是曹雪芹的人物代言诗。不过这个人物比较特殊,是宝琴所述的一位热爱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西洋女子。
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作者曹雪芹的内心产生了高度的契合,使它成为一首代言与自言融合的杰作。也就是说,它既表现了一位外国女子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也融入了曹雪芹本人的民族意识和情感。
由于宝琴所叙这位“十五岁”的真真国西洋女子多“假语村言”的夸饰成分,因此,所谓“真真国女孩诗”实际上可以看作作者曹雪芹的“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夫子自道。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汉”的作为多义语词的符号功能,被曹雪芹发挥尽致。“汉”本是水名,至“汉朝”为国名,至“汉人”为族名,这一变化与中原华夏古民族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最后成为华夏文明即中华文明的主体文化符号。[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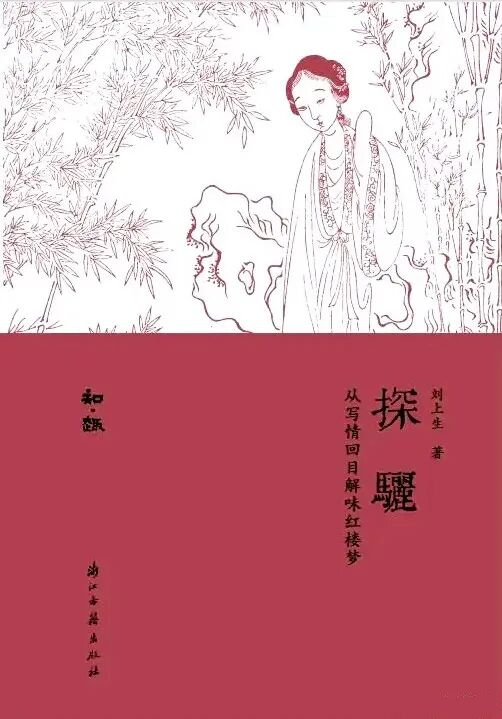
《探骊:从写情回目解味红楼梦》,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版。
这首诗中其实出现了“明”“清”“汉”三个相关符号,但“明”“清”作为朝代符号是隐含在诗句中的,只有兼有地域、族类和文化符号内涵的“汉”凸显出来。
从地域意义说,“汉南”来自《枯树赋》用典,“汉南”代指江南,“依依汉南”,本是羁留北方政权的南梁汉臣庾信怀念故国故土之情。曹雪芹为洋女代言“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实际表达的是在江南生活了四代近六十年的包衣曹家和度过了幼少年时代的曹雪芹本人对江南故土和汉民族生活圈的怀念。
包衣曹家祖籍辽阳,“从龙入关”,但所作并无片语关外乡思。而“秦淮风月忆繁华”“秦淮旧梦人犹在”等诗句,却表明敦敏、敦诚兄弟十分了解好友曹雪芹把江南视为故土故乡的感情。[9]
《红楼梦》贾、史、王、薛“四大贵族家族”以及影射曹家的“江南甄家”,“金陵十二钗”簿册女性悲剧,都以江南为原籍。所有这些,都说明曹雪芹借洋女表达的“关心”“汉南”即江南之情,不在祖籍乡关,而在视为故土的民族本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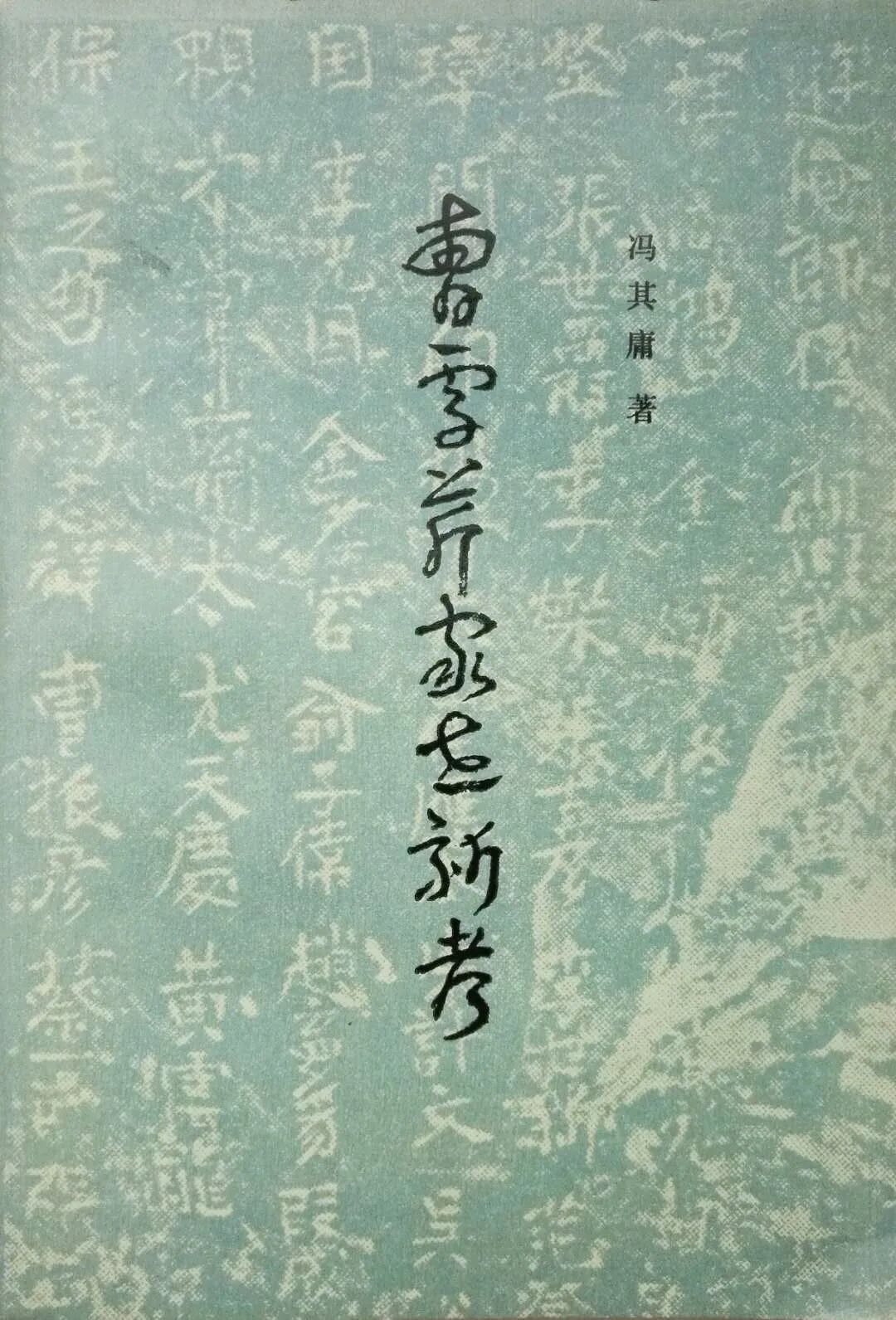
《曹雪芹家世新考》
《红楼梦》一直用真假(甄贾)手法,唯独这首诗是“真真”国人做的,其意乃强调此诗情感寄托之“真”。作为内务府正白旗包衣汉人的曹雪芹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有一种执着热爱之情。
“真真国女孩诗”以“汉南”代“中国”,曹雪芹以“汉南”代“江南”,以“汉地”代“汉人”,以“怀汉”写民族之情,这是在满清王朝时代满汉融合却又旗民分离时代,汉民族文化本根心结的深沉寄托和巧妙表露。
作者紧接着描写,这种西洋女子的“关心”汉地的情感,得到的热烈反应是:“众人听了,都道:‘难为他,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把包含旗汉在内的接受者“中国人”与作为族类,文化与地域符号的“汉”联系共情,“汉”与“中国”完全相通,这在满清统治下的“大清”王朝下,自然用意很深。
历经百年统治,康乾时期,满清统治者已经自觉认同“中国”了。乾隆就明确规定:“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清高宗实录》卷784)曹雪芹则有意突出汉(文化)在中国(华夏文明与王朝政权一体)的主体地位。
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历史华夏文明不因种族冲突王朝兴亡而中断,“关心”和守护主体汉文化,正是入旗的包衣汉人曹雪芹的情感血肉和自觉使命担当。
著名文史学家葛兆光论述“中国”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时,精辟指出:
在文化意义上,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
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使得这一以汉族为中心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经由常识化、制度化和风俗化,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下层扩展,至少在宋代起,已经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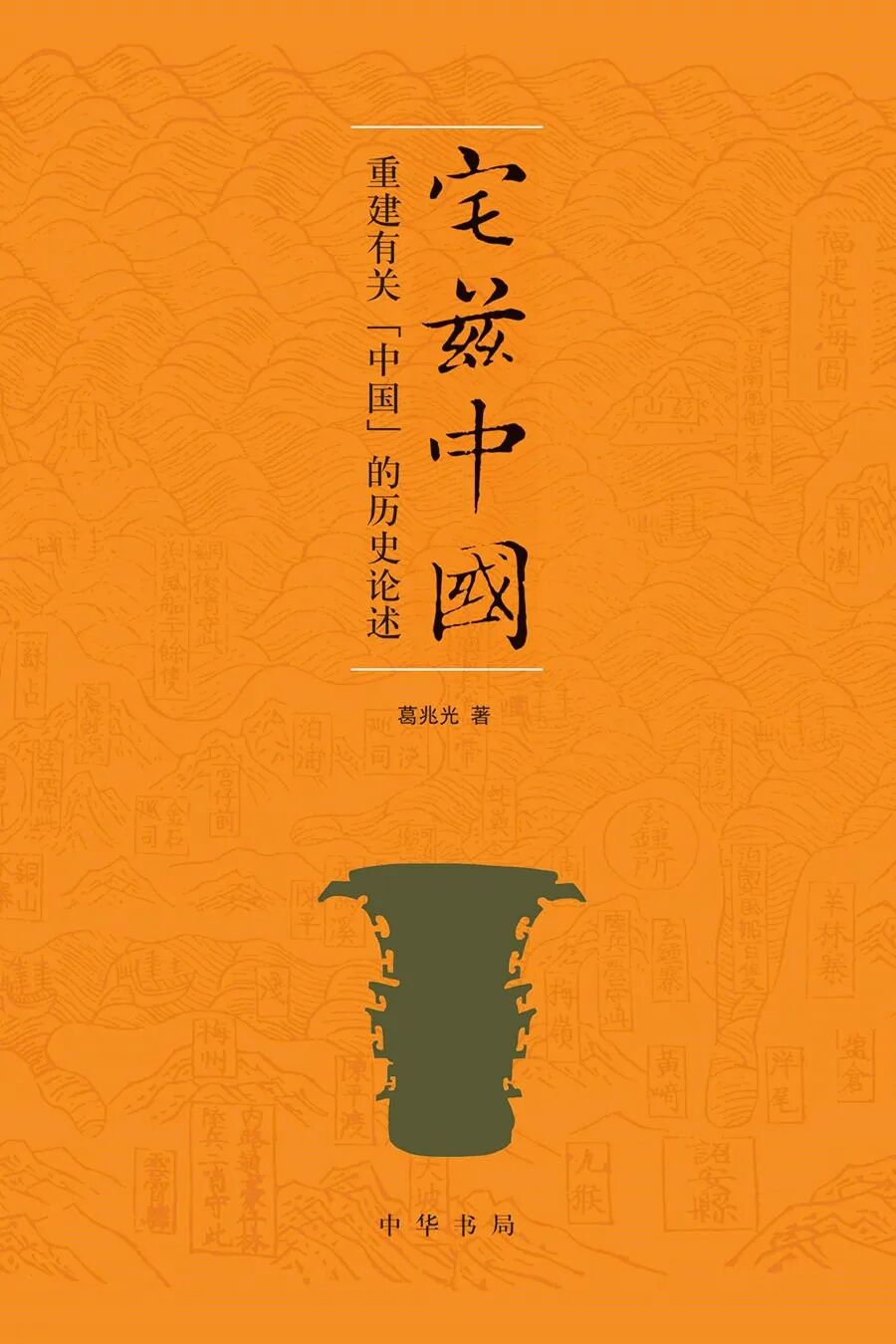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曹雪芹的认识,达到了与历史趋势一致的高点。

四、走近与共情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者代言书中人物薛宝琴转述的所谓“真真国女孩诗”,实际上乃是曹雪芹借洋女爱中之意,写自己的旗人怀汉之情,表达了包衣曹家和作者曹雪芹本人的汉民族本根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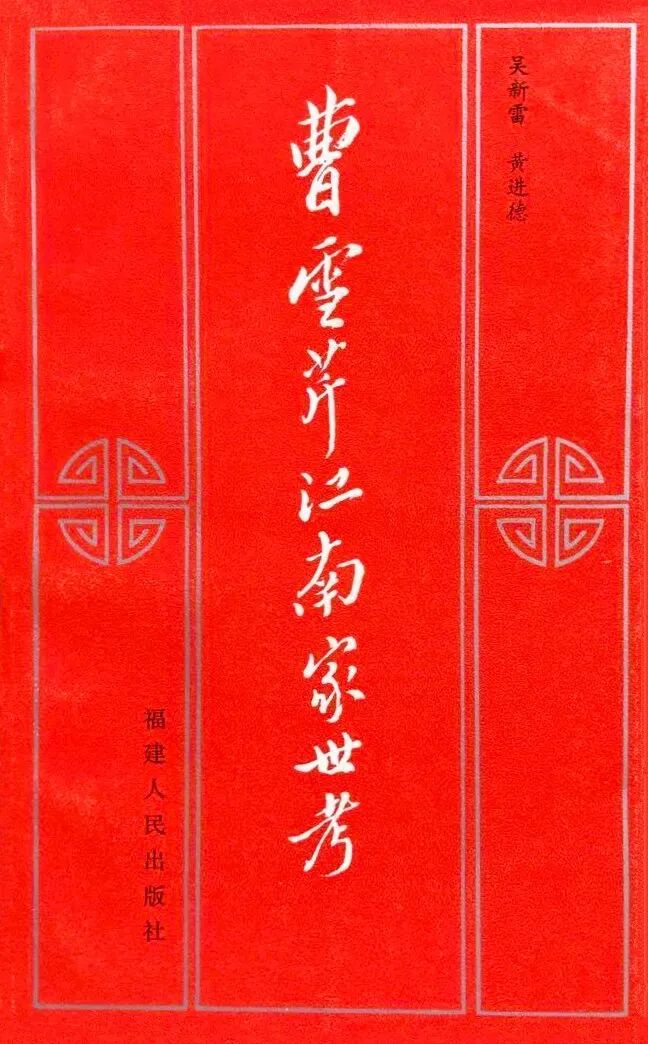
福建人民出版社版《曹雪芹江南家世考》
然而,要理解并与作者共情并不容易。“悼明论”者虽然感受到了曹雪芹和包衣曹家的民族意识,却把它归结为对一姓一朝的忠诚,这是明显的歪曲和矮化。“满化论”者则片面强调旗人的满化影响,看不到或者否定曹雪芹和包衣曹家对民族本根的坚守,也否定了满清王朝和旗人接受汉文化的历史事实,是另一个方向的歪曲和矮化。这两种错误观点的共同之处,则是无视满汉融合于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
至于今日视点,固然高屋建瓴,但也不能脱离时代与作品实际,以致影响与作者共情。有人从宝琴所叙“真真国的女孩子”看到国人的保守和自大心态:
……最好的对于世界对于外国的认识也不过是有一些西洋景,文化还是得听中原的。所以西洋景上的女孩子人长得装扮得再好再美,文化上只有唯中原文化的马首是瞻,那时的人们无法想象中原之外另有文化。阅者不妨自有所感,未与曹雪芹共情,反失其真意。真真国女孩子喜爱仰慕中华文化,善意地“关心”这块土地和人民,何曾“马首是瞻”地盲目崇拜?
古代中华文化固然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但也有悠久深厚确令外人仰慕的一面。特别是中西交流初期,从传教士和外国商旅传回本国的诸多正面信息,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莱布尼茨,德国文豪歌德等对中国文化的理想化议论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印象。宝琴所见真真国女孩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也正是那个时代这一方面情况的真实反映。
何况“西学东渐”以来,一些先进的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包括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说“那时的人们无法想象中原之外另有文化”,也有失偏颇。今天的思想史家已经把十六世纪以后的中国视为思想史的一个新的时代了。[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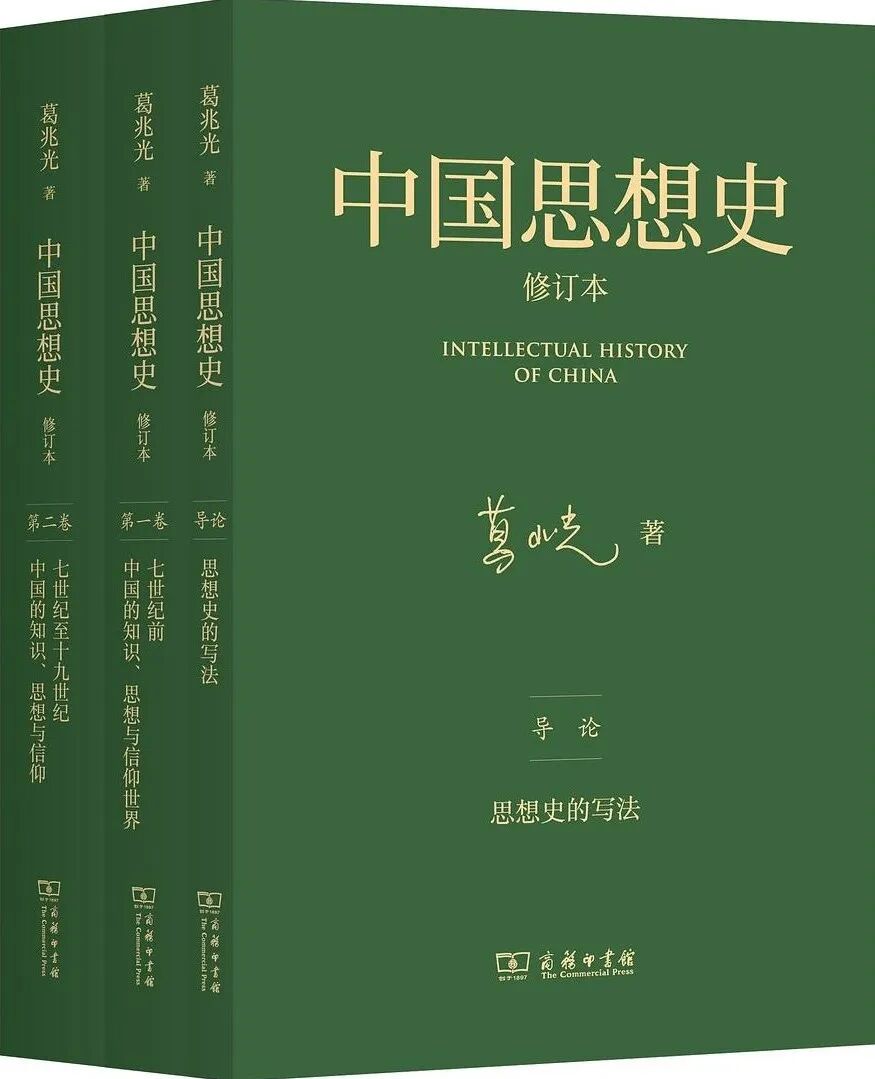
《中国思想史》修订本
曹雪芹借“真真国女孩诗”表露的对汉文化本根的坚守,对中外交流的善意态度,符合中华民族利益,顺应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写汉”是曹雪芹表达民族情感的重要用笔,当然并非《红楼梦》的主旨,要正确阐释研究。我们只有走近曹雪芹,才能真正走进《红楼梦》。
2025年12月28日于深圳
注释:
[1] 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苗怀明整理《王伯沆批校<红楼梦>》(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715-716页。
[3]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注释》,现代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233页。
[4] 李希凡冯其庸主编《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260-261页。
[5] 张俊、沈治钧《新批校注红楼梦》(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942页。
[6] 王蒙《王蒙谈红说事》,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201页
[7] 徐震堮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64页。
[8] 参见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9] 参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1、6、7页。
[10]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32页。
[11] 参见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版,439-5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