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已经走过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求学和职业路径。
然而,这份光鲜背后,是她长期无法融入社交的困惑与自我怀疑。
2025年3月,小云被确诊为阿斯伯格综合征,这个迟来的诊断为她过往种种不合群提供了不同的理解框架:
从小到大,小云感到自己像是被困在一个她无法理解规则的游戏中。
幼年期,她就与同龄人没有共同兴趣爱好;到小学高年级,她便感觉到无法融入到主流的社会规则中;再到成年后,几乎所有的恋爱关系都以对方厌恶告终;即使在最擅长的医学领域,她也因为种种原因选择离开。
但确诊并没有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变,小云依然过着她所形容的“边缘生活”,依赖严格的作息维持身心平衡。
小云的故事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一个崇尚统一标准的社会,神经多样性个体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
文 | 鹿小葵
编辑 | Zoey_hmm
图源 | 受访者、Pexels、Pixabay、AI
 从怀疑到确诊的漫长之路
从怀疑到确诊的漫长之路2020年起,小云在国内接受心理咨询,但这条路并不顺利。
她的咨询师归属精神分析流派,将她的问题归为后天家庭环境影响,给出的诊断是“自恋型”,治疗核心是让她学会接受不确定性,例如工作上临时变动、没有提前安排好的事情,又或许是突发的聚会邀请。
“咨询师让我去感受这些东西发生时,那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接纳它。”
小云回忆。咨询师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改变她对不确定性的排斥。
但这恰恰是她最难承受的刺激,几年下来,这种治疗方向并没有减轻她的不适感。

更让她困惑的是,当小云告诉咨询师她的ASD诊断时,对方并不认可。“咨询师觉得我不是自闭症。”小云说,“这也影响了我对她的信任。”
作为医学专业出身,小云对ASD并非完全陌生。她甚至学习过自闭症的诊断标准,但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符合。“很神奇,我自己都学过,但我根本不觉得自己是。”
在精神科当住院医师轮转期间,小云曾主动向科室主任求助:“我觉得我应该有精神问题,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主任回应说:“你有今天的这种学术成就,你考到这种学校,不可能有问题的。你肯定没有任何精神类的诊断。”
听到这样的回应后,小云失望地走了,继续在困惑中摸索。
转机出现在2024年年底。
那时她已在英国工作,一次升职后,小云的工作职责发生了变化:需要带领团队,更频繁地与人沟通协调。而那段时间合作的同事,常让她觉得“不够坦诚”,也喜欢“反复更改既定计划”。

小云离开北京去英国的飞机上
多重因素长期影响下,她的情绪逐渐陷入低谷。于是,她开始在当地寻求心理支持。
恰好她在公司听到了关于“neural diversity”(神经多样性)的宣讲,结合当时的挣扎状态,她开始考虑自己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通过网络搜索,小云找到《青衫》公众号做了筛查量表,结果显示阳性。虽然她知道“很多人都会筛查出来”,但这个结果还是为她的怀疑提供了某种印证。
真正推动她寻求正式诊断的,是英国的GP(全科医生)。在她描述自己的困扰时,GP建议她可以考虑转诊到专门的机构进行“neural diversity”相关评估。
2025年3月,经过专业评估,小云获得了ASD的正式诊断。

诊断证明
“我回答不出来,因为我也有述情障碍。”谈及确诊那一刻的感受,小云说,“我只能说心情很复杂,但是具体是什么我说不出来。”
面对结果,她保持着理性和开放的态度:“我不觉得自闭症、ADHD或者其他症,是我们对这件事情认知的尽头。”在她看来,当前的诊断只是科学认知的一个阶段,“但我觉得还有更多可能性。”
从怀疑到确诊,小云这一路走得十分漫长,也很挣扎。确诊则是重新理解自己的开始。
 用ASD解读过往人生
用ASD解读过往人生确诊后回看过往,小云开始从一个新的视角回看自己的成长,许多往事也因此有了不同的解释。
从小就读于全寄宿制学校的她,很早就被生活老师注意到一些特别之处,并多次向父母反馈“小云应该是有神经质,她对于某些事情过度执着了”。
幼儿园时期,其他孩子们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小云唯独喜欢积木。小学阶段,小云在理解语文阅读题方面很是困难,但对数字有强烈的兴趣。在生活上,她严格执行每日作息,需要在固定的时间起床、吃饭和睡觉。
社交方面,虽然能结识朋友,却总难以维持长时间的友谊。她依稀记得,从小到大经历过多次春游,其他同学都会三三两两坐在一起欢声笑语,自己旁边的座位总是空的。

这样的社交障碍一直延续到成年后。小云坦言自己曾有过多段情感经历,但“全部都是以对方非常讨厌我结束”。
一个典型的例子至今让她印象深刻。大学时期的某任前男友,分手时崩溃地问:“为什么无论和你聊什么东西,最后你都会谈到人类的进化?”
不管聊什么日常话题——吃饭、喝水、睡觉,小云都会不自觉地引向抽象、宏观层面的思考,例如“我们人类的历史发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这样生活?”
当时她将此归结于自己的原生家庭和性格问题。现在明白了:“其实就是说不到一块去。仔细想,那些前男友基本上都是这个原因分手的。”
小云另一个被朋友评价的特质则是她对未来“奇怪的天真”。“我要到几岁结婚,几岁生孩子,我后面人生怎么过,”这种详细到80岁的人生规划,让很多人感到压力和古板。
“大家谈恋爱,都是当下玩一玩开心就好了。”小云的思维模式却是系统性的、长远的。
这种思维模式同样体现在她的学习上,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一年级,刚刚接触新学科时,她都会经历倒数的过程。
学医时尤为明显。“我当时排名倒数持续有两年,相当于这两年的时间完全学不明白。”当时她感到医学课程都是“非常琐碎的知识点”,而她“想要一些系统性的知识”。
解决方案则是课外自学,将知识点提炼为体系。过一年或者一段时间后,顿悟就好了。学医后期,开始进行理论与知识实践时,她才适应和上手。
而做住院医师时,她偏执的特质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她坚持(并且现在也这么认为)认为脑梗病人最关键的治疗是康复训练,“比如某个病人有半边偏瘫,你就需要每天早晚帮病人活动关节,康复肌肉的力量。”
而其他医生更关注CT、抽血等检查数据。同事会告诉她“你纠结这个是没有用的”,对她的行为感到不解,并认为她影响了正常的医疗流程。“我当时基本上都觉得(自己)有点轴了,每天盯着康复医生去活动病人身体。”
小云认为这对病人最重要,数据反而不是关键。这种“轴”让她与周围人显得格格不入,她觉得“大家都只是在KPI里面活着。”

如今回头看,小云意识到这种对细节的执着、对自认正确的坚持,也是ASD特质的体现之一。
小云考入的是北京大学八年制临床医学项目。但由于始终无法适应医院的环境,她最终在博士阶段选择退学。“我需要找到一个更适合我的地方。”她解释道。
这也是她认为目前人生中自闭症特质对她生命轨迹影响最大的一次。
实际上,直到2021年到英国攻读硕士项目时,她的学习模式终于得到了更好的匹配。该项目以问题解决为核心,遵循“先提出问题、再寻找答案”的思路,这一教学方式更契合她的思维方式。
然而,与这种专业领域过度聚焦相映照的是,她在信息获取方面的局限性。她用“管状视野”形容自己:只关注兴趣领域,对其他信息视而不见。“我完全不喜欢八卦追星,这些东西我没有任何了解。”
这种特质在求职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她并不清楚自己到底能干什么,后来才发现,别人会为了求职做广泛研究:在英国能干什么工作、有哪几种签证、哪些行业好进入等等。
通过ASD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这些经历,小云发现那些曾经让她困惑的特质,从感情关系、学习模式、再到求职,都有了不同的解释。
新角度帮她更好地认识了自己的神经特质,也有助于她在比成年前更复杂的社会、职场中,探索更适合的生活方式。
 当下的边缘生活
当下的边缘生活“我现在已经是边缘活着的状态。”
小云如此描述当前生活状态。确诊ASD六个月后,她的日常依然被各种困境包围。
最大的挑战来自工作中的持续消耗。每天上班像一场表演。“上班开会的时候,我会用另一种状态去应付,这可能就是他们所说的masking(掩盖)。”

这种职业化的标准化表现让她看起来与同事无异,但内心承受着巨大的情绪劳作。
“跟同事说话就很累,”她坦言,“我觉得我想说的别人不明白,别人说的我也不明白”,与人沟通总隔着一层。
更具体的表现是,她不知道别人的笑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自己应该什么时候笑,但是她会排练出一种“笑”的表情和一套动作来,以便随时应对各种社交场合。
下班后,疲惫不堪的她选择了完全社交隔离。周末不出门,在家一直玩游戏,她喜欢一字一句地看角色对话,或者重复观看自幼就喜爱的动画系列作品。这已是她努力维持的状态。除了非常包容她的丈夫,她没有朋友。
身体层面的困扰更是从未停止。睡眠问题从小伴随她至今,“对光和声音敏感,每天都会睡不好,一直做非常焦虑的梦”。
更困扰的是那些无法确诊的身体小毛病。“我一直肠胃就不好,但怎么都诊断不出来是什么。”作为女性,生理周期的不规律也增加了她的困扰,“不知道下一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只能随时准备着。
日常生活必须严格按照固定模式进行。比如,必须中午12点左右吃午饭,否则“胃就不舒服,马上影响心情,头晕、头疼乱七八糟的都开始了”。
这种对确定性的需求让她无法灵活社交,“可能大家出去玩都挺开心的,但我必须要在中午12点吃午饭,这就很难做到。”
而职业野心与现实的冲突让她更加痛苦。她不愿意像大多数ASD人群那样“转向一个不跟人有接触的职业”,而是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她想要追求管理层的发展目标。
但现实残酷,她现在带团队就已经沟通不畅,每天都很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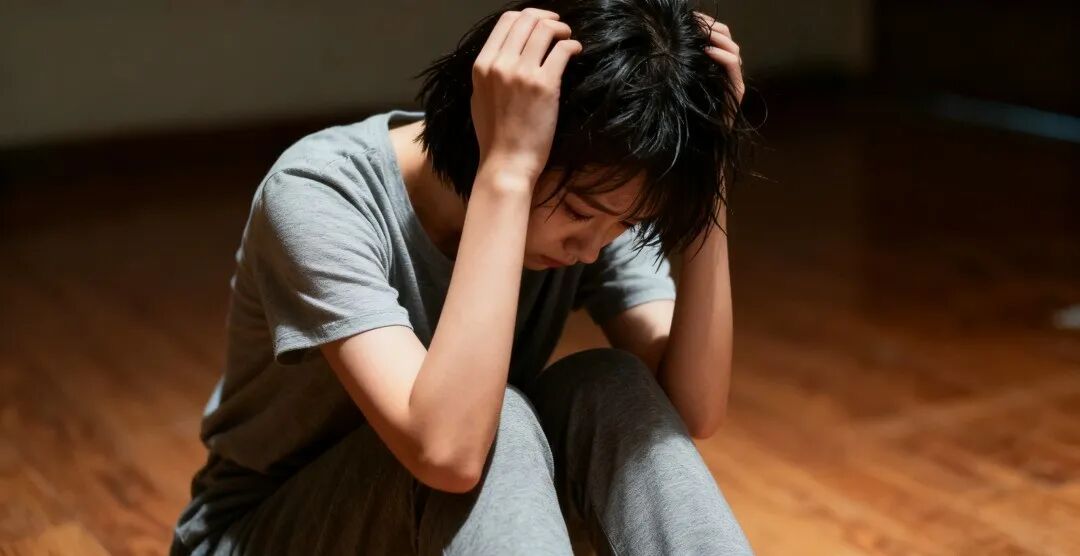
工作中的困难再次体现在细节执着上。“比如说一个项目,我会觉得某一个细节是很重要的。”但同事们经常提醒她“不要纠结那些东西,那些东西不重要”。
这让她陷入双重消耗,“白天我尝试按别人的思考方式,晚上我自己去纠结那些细节。”
面对困境,小云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解决方案。她坦诚告诉老板自己的诊断,获得了更多理解和支持,也参加过当地的ASD支持课程。
对于其他处于相似困境的ASD成年人,小云建议:“最重要的就是不断了解自己。市面上的经验都不适合,你只能自己探索一条路出来。”
而这条路注定孤独而艰难,但她选择继续探索。

1,关于个体差异:
每个ASD人士的经历都是独特的,请避免刻板印象。本次访谈对象不能代表整个ASD群体,也不要将本文视为ASD人士的标准模板。ASD谱系很宽广,每个人的表现和需求都不同。
2,小云补充:
“我知道由于ASD的特殊性,我试图传达的感受永远不代表我个人的真实感受。
“我只能是尽力试着传达,但我觉得语言本身十分匮乏,文字也不能反映一个人或群体的经历和思考,思考过程也无法加进稿子,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曲解。
“此外,我大概率是双A,也就是自闭症和ADHD共患。所以会展现出更多的特殊性。只是我在ASD诊断后,并没有继续去寻求ADHD的诊断。”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