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五的晨光像一柄钝刀,缓慢地劈开窗棂上的冰凌。画室里的水彩盘凝着薄霜,我呵开白气,在瓷碟边缘调出第一抹赭石色——这该是佛像袈裟的底色。窗外,村庄的炊烟正与雪雾缠绵,而画中的莲台已悄然浮出水面,仿佛从冰湖里打捞出的月光。

"佛像的眉目要留白,像腊月的雪地。"母亲的声音从厨房飘来,混着熬粥的咕嘟声。她总在腊月念叨这些旧事,仿佛记忆是陈年的糯米,越到寒冬越要蒸腾出香气。我蘸取群青,在宣纸上晕开佛光的轮廓,水色在纤维间游走,像幼时在冰面滑行的木陀螺。那时外婆说,腊月的佛像是"冻出来的慈悲",如今想来,这该是水彩在寒冬特有的凝滞与温柔。

画中佛像的右手已现出雏形,掌心向上的姿态让我想起村口那尊石佛。去年腊月,我曾用冻红的手指触摸过它,石缝里渗出的水珠在指尖结成冰晶,与此刻画中佛光边缘的霜花何其相似。我添上钛白,画衣褶间的明暗,颜料在低温下干得极慢,每一笔都像在雪地里跋涉。母亲端来姜茶时,我正用细笔勾勒璎珞,她鬓角的银丝与画中佛冠的流苏竟在某个瞬间重叠。

"腊月画佛,要画它破冰的模样。"母亲忽然说。这让我想起旧时庙会,腊月的佛像总要裹上棉被,怕冻裂了金身。而此刻画中的佛陀,正从水色中缓缓浮现,仿佛是从冰湖里打捞出的暖阳。我调出藤黄,画莲座的纹路,颜料在瓷碟里结成细小的冰渣,用笔尖碾碎时发出细微的脆响,像佛前供果被风干的声响。

画至佛眼时,我用了最淡的墨色。这双眼睛该是腊月特有的慈悲——不似春日的明艳,不似夏日的炽烈,而是像冻湖下的暗流,在冰层下无声涌动。母亲收拾画具时,一枚铜钱从她袖中滑落,那是她总在腊月初五用来卜卦的"佛钱"。铜钱在画纸上滚动的轨迹,竟与画中佛光的晕染方向暗合,仿佛命运早已在寒冬中埋下伏笔。

暮色渐沉时,佛像已具足庄严。我添上最后一笔朱砂,画佛唇间的微笑,这抹红在灰白画纸上格外醒目,像雪地里突然绽放的野梅。母亲将铜钱压在画纸一角,说这样能"镇住画中的佛气"。我忽然懂得为何古人要在腊月画佛——那凝滞的颜料、缓慢的晕染、与寒冷对抗的创作,本身便是对慈悲最虔诚的摹写。

夜深,画上的水彩开始呼吸。佛像的衣褶间渗出细密水珠,在宣纸上结成霜花。母亲睡去后,我独自守着这幅画,看佛光在夜色中流转。腊月的佛像是特殊的,它不似其他时节那般金碧辉煌,而是带着水彩特有的朦胧与温柔,像冻僵的手指在暖炉边慢慢舒展。

晨光再次漫过画纸时,佛像已完全干透。母亲用铜钱轻叩画框,说这是"唤醒佛光"。我望着画中佛陀,那抹朱砂红在晨光里愈发鲜艳,仿佛腊月最凛冽的寒风,也冻不住慈悲的温度。腊月初五的大寒终究会过去,但画中这尊水彩佛像将永远鲜活在雪色里——当最寒冷的时节遇见最温柔的窗,便有了破冰而出的佛影,在人间烟火中静静融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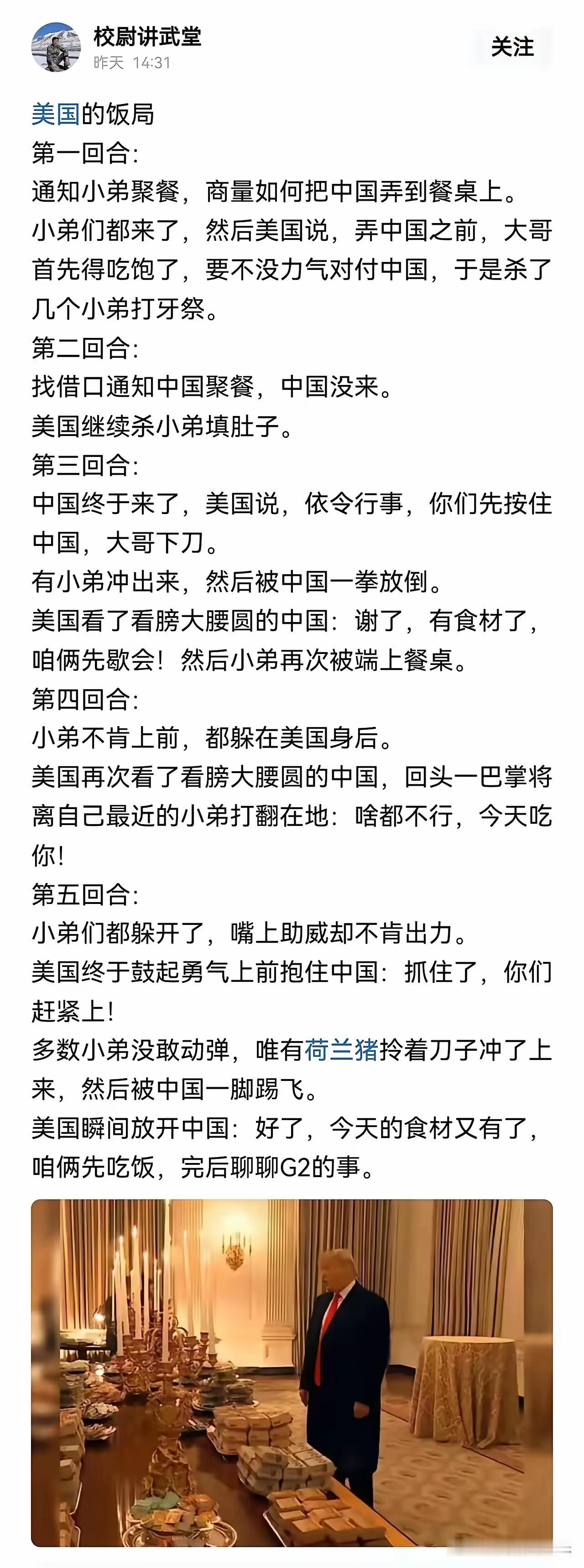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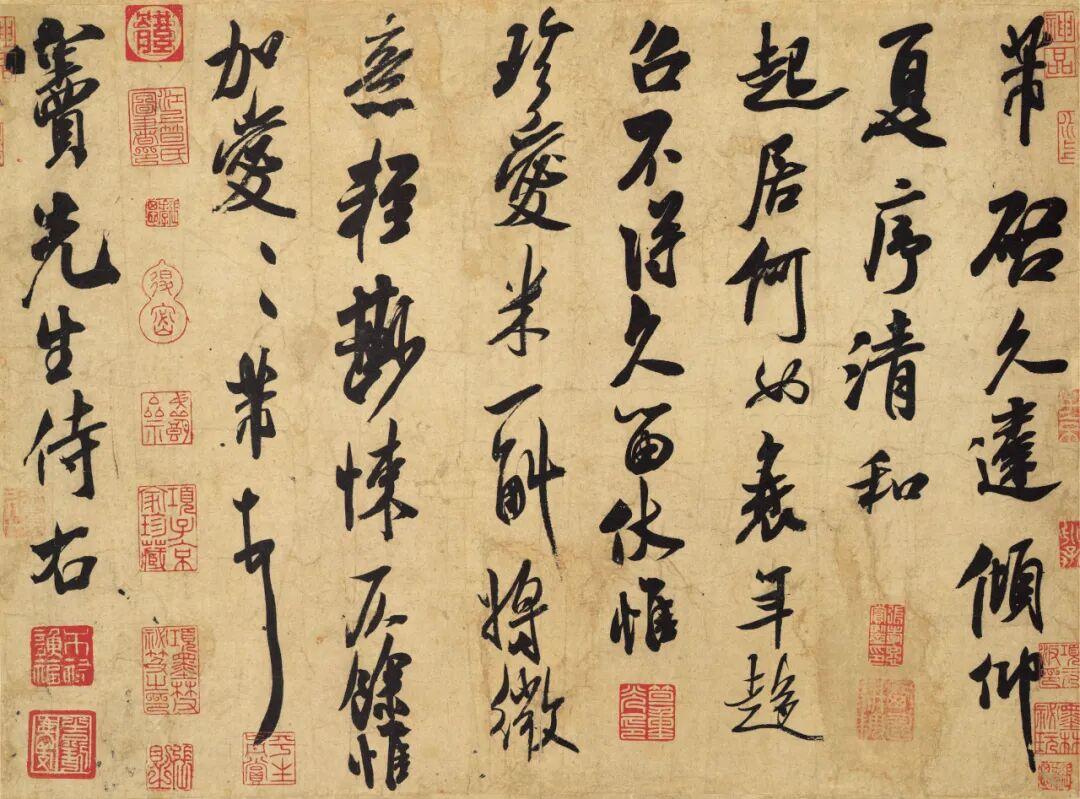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