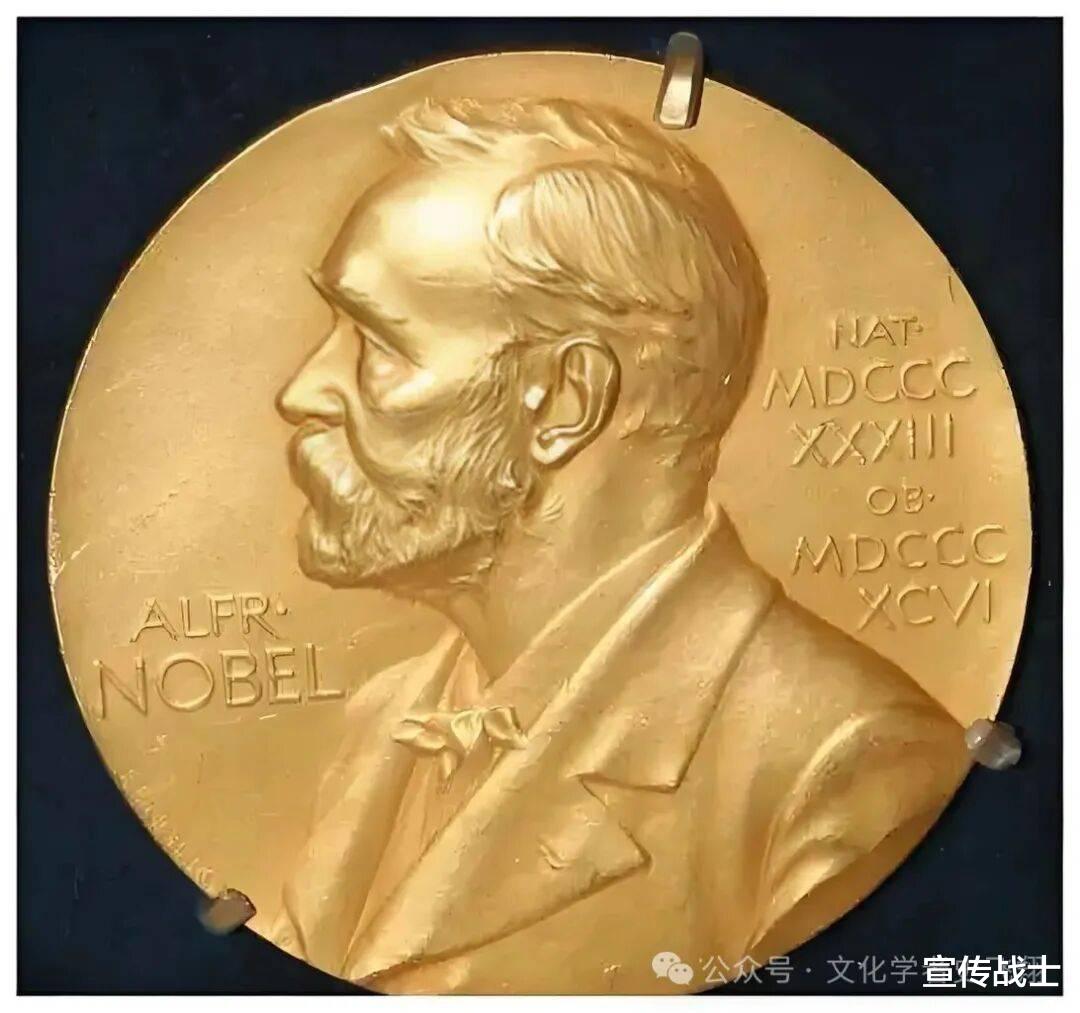
再过几小时,万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就要揭晓了。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夕,全球文学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于斯德哥尔摩,而在中国,这场文学盛典更像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仪式。当倒计时的钟声临近,无数人屏住呼吸、翘首以盼,猜测着“文学王冠” 究竟会花落谁家。这种近乎狂热的关注,背后折射出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自1895 年设立以来,在中国社会心中沉淀百年的复杂情感——它既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萦绕心头的 “情结”,更是一段难以释怀的 “郁结”。从早年的翘首以盼却屡屡落空,到 2012 年莫言获奖时的举国欢腾,再到如今逐渐回归理性的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互动史,俨然成为一部浓缩的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史。
2012 年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当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时,整个中国都沉浸在 “一雪前耻” 的喜悦之中,仿佛多年的文化夙愿终于得以实现。彼时,舆论场上一片欢呼,有人将其视为中国当代文学 “走向世界” 的终极证明,有人认为这标志着中国文学终于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就在这样的热烈氛围中,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一篇题为《莫言获诺奖,国人应冷静》的文章发表于《西安晚报》与《杂文月刊》。我在肯定莫言获奖是“好事”“喜事” 的同时,不无忧虑地指出:“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当代文学立刻就达到了世界水准。中国当代文学距离世界文学尚有差距,中国作家仍须努力。”这番观点在当时的网络语境中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泼冷水”,是对中国文学成就的否定;但如今回望,这番话恰恰戳中了中国文学在诺奖情结裹挟下的核心问题 —— 我们是否过度将诺奖视为衡量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应当回到近一个世纪前,聆听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先生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1927 年春,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来华考察时,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先驱刘半农商议,计划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随即托学生台静农给鲁迅写信,征询其意见。彼时的鲁迅正身处广州西堤的寓所,焦急等待前往上海的船票,但他仍迅速回复了这封信。在信中,鲁迅的态度清晰而坚定:“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这封信堪称中国文学史上关于“诺奖态度” 的经典文本,它不仅展现了鲁迅作为文人的谦逊与清醒,更蕴含着深刻的文学理性与民族自觉。首先,鲁迅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阶段有着精准的判断——他深知当时的中国新文学刚刚摆脱古典文学的桎梏,在思想深度、艺术手法与世界文学的对话能力上仍处于 “起步阶段”,距离世界文学的成熟尺度尚有巨大差距。这种对文学发展规律的尊重,让他拒绝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也避免了将个人荣誉与国家文学地位简单捆绑。其次,鲁迅对文学创作的纯粹性有着极致的坚守——他担心一旦接受诺奖,“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在他看来,文学创作的核心是对现实的关注、对人性的探索,而非对荣誉的追逐;若被诺奖的光环所束缚,轻则失去创作的锐气,重则沦为 “御用文学”,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绝不能容忍的。最后,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洞察可谓一针见血——他警惕 “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 的 “特殊照顾”,更担心这种 “优待” 会助长中国人的 “虚荣心”,误以为中国文学已能与世界顶尖水平比肩。这种对 “文化自尊” 的坚守,远比单纯获得一个奖项更为珍贵。
在鲁迅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界仍有不少作家延续了这种理性态度,陈忠实先生便是其中的代表。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时,这位以《白鹿原》震撼文坛的作家平静地回答:“我从不考虑这个问题。诺贝尔文学奖奖给中国当代任何一个作家,我都不吃惊。不但不吃惊,反而替他高兴,并由衷祝贺他。” 这番话没有刻意的谦卑,也没有功利的渴望,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平和与通透。在陈忠实看来,诺奖只是一个国际文学奖项,它有自己的评选标准、价值取向,甚至可能存在文化差异带来的认知偏差;作家的核心任务不是“求奖”,而是 “创作”——只要能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品,无论是否获得诺奖,都能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这种 “平常心”,恰恰是对鲁迅文学精神的传承,也是中国当代作家应对诺奖情结的最佳姿态。
古人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对待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之所以需要保持 “平常心”,本质上是因为文学价值的多元性与诺奖评选的局限性之间存在天然的张力。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中,“具有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 这一表述本身就带有主观色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立场的评委,对 “理想倾向” 的理解必然存在差异。例如,西方评委可能更关注文学作品中的个体意识、现代性反思,而中国文学传统中更强调的 “家国情怀”“民生关怀”,有时未必能完全进入其评价视野。此外,诺奖的评选还受到翻译质量、文化传播力度、国际文坛话语权等诸多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因此,一部作品能否获得诺奖,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文学水准,还与诸多外部因素相关。若将诺奖视为中国文学 “走向世界” 的唯一通道,或将其作为衡量作家成就的绝对标准,无疑会陷入 “唯诺奖论” 的误区,进而忽视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与独特价值。
当下,中国当代文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机遇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走向世界舞台;数字媒体的发展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载体与传播路径,网络文学、跨界文学等新形态不断涌现,丰富了文学的生态。但从挑战来看,中国当代文学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部分作家缺乏对现实的深度关注,要么沉溺于个人化的情感宣泄,要么陷入对西方文学的简单模仿,难以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经典作品;二是文学评价体系仍不够完善,市场逻辑与流量思维对文学创作的干扰日益加剧,一些作家为追求商业利益,放弃了文学的审美追求与思想深度;三是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中国文学仍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不少作品在国际传播中因文化差异与翻译问题,难以被准确理解,进而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国际认可度。
面对这样的现状,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究竟在何方?答案或许就藏在鲁迅与陈忠实的态度之中——以理性破除诺奖情结的桎梏,以自信坚守中国文学的民族根基,以创新推动文学与时代的同频共振。具体而言,首先,作家应回归文学的本质,坚守 “为人民写作” 的初心。文学不是象牙塔中的自娱自乐,而是对时代的记录、对人性的探索、对精神的引领。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需求,才能创作出具有生命力的作品。莫言的成功,恰恰在于他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故事,让世界通过他的作品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苦难与坚韧、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
其次,中国文学应在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话语体系。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古典文学中的“意境”“风骨”“比兴” 等美学传统,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智慧;而现当代文学中,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开创的 “现实主义” 传统,也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我们不应盲目排斥西方文学,也不应简单照搬西方的文学范式,而是要将西方文学的创作技巧与中国的文化语境、审美传统相结合,创作出既具有国际视野,又充满中国韵味的作品。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既借鉴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元素,通过对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百年兴衰的描写,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碰撞与传承,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巅峰之作。
最后,我们应构建更加多元、开放的文学评价体系,减少对诺奖等国际奖项的过度依赖。文学评价不应只有一个标准,而应兼顾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等多个维度;既关注作品的文学价值,也关注其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同时,我们应加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培养更多优秀的文学翻译人才,搭建更多中外文学交流的平台,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也让中国文学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学的大家庭。唯有如此,中国当代文学才能真正摆脱诺奖情结的束缚,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发出属于中国的声音。
诺贝尔文学奖终究只是一个奖项,它可以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桥梁,但不应成为束缚中国文学发展的枷锁。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是否获得诺奖,而在于它是否能记录这个时代,是否能滋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否能为世界文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正如鲁迅所说,中国文学的进步,需要的是作家“还欠努力” 的谦逊与坚持,需要的是整个社会对文学的理性看待与真诚支持。当我们不再以 “诺奖得不得” 来评判中国文学的成败,当我们能以平常心看待国际奖项,以自信心坚守民族文学的根基,以进取心推动文学的创新发展,中国当代文学才能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才能在世界文学史上书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