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八年不上朝,埋下大明覆亡的百年祸根?崇祯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前,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下:“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但历史学者黄仁宇却指向前朝:万历皇帝的怠政,早已为大明埋下了“定时炸弹”。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紫禁城传出了沉闷的丧钟。在位48年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终于走完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当大臣们打开他的陵寝——定陵地宫时,一个细节令人深思:许多陪葬品制作粗糙,明显是仓促赶工。连皇帝的葬礼都如此敷衍,这个王朝的运转机制已经出现了怎样的问题?
而24年后,当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崇祯皇帝至死都不明白:为何他“夙夜焦劳,励精图治”,却无法挽回大明覆亡的命运?答案或许要从他祖父的祖父——那位近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说起。

万历十七年(1589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道震惊朝野的奏疏,直指皇帝“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皇帝的反应是——从此开启了长达近三十年的“不上朝”纪录。
表面上,万历只是躲在后宫;实际上,他开启了一种“选择性理政”模式:对自己有利的事(如征收矿税)异常积极;对国家社稷有利的事(如边防、赈灾)则能拖就拖。
万历中后期,中央六部尚书、侍郎缺员达三分之二,地方督抚也大量空缺。官员的任免、升迁、考核几乎停滞,整个官僚体系陷入了空转状态。这好比一家公司的CEO长期不上班,部门主管位置空着一大半,公司还能正常运转吗?
更可怕的是,这种怠政模式被制度化地传承了下去。泰昌皇帝在位仅一个月,天启皇帝沉迷木工,崇祯虽然勤政却刚愎自用——万历开启的“皇帝不作为”传统,成为明后期政坛的顽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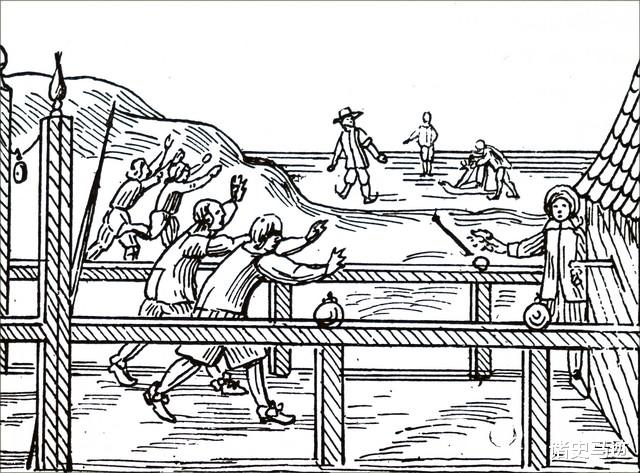
万历前十年,实际上是张居正的时代。这位明代最杰出的改革家推行“一条鞭法”,整顿税收,使太仓存银从不足维持三个月增加到可支十年。
但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不仅抄了张的家,更全盘否定其改革措施。“考成法”被废,“一条鞭法”虽保留但已变形。最核心的是,张居正建立的财政管理体系被彻底破坏。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精辟指出:明朝财政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数字化管理。张居正试图建立一套有效的税收和审计体系,但他死后这套体系就瓦解了。到万历后期,朝廷甚至不清楚全国到底有多少田地、多少人口、能收多少税。
这种财政混乱在辽东战事中暴露无遗。当努尔哈赤崛起时,兵部请求拨付辽东军饷,户部却拿不出钱。太仓库在万历三十八年时存银仅8万两,而一场中等规模的战役就需要数十万两。皇帝自己的内帑(私人金库)却堆满了从全国搜刮来的矿税银子。

万历时期有过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史称“万历三大征”。表面上看,明军都取得了胜利,但这背后是国力透支的巨大代价。
仅朝鲜之役(15921598年),明朝就花费了约1000万两白银,这相当于当时全国两年的财政收入。战争虽胜,却埋下了三个隐患:
第一,辽东军事力量被削弱。精锐部队调往朝鲜,辽东防务空虚,为努尔哈赤崛起创造了条件。
第二,财政体系彻底崩溃。为筹措军费,朝廷不得不增加税收,而增加的税负大多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导致民怨沸腾。
第三,军事改革停滞。战争胜利给了朝廷虚假的安全感,错过了改革军事制度的最佳时机。明军依然沿用落后的卫所制,而女真已经建立起更有效的八旗制度。
黄仁宇评价:“‘三大征’的胜利,掩盖了明朝军事、财政制度的根本缺陷,就像给一个重病患者打了兴奋剂,表面精神了,内在的疾病却在恶化。”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一个荒诞的决定出台了:皇帝派遣太监到全国各地开矿收税。这些“矿监税使”如蝗虫过境,所到之处民不聊生。
在湖广,税使陈奉“剽劫行旅,恣行威虐”,引发民变十余次;在山东,税使马堂的爪牙在临清一天之内逼死三十余人;在云南,税使杨荣随意抓捕平民,指其为盗矿者,勒索赎金。
这些矿税大部分进入了皇帝的私人金库。据不完全统计,万历二十五至三十三年,各地矿监税使进奉内库的银子就达三百余万两。而与此同时,太仓(国库)年收入仅约400万两,却要承担全国的行政、军事开支。
皇帝与民争利,造成了三个致命后果:一是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激化;二是官僚体系分裂,正直官员被排挤;三是中央财政与皇室财政混淆,国家治理失去理性基础。万历的这种短视行为,为明末农民起义埋下了火种。

万历朝是明代党争的起点。张居正时代就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张居正死后,朝臣分裂愈演愈烈;到万历后期,形成了东林党、浙党、齐党、楚党等多个政治集团。
党争的焦点之一是“国本之争”——关于立太子的问题。万历想立宠妃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而大臣们坚持“立长”原则,要求立宫女王氏所生的朱常洛。这场争论持续了十五年,最终以万历妥协告终,但消耗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加剧了君臣对立。
黄仁宇指出:明朝的政治制度缺乏解决重大分歧的机制。当皇帝与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内部出现矛盾时,没有有效的仲裁和妥协机制,只能通过无休止的争论和相互攻击来解决,这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
更严重的是,党争从政见之争演变为意气之争、利益之争。到天启年间,魏忠贤利用党争打击东林党,制造了“六君子案”“七君子案”等冤狱;崇祯时期,党争依然激烈,君臣之间、大臣之间互相猜忌,难以形成合力应对危机。

万历时期,明朝军事制度的深层问题已经暴露无遗。
表面上看,明朝有数百万军队(理论上),但实际上,卫所制度早已崩溃。军户逃亡严重,部队缺额普遍在一半以上;军官克扣军饷,士兵衣食无着;训练废弛,装备落后。
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曾说过:“我军十不当倭一。”他虽然建立了一支有战斗力的戚家军,但这只是特例。张居正死后,戚继光被贬,戚家军也逐渐解体。
在辽东,李成梁父子虽然多次击败蒙古、女真,但他们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的策略:扶持听话的部落,打击不听话的。这种策略短期有效,却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创造了条件——李成梁打击了努尔哈赤的对手,客观上帮助他扫清了障碍。
更致命的是军事思想的落后。明朝将领大多不知近代战争已发展到火器为主的时代,仍迷信骑兵冲锋。萨尔浒之战(1619年),明军总兵力约11万,其中火器部队占比不到三成;而后金军虽然总兵力只有6万,但骑兵机动性强,战术灵活。此战明军惨败,从此辽东局势彻底逆转。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明朝的灭亡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制度性、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万历朝正是这些问题集中爆发的时期。
从“大历史观”看,明朝的问题在于:
第一,财政税收制度的落后。明朝始终没有建立像唐宋那样完善的中央财政体系,税收主要依赖农业,商业税征收不力。到万历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达,这种落后的税制已经无法适应时代需求。
第二,法律与道德的混淆。明朝政治过于依赖道德教化,缺乏明确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官员们热衷于道德争论(如“国本之争”),却忽视了实际政务。
第三,数字管理的缺失。明朝政府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决策往往基于经验和直觉。张居正曾试图改变这点,但他死后改革中断。
第四,上下层社会的脱节。朝廷高层的政治斗争与基层社会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皇帝和大臣们争论该立哪个太子时,陕北农民正因为连年干旱而吃不上饭。
黄仁宇指出:“万历的怠政,只是表象;更深层的是整个帝国管理体系的失效。”当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近三十年不上朝而国家还能勉强运转时,恰恰说明这个国家的治理已经出现了系统性问题——它不再依赖于领导人的英明决策,而是依靠惯性在滑行。而当惯性耗尽时,崩溃就不可避免。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时,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崇祯皇帝的私房钱(内帑)只剩下区区几千两银子,而万历皇帝留下的内帑早已被挥霍一空。这个细节仿佛是历史的讽刺——最贪财的皇帝留下了空虚的国库,最勤勉的皇帝却无力回天。
万历皇帝躺在定陵的地宫中,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他的“懒惰”不仅仅是个人的性格缺陷,更是一个制度走向衰亡的征兆。他那些看似任性的决定——不上朝、征矿税、拖延立太子——就像一颗颗钉子,钉在了大明王朝的棺材上。
黄仁宇说得对:崇祯不是明朝灭亡的第一责任人,他只是一个不幸的继承者,接手了一个已经被蛀空的帝国大厦。而当大厦将倾时,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显得徒劳。万历埋下的“定时炸弹”,在崇祯十七年准时爆炸——这不是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明朝的灭亡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衰败,往往始于制度失灵;而制度失灵,往往始于最高层的失职。 万历皇帝的“懒政”不只是个人的懈怠,更是一个庞大帝国管理系统的全面失效。当皇帝可以二十八年不上朝而国家还能“正常运转”时,这个“正常”本身就是最大的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