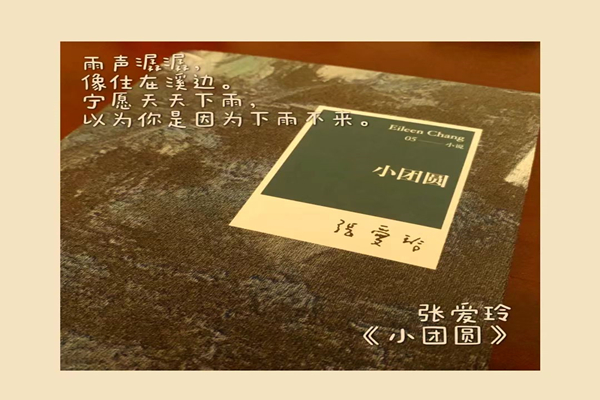
文/王栩
(作品:《小团圆》,张爱玲著,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
九莉就像站在一座古建筑的门口朝里看,门内早已不再金玉满堂、美轮美奂,而是覆落一地的断瓦颓垣、朽木衰草。门内的破败景象用不着一一览过,细细端详,“一瞥间已经知道都在那里”。
那便是九莉挥之不去的记忆,灰暗又阴郁。最为明亮的也不过很少的一捧,捧出九莉一个别样的童年。那是何等的别样?“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背诗,触动了做过总督的二大爷悄悄地拭泪。泪光闪闪,闪现出豪门巨族的颓势。家族的一个分支仍然恪守重于泰山的宗族观念,在时代变迁下遵循旧日的生活轨迹。可败絮如疾风对家族的席卷势不可挡。
九莉的童年在席卷而至的败絮中悠游逍遥,有着少有的快乐。女佣、男仆、门房,他们充当九莉的玩伴,给了女孩一个辽远的眼界和精到的认识。得益于心性的纯粹,有效地摒除了豪门中人同虚荣搭界的浊气,着眼于九莉,她能语出清新地护着爱老三,“‘我倒觉得她好看’”。卫护被父亲抛弃的情妇,出于一个女孩的口不会搅乱人心,看不起爱老三的仍然会看她不起。只是,没人会懂得,自由和纯粹在童年的九莉心里埋下了一颗生机盎然的种子。
这颗种子经受的土壤贫瘠,世间凉薄的气候催生了它的敏感与天性的闲散。九莉把童年比作一个梦,却又疑心梦的可靠。这模棱两可的认识让童年的记忆轻盈,在她将其捧出,用文字赋予其生命的气息时越发珍重。除了童年,那些大段大段的回忆构成了针刺般异常疼痛的往事。它们不像轻烟易于飘散,它们顽石块垒般压进沉郁的文字,皆是触目伤。
“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奶奶生前仅有的一首集句里预言性的先声,道出了日落西山的悲凉。长大了的九莉朝一座古建筑的门里看去,悲凉落满她的肩头。她不是在承受,而是担负了记忆的重量。长大,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当争吵充塞耳内,九莉知道了“‘你不喜欢的人跟你亲热最恶心’是说她父亲”。带着对九莉父亲的厌恶,九莉的母亲奔向了自由。
九莉的回忆里,母亲的情史厚重,若以常论,难免惊吓了世人。但它们的发生,皆在蕊秋争得自由身后。比之藏于豪门断瓦颓垣下的龌龊,“九莉一直以为蕊秋是那时候最美”。美与龌龊交替出现在九莉的回忆,并未厚此薄彼的加以掩饰。九莉自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目睹或是耳闻高门大院里的种种情事,它们无一自由,也就跟丑恶相类。
捻住了情事这根敏感的线头,循根循迹地梳理,钱,无异于成了大家族中人日常闲谈的要紧事。轻言悄语,张罗着九莉听不懂的话。话里的隐忧,无非世情。九莉能听懂的,莫过于大考,它是九莉的隐忧,不通世故即是闲散之人心性上的要害。
因为太过纯粹,九莉照实搬出回忆里的丝丝缕缕。连她在香港读教会学校时,“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也用文字记录的令人心悸。豪门世家的破落藉由这样的记录,沧桑得无所遁形。不通世故的九莉不去思虑自揭疮疤给他人的恶感,她的心性高尚,她的事业便也无可挑剔。
闲散的性子不会在意他人的妄议,这一点,九莉同蕊秋挺像,她们都爱自由,却各有殊异。蕊秋爱得热诚,爱出了掌控自由的力度,直到色衰颜败,老到不行了。九莉不然。她自由的去爱,遇见妄议自己的邵之雍,自由一途成了囚笼,推着她拼命地转化,陷入一个喜之悲之的境况。那个境况有着童话般的韵味,她从未如此的把自己彻底打开,疯长成一棵树,在邵之雍窗前的灯光里开满一树的小花。活在童话世界,她的转化是喜悦的。现实世界,自由给了她作茧自缚的一击。她繁花满树,却只能在邵之雍的窗外窥视。一心渴求欣赏,终至无处安放。她的悲哀,自渡亦是绝路。
人言藉藉,九莉如何自渡。日本投降,满街的炮竹声里,九莉都能安然入睡。她不关心大事小事,她只关心能否和邵之雍在一起。这样的关心形诸于回忆的文字,又是会惊吓到世人的争议性记录。难怪九莉会将母亲的认识保存下来,“蕊秋常说中国人不懂恋爱,‘所以有人说爱过外国人就不会再爱中国人了。’”单纯地谈爱,邵之雍办不到。做过汪政府的官,日本投降后,邵之雍带着小康姑娘去乡下避难印证了“讲古”里的中国人风流渊薮的恋爱观。那样的恋爱观比照豪门巨族里按照大排行一字儿排开的大小姨太太们,以及她们和各房表少爷、侄少爷的情事,又是跟丑恶相类的回忆。
回忆中的九莉未能免俗。邵之雍在报上连续登了两份声明,同两个太太离了婚。九莉写下了邵之雍的凄楚,写出了她崇拜的邵之雍未失风度的难受。她换来的,一纸婚书,作为“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慰藉。她看重这份慰藉,并像所有未能免俗的中国女人那样对邵之雍谈论小康姑娘有了猜疑。当九莉把猜疑解释成自己的曲解,她的眼界与认识已卑微到女性“三从四德”的礼教层面。
在弃与被弃的夹缝间,对九莉而言,摊牌是一个未能免俗的女人最后的攻势。组织好的攻势毁于邵之雍的谈笑,一句“要选择就是不好”断绝了九莉的信心与期待。他们的分手像是一场今生的约定,用等待而非告别在时间长河里预埋再次相逢的机缘。他们给那个机缘要等多久设下了一个限定,“永远”,这个充满理性色彩又温和尚礼的词记下了始乱终弃的邵之雍伪君子的面目,记下了为爱而把自己俯得很低的九莉强作欢颜的伤悲。
别了邵之雍,燕山填补了九莉情感上的真空,他带给九莉初恋的感觉。作为只有一次的初恋,九莉更觉这晚来的补偿值得“凄迷留恋”。这般况味关乎未曾言说的哀叹,富贵浮云,真爱成灰,它们同伤痕遍布的往事一道在指缝间流掉了。如此的心绪下,“掬水月在手”是悲情,是两手空空的预见,更添“凄迷留恋,恨不得永远逗留在这阶段”的份量。
期待美好,光阴残酷。九莉用冷水浸脸,使皮肤紧缩,延缓女人色衰的过程一一展开,再一次未能免俗的她回复了小女人的本色。可她仍是孤身一人,晚来的对初恋的补偿无疾而终。她不怪谁,只怪下了许多天的雨。她不去指责多雨而阴湿的季节,她用柔美的文字移除因失诺而致的悲酸,独自在泪水的流淌中攒下惯常的落寞。“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她习惯了这样的沉重,却从心底把它倒出的轻细。
轻细是九莉倒出过往回忆时心力的呼应。她不是在回忆中构建大厦。她的回忆并不光鲜,徒剩华丽的幻象。当幻象生成的迷雾散尽,遗下的,荒凉的废墟。那即是九莉朝门里一瞥,见到的一切。一切都不美好,就连等待也成了她梦里恐怖的一幕。她还是要轻细地把一切倒出来。如果团圆是一生的句号,她用唯一的一次对邵之雍的梦见,给回忆作结,打上了象征团圆的句号。那个梦里,他们仍然相爱。
2025.11.7
——文中图片为网络配图,与正文内容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