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姬明,在周朝做了十余年司寇,管的就是刑狱司法这档子事。现在的打工人天天喊“工资月光”,可你们知道不?三千年前我当周朝卿大夫那阵,国君给的“工资”,不仅能养全家、雇仆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这工资既不是银子也不是铜钱,全是粮食和一块实实在在的田地。你肯定要问了:靠粮食当工资,难道不怕放坏?这里面的门道,可比现在的薪资条复杂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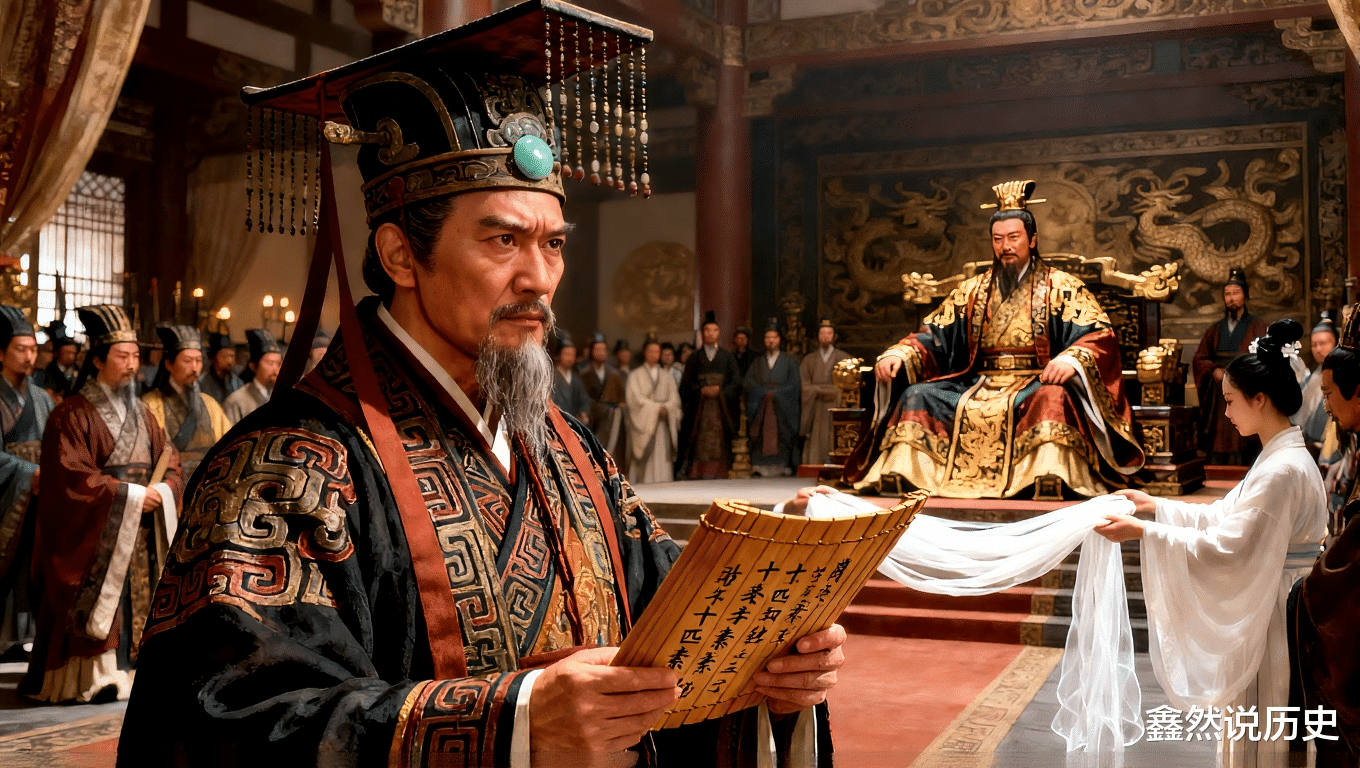
先说说我们卿大夫的“基本工资”——“禄田”。估计不少朋友搞不清卿大夫和司寇的关系,我用大白话解释下:卿大夫是周朝官员的等级,就像现在的“管理层”,在诸侯下面、士人上面,算是朝廷的核心人物;而司寇是具体的官职,管刑狱司法,我就是以卿大夫的身份,干着司寇的活儿。说白了,卿大夫是我的“身份级别”,司寇是我的“具体岗位”。
国君会按官职大小赏田地,我这司寇不算小,分到了一百亩“上田”——就是土壤最肥沃的那种。这田不用我自己弯腰种,有专门的“庶人”替我打理,每年收成的八成,都得乖乖送到我家粮仓。别小瞧这一百亩地,按现在的粮食产量算,一年能收两万多斤粟米,够二十口人的大家庭吃一整年,温饱是绝对不愁的。
除了禄田这份“固定工资”,还有“绩效奖金”——就是祭祀后的祭品和朝会时的赏赐。上个月祭祀先祖,仪式结束后国君大手一挥,赏了我半头太牢(也就是公牛),这在当时可是顶好的东西!要知道,普通士人一年到头都未必能闻着肉香,我家连仆人都跟着开了荤,个个喜笑颜开。
还有一回朝会,我提了个整治市集盗窃的法子——既治得了小偷,又不至于量刑太重,合情合理。国君听了特别满意,当场就赏了我十匹“素纱”。我妻子拿到手眼睛都亮了,立马找了城里最好的绣娘,做成了一套礼服。后来穿去参加贵族宴会,不少大夫的夫人都围着问在哪弄的,那叫一个有面子!

不过这“粮食工资”也有糟心事,我家管家天天跟我念叨。夏天雨水多,粮仓里的粟米潮得很,稍不留意就发芽发霉,得雇人天天翻晒;要是遇上灾年,地里收成差,不仅仆人的“工资”(也是粮食)发不出,更头疼的是封地的庶人要饿肚子——这对我这司寇来说可不是小事,饥民多了就容易出盗案,刑狱案子堆成山,我能愁得睡不着觉。
就说去年冬天,特别冷,封地的庶人张三揣着冻得硬邦邦的窝窝头,带着老婆孩子来我家求情,孩子饿得当街哭,小脸冻得青一块紫一块。我看着实在不忍心,让管家给了他两石粟米。倒不是我有多心善,实在是心里有本账:庶人是禄田的根本,他们饿肚子了,明年谁替我种地?这就跟现在老板给员工发年终奖一样——都是为了稳住队伍,长远打算。

肯定有人要问了:光有粮食和布料,想买点笔墨、陶罐这些日用品咋办?这就得靠“以物易物”了,相当于现在的“以货换货”。我常让仆人扛着几斗粟米去市集,换些做饭的陶罐、缝衣服的麻线;要是想买青铜剑这种“贵重物品”,就得攒好几季的粮食,跟专门的工匠慢慢磨。
有次我看中了一把工匠打的青铜剑,耍起来特别顺手,结果那工匠狮子大开口,要五十石粟米才肯卖——这可是我三个月的“工资”啊!我攥着粮食账本算了又算,心疼得好几天没睡好,最后还是咬咬牙换了,毕竟司寇出门办事,得有把像样的兵器撑场面。
现在回头想想,那时候的“工资体系”虽然看着原始,却藏着古人的生存智慧。禄田就像现在的“底薪”,保证基本生活;赏赐好比“绩效奖”,干得好多得钱;而“以物易物”的模式,让每一份收入都看得见、摸得着,不像现在,工资就是银行卡上的一串数字,刷起来都没感觉,不知不觉就花超了。
其实历史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制度条文,而是一个个为了生计奔波的普通人。不管是三千年前算计着粮食收成的我,还是现在盯着工资条的你,为生活努力、为日子打拼的样子,从来都没有变过。
话说回来,你觉得周朝卿大夫的“粮食工资”,比现在的月薪制更靠谱吗?要是让你每月领粮食当工资,不用还房贷但得担心发霉,你能接受不?快来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