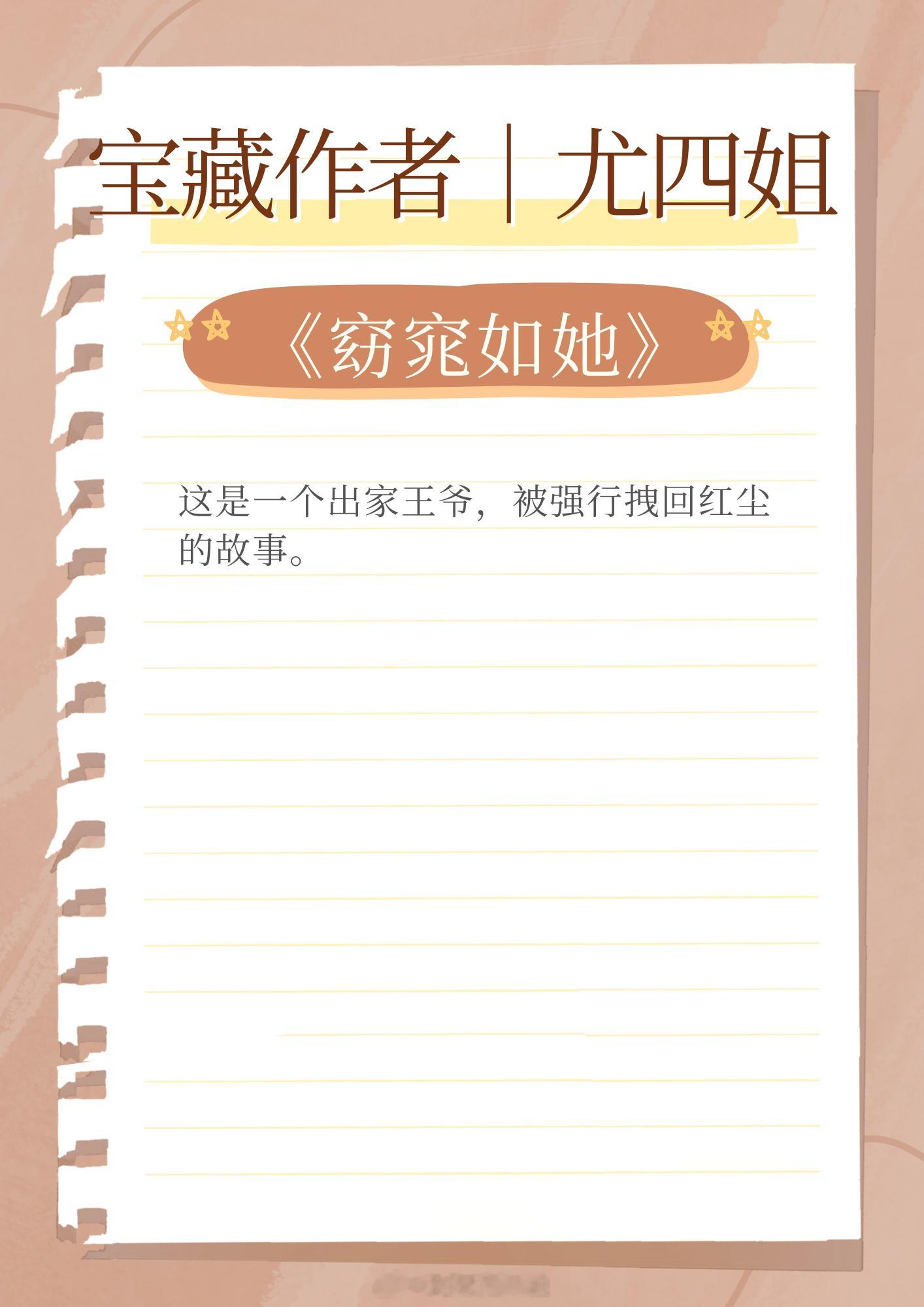我爹亲手将我娘送到了靖国军营。
3个月后,她活着回来了,却成了不言不语的疯子。
宫中所有人都说,我娘是受不了那3个月的折辱,自己疯的。
没人知道,就在她被送走的前一夜,是我摸黑进了她的寝殿。
我用沾了麻沸散的帕子捂住她的口鼻。
将3根浸了药的银针,对准她颅顶的穴位,生生摁了进去。
01
今日是昭阳公主的生辰,整个皇宫都浸在一种虚假的繁荣里,连西边最偏僻的浣衣局,也能听见远处琼华殿飘来的丝竹声。
我正在井边搓洗一堆厚重的宫袍,冰冷的井水冻得指尖发红麻木。
掌事刘嬷嬷像一阵阴风似的刮到我面前,用她那惯常的、带着积年怨气的眼神剜了我一眼。
“陛下传你去琼华殿,给贵客献舞一曲。”
她鼻子里哼出一声冷笑,裙裾扫过门槛时,那句刻薄的话才轻飘飘地落进我耳中。
“也不知叫个窑姐儿生的去做什么,没得脏了贵人的眼。”
我低着头,指尖深深掐进掌心,那点尖锐的疼让我保持清醒。
是啊,我娘曾是艳名动京华的花魁,后来成了君王的婉容,如今又是什么?
我缓缓直起身,望向琼华殿的方向,那里灯火通明,映得半个夜空都亮堂起来。
而我将要去那里,穿着单薄的舞衣,跪在冰冷的地上,取悦那些决定我们母女命运的人。
宴席比我想象的还要奢华,琉璃盏映着烛光,酒香混着龙涎香,熏得人头晕。
我跪在玉阶之下最不起眼的角落,青石板的寒意透过单薄的布料,一丝丝渗进骨头里。
斜前方两个身着锦缎的贵妇,正用不高不低、恰好能让我听见的声音交谈着。
“瞧那跪着的丫头,缩头缩脑的,果真是下贱坯子。”
“可不就是?她娘当年凭着那张脸惑乱君心,如今报应到自己女儿头上了。”
我缓缓抬眼,目光平静地扫过她们精心修饰的脸。
那两人像是被冰冷的蛇信子舔了一下,倏然噤声,不自在地扭开了头。
高台之上,我的父皇,大胤的皇帝,正含笑看着他最宠爱的昭阳公主。
昭阳一身绯红,依偎在父皇身边撒娇,鬓边的明珠步摇晃出细碎的光。
“父皇,儿臣今日舞剑可好?您再赏儿臣一匣子东珠可好?”
“好,都依你。”
父皇的声音温和得几乎能滴出水来,那是我从未听过的语气。
曾几何时,他也曾这样对我娘说话吗?
鼓乐声忽然停了,昭阳公主兴致勃勃地夺过侍卫的剑,旋身跃下高台。
剑光如雪,在她手中绽开,引来满堂喝彩。
就在一片叫好声中,那剑光忽然一转,带着凌厉的破空声,直直朝我的面门刺来!
我想躲,可跪得太久,双腿早已僵硬得不听使唤。
剑尖的寒气几乎要刺破我的皮肤。
“叮——”
一声极清脆的撞击声。
一粒不知从何处飞来的石子,精准地打在剑脊上,长剑脱手飞出,哐当一声落在不远处。
昭阳踉跄后退,又惊又怒地看向石子飞来的方向。
殿角的阴影里,一个人慢慢走了出来。
玄色披风,腰悬短刀,面容在晃动的烛火下半明半暗。
他轻轻抚掌,声音里带着一种玩味的笑意。
“本将竟不知,大胤的公主不仅舞姿动人,剑术也如此了得,差点让本将都开了眼界。”
高台上,父皇的目光这才落到我身上,只一瞥,便冷然移开,仿佛看的是一件碍眼的杂物。
“将军见笑了,小女无状。”
他顿了顿,唇角勾起一丝我看不懂的弧度,转向我。
“贱婢,还不快为裴将军献舞赔罪?”
“贱婢”两个字,像两把冰锥,狠狠扎进我心里。
那个曾经把我抱在膝头,教我念“平安”二字的父亲,不见了。
座上那位裴将军,裴琰,闻言挑了挑眉。
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一双桃花眼隔着晃动的光影望过来,深不见底。
“那就有劳……楚姑娘了。”
他没有像父皇那样称呼我,也没有用任何封号。
他只是叫了“楚姑娘”。
那是我娘给我取的名字,楚安。
她说她不求荣华,只求我一生平安。
可自从三个月前,我和娘被送往靖国军营那一刻起,楚安就已经死了。
我缓缓站起身,腿像灌了铅,一步步挪到殿中央。
乐声再起,我抬袖,旋身,裙裾扫过光滑的金砖。
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踩在过往破碎的梦和冰冷的现实上。
舞跳给谁看呢?
给座上高高端坐、视我如草芥的父皇?
给一脸玩味、不知是敌是友的敌国将军?
还是给这满殿看我笑话,恨不得我再跌得惨些的人们?
裴琰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不是狎昵,而是一种审慎的打量,像在评估一件物品的价值。
舞至激烈处,袖中我亲手缝入的细小银珠,摩擦着皮肤,带来轻微的刺痒。
那里面的药,不会立刻要人性命,只会让人慢慢衰弱,惊悸难眠。
这是我为自己选的复仇方式,缓慢,但确保无人能够逃脱。
舞毕,我重新跪伏于地。
殿内一片寂静,随即响起零星的、敷衍的掌声。
父皇的声音从高处传来,听不出情绪。
“裴将军觉得此舞如何?若将军不弃,便将这婢子赐予将军,斟茶倒水,也算她的造化。”
我的心猛地一沉。
02
昭阳公主立刻尖声叫起来:“父皇!这种女人您也送得出手?她娘是什么货色,满京城谁不知道?”
她转向裴琰,眼中闪着恶意的光。
“将军,您三个月前,不是亲自点名要她们母女去军营的吗?怎么,如今又看上这小的了?”
满殿哗然。
无数道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背上。
裴琰依旧稳稳地坐着,指尖轻轻摩挲着酒杯边缘,仿佛昭阳说的是一件与己无关的趣事。
他的目光越过众人,落在我低垂的头上,幽深难测。
父皇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额角青筋微跳,但嘴角仍勉强扯着笑。
“将军若当真有意……朕,自然没有不允的道理。”
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猛地以头触地,额头重重磕在金砖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奴婢卑贱之躯,不敢污了将军座前!求陛下开恩!求陛下让奴婢留在大胤!”
我的声音带着哭腔,眼泪混着额上沾的灰,狼狈地滴落。
父皇立刻顺势拍案而起,怒道:“大胆!裴将军抬举你,是天大的恩典,岂容你推三阻四?来人——”
“拖下去,重责三十,关入柴房思过!”
侍卫如狼似虎地扑上来,架起我的胳膊就往殿外拖。
我挣扎,哭喊,发髻散了,衣裳也被扯裂。
“父皇!父皇!女儿知错了!求您饶了女儿吧!”
我像个真正的、绝望的少女那样哀嚎。
可高台上的人,再也没有看我第二眼。
只在被拖出殿门,泪眼模糊的最后刹那,我看见裴琰微微举杯,朝我的方向示意了一下。
他的嘴唇无声地动了动。
我看懂了。
他说的是:“不错。”
柴房又冷又黑,只有一道惨白的月光从破窗斜斜照进来。
三十板子打得我后背皮开肉绽,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剧痛。
我蜷在满是灰尘和碎草的泥地上,身体冷得发抖,心里却有一团火在烧。
不知过了多久,门轴发出干涩的“吱呀”声。
昭阳公主披着月白的斗篷,站在门口,金步摇在月光下闪着微光。
她慢慢走过来,蹲下身,用冰凉的指尖抬起我的下巴。
借着月光,她仔细端详我的脸,忽然笑了,笑声又轻又冷。
“仔细看看,这张脸,还真有几分像你那个狐媚子的娘。”
我没有说话。
她继续说着,语气温柔得像在念诗,内容却毒如蛇蝎。
“你知道当年父皇为什么答应得那么痛快,把你娘送去靖国吗?”
“因为我母妃答应他,只要他点头,我舅舅手里的十万边军,就听他的调遣。”
“一个妓子,换十万精兵,多划算的买卖,你说是不是?”
我依旧沉默,只是看着她近在咫尺的、满是得意的眼睛。
然后,我动了。
积蓄了三个月的力气,在浣衣局每日劳作中练就的力气,瞬间爆发。
我反手扣住她抬着我下巴的手腕,猛地向下一拽,同时另一只手如铁钳般扼住了她的喉咙!
她完全没料到我会反抗,更没料到我有这样的力气。
惊愕甚至还没来得及完全浮现在她脸上,整个人就被我带得向前扑倒,后脑重重磕在地上。
我顺势压上去,膝盖抵住她的腰腹,五指收紧。
她美丽的眼睛骤然睁大,瞳孔里倒映着我冷漠的脸,喉间发出“咯咯”的声响,双手徒劳地抓挠着我的手臂。
“楚……楚安!”
她终于从齿缝里挤出我的名字,带着难以置信的惊惧。
我俯视着她,看着她因为窒息而涨红的脸,看着她眼中终于流露出的恐惧。
“你这双眼睛,真好看。”
03
我轻声说,空着的那只手,指尖轻轻拂过她光滑的脸颊。
“像你母妃。她当年,大概也是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娘跪在雨里求饶的吧?”
她浑身一僵。
我手上又加了一分力。
她的脸开始由红转紫,舌头微微伸出,泪水从瞪大的眼睛里涌出来。
就在她快要彻底窒息的时候,我松开了手。
她立刻像离水的鱼一样大口喘气,剧烈地咳嗽。
没等她缓过来,我已经抄起了旁边一根用来顶门的粗木棍。
掂了掂,然后,朝着她那条完好无损的右腿,狠狠砸了下去!
“啊——!!!”
凄厉的惨叫划破了柴房的死寂,也划破了皇宫看似平静的夜空。
骨头断裂的声音,清脆得令人牙酸。
她蜷缩起来,抱着腿,浑身抖得像风中的落叶,冷汗瞬间湿透了华丽的衣裳。
我丢开木棍,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俯视着地上痛苦抽搐的人。
“这条腿,是替你娘,还给我娘的。”
门外的脚步声这才急促地响起。
侍卫们冲进来,轻易地将我制服,按跪在地上。
我没有再反抗。
昭阳公主被人慌乱地抬了出去,临走前,她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刻骨的怨毒和一丝……深藏的恐惧。
我被带到父皇的书房时,天已经快亮了。
他坐在巨大的紫檀木书案后,身上只披着常服,脸色在跳动的烛光下显得晦暗不明。
书房里安静极了,只有炭火偶尔“噼啪”爆响一声。
我看着他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忽然低低地笑了出来,笑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父皇,”我哑着嗓子开口,“您刚才,就在柴房外面看着,对吧?”
“放肆!”他暴怒,抓起手边一份奏折就朝我掷来。
坚硬的奏折边角砸在我的颧骨上,火辣辣地疼,温热的血顺着脸颊流下来。
我舔了舔嘴角的血腥味,依旧笑着,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
“让女儿猜猜……是靖国那边,又提和亲的事了?”
我慢慢用手背擦去血迹,自顾自地说下去。
“大公主病重不起,二公主楚安是个可以随手送人的奴婢,唯一能代表大胤诚意、又身份尊贵的,就只剩下最得宠的三公主昭阳了。”
“可昭阳性子烈,又自幼习武,定然不肯乖乖远嫁。”
我顿了顿,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
“所以,得有人废了她一条腿,让她变成一个跑不掉的废人。这样,送去和亲,就成了无可奈何之下最好的选择,对么?”
父皇猛地站起身,几步走到我面前,脸色铁青。
他扬起手,狠狠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恰好打在刚才被奏折砸伤的地方,剧痛让我眼前黑了一瞬。
我偏着头,没躲,也没哭,只是慢慢转回来,继续看着他。
“叫我去献舞,故意激怒昭阳对我动手,再默许我反击……一切都是算好的,对吧?”
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
“这样一来,不是你逼她和亲,是她自己惹事受伤,不得不去。朝廷内外,柳家那边,也都无话可说。”
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着,看着我的眼神里杀意翻腾,仿佛下一刻就要叫人把我拖出去斩了。
我却迎着那目光,轻轻开口:
“父皇。”
“只要您愿意,女儿可以一直是您手里最快、最听话的那把刀。”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
杀意慢慢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东西,像深渊,望不到底。
最终,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疲惫地挥了挥手。
“滚出去。”
我恭顺地磕了个头,慢慢退出了书房。
04
后背的伤疼得我直冒冷汗,但我的嘴角,却缓缓勾起一个极淡的弧度。
第一步,成了。
昭阳公主将远嫁靖国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一夜之间传遍了皇宫的每个角落。
连浣衣局浆洗衣服的嗡嗡声里,都夹杂着宫女们压低的、兴奋的议论。
“听说了吗?昭阳公主的腿断了,好不了啦!”
“真是报应……谁让她平日那么跋扈……”
我蹲在老地方,用力搓洗着木盆里似乎永远也洗不完的衣物,仿佛一切都与我无关。
指节在冷水里泡得发白,破皮的地方刺刺地疼。
自从那日从书房出来,我名义上仍是浣衣局的奴婢,但管事刘嬷嬷再也不敢让我干最重的活,有时甚至会对我的晚来早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宫里的风向,变得比天气还快。
裴琰以“护送公主,商议细节”为名,住进了宫中的清晖阁。
他每日都会来向父皇请安,态度恭敬有礼,仿佛那晚宴席上锋芒毕露的不是同一个人。
朝堂上却不平静。
昭阳的舅舅,镇守北境的柳大将军柳承威,接连上奏,言辞激烈,痛陈和亲之辱,恳请陛下收回成命。
那些言辞恳切甚至以死相谏的奏章,最终都堆在了父皇的书案上,然后,由我亲手,一份一份,投入了暖阁角落的铜火盆里。
纸张在火焰中蜷曲、变黑,化作灰烬,像一群挣扎的黑色飞蛾。
火光映着我的脸,明明灭灭。
这日,我正安静地站在书房一角,整理着书架。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和急促的、拖沓的脚步声。
“父皇!父皇!儿臣求您!”
昭阳公主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她的右腿还裹着厚厚的绷带,脸色苍白如纸,头发散乱,早已没了往日的光彩。
守门太监想拦,被她狠狠推开。
父皇从书案后快步走出,一把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体,眉头紧锁,声音里满是“疼惜”。
“胡闹!伤还没好,怎么就跑出来了?”
他演得可真像一位慈父。
我垂着眼,将手中一本边角卷起的书轻轻抚平,放回原处。
“我不嫁!死也不嫁去靖国!”昭阳死死抓住父皇的衣袖,哭得涕泪横流,声音嘶哑,“那是蛮子待的地方!他们会杀了我的!他们会把我吊在旗杆上!”
她哭喊着,目光扫到一旁静立的我,突然像见了鬼一样,瞳孔骤缩。
“是你!是你害我!”
她尖叫起来,松开父皇,拖着断腿想朝我扑来,却立刻失衡,重重摔倒在地,额头磕在青砖上,血立刻渗了出来。
她不管不顾,用手扒着地,指甲断裂了也毫无所觉,就那么朝着我的方向爬,眼中是癫狂的恨意。
“楚安!我要杀了你!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狼狈不堪的模样,忽然觉得有些可笑。
然后,我就真的笑了出来。
声音很轻,但在她凄厉的哭喊和父皇的“安抚”声中,却格外清晰。
她停下爬行的动作,抬起头,死死瞪着我。
“你笑什么?!你这贱人!若不是你娘当年狐媚惑主,抢走我母妃的恩宠,若不是你们母女存了歹心,我母妃怎会……怎会死在靖国那种地方!”
我慢慢走过去,蹲下身,与趴在地上的她平视。
窗外的阳光恰好照进来,一半落在我脸上,一半落在她染血的、肮脏的手指上。
“你说,是我娘害死了柳贵妃?”我轻声问,语气平和得像在讨论天气。
她咬牙切齿:“难道不是?!”
我静静地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母妃咽气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的,是你父皇当年赐给她的、那个绣着鸳鸯的香囊?”
昭阳公主猛地怔住,眼中的疯狂和恨意瞬间凝固,然后,慢慢被一种更深、更冷的恐惧取代。
05
她的嘴唇颤抖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没有再说话,只是站起身,轻轻掸了掸裙摆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父皇已经坐回了龙椅后面,脸上恢复了帝王的威严与淡漠,仿佛刚才那出父女情深的戏码从未发生过。
他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
“和亲之事,关乎两国邦交,社稷安宁,朕意已决。”
“你是大胤的公主,享万民供奉,自当为江山百姓分忧,此乃你的本分,亦是你的荣耀。”
昭阳公主仰着头,望着高高在上的父亲,眼中最后一点微弱的光,彻底熄灭了。
那个会把她扛在肩头看花灯、会因为她一句喜欢就为她摘下星辰的父亲,死了。
死在了权势和算计里。
就像我的娘亲,也死在了这里。
我伸出手,将她从冰冷的地上扶起来。
我的手指触碰到她手臂的皮肤,一片冰凉。
我靠近她,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轻轻地说:
“你知道吗?我和我娘从靖国活着回到京城的那天,你母妃就死了。”
“你恨我入骨,觉得是我害了她。”
“可你从来没问过……她究竟,是怎么死的。”
她的身体在我手中剧烈地颤抖起来,不是愤怒,而是某种信念崩塌后的彻骨寒意。
风从洞开的门外吹进来,卷起几片枯黄的落叶,打着旋儿,落在光洁如镜的金砖上。
柳承威没有放弃。
朝会上,他再度抗辩,声音洪亮,震得梁柱似乎都在嗡嗡作响。
“陛下!此乃辱国之举!请斩主和之臣,整军备战,以振国威!”
然而,龙椅之下,暗流早已汹涌。
宫中禁军的数量悄无声息地增加了,巡防的路线和时间也变得诡异。
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身着玄色轻甲、面覆半甲、气息精悍冷冽的陌生武士,出现在了宫墙之内。
他们来自柳承威的麾下,美其名曰“加强宫廷戍卫”,实则与皇帝亲卫隐隐形成对峙。
我知道,摊牌的时刻快到了。
父皇很快下旨,以“巡幸南疆,抚慰边民”为名,摆开銮驾,即将南行。
明眼人都知道,这所谓的南巡,实则是迫于柳家压力的一场政治流放,前途未卜,生死难料。
而我,也被一道简单的口谕,点名随行。
江风带着深秋的凉意,暮色像滴入水中的浓墨,缓缓染黑了天际。
庞大的船队驶离了京城码头,桨橹划破平静的江面,留下长长的、逐渐消散的涟漪。
我跪坐在父皇宽敞的龙舟船舱内,为他轻轻捶着腿。
他闭着眼,似乎睡着了,但眉心那道深刻的竖纹却一直没有舒展。
我的动作机械而温顺,目光却像最警惕的夜鸟,掠过船舱的每一个角落,扫过窗外甲板上那些沉默巡视的、身着柳家军服色的士兵。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安静,连江水拍打船身的哗哗声,都显得格外单调而响亮。
忽然,一股极淡、却异常甜腻的香气,随着窗缝流入的微风,飘进了我的鼻腔。
是麝香,但又混着一丝别的、难以形容的腥甜。
我的头立刻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眼皮也开始发沉,像是熬了几宿没睡。
我悄悄用牙齿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
剧痛传来,带着铁锈味的鲜血溢满口腔,瞬间驱散了那恼人的困意。
就在我神智为之一清的刹那——
一道黑影,如同鬼魅般从高高的桅杆顶端倒坠而下!
速度太快,快得像一道撕裂夜色的闪电!
寒光乍现!
一柄毫无光泽的漆黑短刃,精准无比地刺破窗纸,直取榻上父皇毫无防备的咽喉!
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
船舱外的侍卫似乎毫无察觉,或许……他们本就“不应”察觉。
我的身体在大脑做出任何思考之前,已经本能地扑了出去——
重重地,挡在了那道寒光与榻上的人之间。
剧痛。
先是左肩胛骨下方传来冰凉的触感,紧接着,是滚烫的、液体汹涌而出的感觉。
世界的声音仿佛瞬间被抽离,然后又轰然灌回。
我听见了侍卫们惊怒的呼喝,杂乱的脚步声,兵刃出鞘的铿锵声。
我倒在冰冷的地板上,侧过头,看见那黑衣刺客在一击不中之后,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没有看我这个突然出现的“障碍”第二眼,身形如烟,向后疾退,眼看就要撞破另一面的舷窗,投入外面漆黑的江水。
他的动作干脆利落,目的明确得可怕。
就在他的指尖即将碰到窗棂的前一瞬,另一道身影,以更快的速度,从舱门外的阴影里掠入。
玄色衣角在烛光中一闪。
“铿!”
短兵相接的刺耳锐响!
裴琰手持他那把标志性的乌沉短刀,架住了刺客反手挥出的另一把匕首。
火星迸溅。
两人在狭窄的船舱内闪电般过了几招,招式狠辣简洁,皆是杀人之术。
裴琰显然技高一筹,一刀格开对方匕首,刀柄顺势狠狠砸在刺客的颈侧!
刺客闷哼一声,软软倒地,被随即涌进来的侍卫死死按住。
裴琰收刀,转过身。
他的呼吸平稳,仿佛刚才那电光石火的交手只是闲庭信步。
他的目光先落在被侍卫扶起、面色惊怒交加的父皇脸上,微微一颔首。
“陛下受惊了。”
然后,他的视线才缓缓下移,落在了倒在地上的我身上。
我肩上的伤口还在汩汩冒血,染红了半边粗布衣裳,脸色大概白得吓人。
他的眼神很深,像结了冰的湖面,下面却涌动着看不清的暗流。
他看了我几秒,忽然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极淡的、难以捉摸的笑。
什么也没说。
父皇似乎这时才从惊变中完全回过神来,他的目光复杂地在我和裴琰之间扫了一个来回,最终落在我的伤口上,对赶来的御医挥了挥手。
“给她止血。”
语气平淡,听不出太多情绪,就像在吩咐处理一件磕碰了的器物。
我被抬到隔壁狭窄的舱室。
御医处理伤口的手法不算轻柔,药粉洒上去的刺痛让我浑身一颤,但我咬着牙,没吭声。
窗外的江面黑沉沉的,对岸有零星灯火,像鬼火般飘忽不定。
龙舟在继续向前行驶,仿佛刚才的刺杀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小插曲。
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伤口包扎好后,侍卫退了出去,只留我一个人躺在硬邦邦的板铺上。
夜深了。
江风更凉,一阵阵从窗缝钻进来。
我睁着眼,望着头顶低矮的、绘着简单祥云纹的舱板,毫无睡意。
左肩的疼痛持续不断地传来,一下,又一下,敲打着我的神经。
但这痛,却奇异地让我感到一丝清醒,一丝……真实。
我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了娘亲疯癫前,最后看我的那个眼神。
不是恨,不是怨,而是一种空茫的、仿佛什么都映不进去的寂静。
想起了我把那三根细如牛毛的银针,慢慢推进她乌黑发间时,指尖感受到的、她头颅骨缝的微小阻力,和她身体无法自控的、细微的颤抖。
想起了更早以前,在靖国那座清冷的别院里,裴琰扔给我那卷兵书时,脸上似笑非笑的神情。
他说:“眼泪和美貌,是这世上最无用的武器。想活着,得学会用别的。”
当时我不懂,或者说,假装不懂。
现在,我好像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