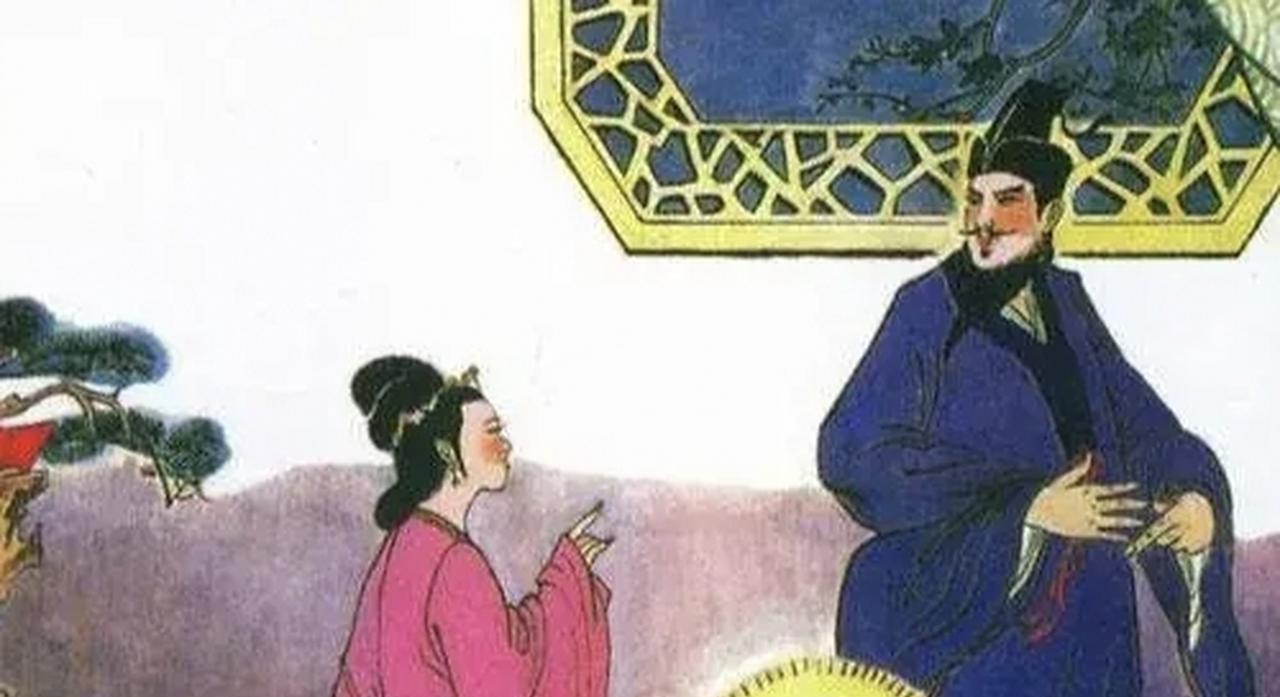北宋时期,宰相王安石发现小妾与家丁私会,本欲惩戒,小妾作诗道:“八月十五月光稀,谁让老夫娶少妻?”王安石听后羞愧不已,随后他做了一件事,成了千古佳话。 北宋元丰年间,宰相府邸里王安石端坐主位,一身官服洗得有些发白,与这佳节华宴的氛围格格不入。 他面容清癯,目光停留在侧席那位年轻女子身上。 姣娘,不过双十年华,身着月白褙子,衬着杏子黄的抹胸,烛光下肌肤胜雪,眉眼如画,此刻却低垂着眼睫。 王安石端起酒盏,他没有看姣娘,反而看向庭院中那轮冷月,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了席间细微的谈笑与丝竹余音,缓缓吟道。 “日出东来还转东,乌鸦不叫竹竿捅。鲜花搂着棉蚕睡,撇下干姜门外听。” 诗句落地丝竹声停了,家眷们面面相觑,不解其意。 唯有姣娘,身体猛地一僵! 她猛地抬起头,撞上王安石那双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眼眸。 那目光里没有暴怒,没有斥责,只有一种冰冷的审视。 “日出东来还转东”暗指那本不该发生、却周而复始的私情。 “乌鸦不叫竹竿捅”隐喻他中秋前夜,撞破丑事后强忍怒火,借捅乌鸦窝惊走屋中人。 “鲜花搂着棉蚕睡”将她的青春美貌与那年轻家丁的卑微身份,勾勒得不堪入目。 而最后一句“撇下干姜门外听”更是赤裸裸的自嘲与控诉,他这位被岁月风干的“老姜”,竟成了门外听壁角的可怜虫! 巨大的羞耻与恐惧包裹住了她,让她几乎窒息。 然而,在慌乱之后,一股积压已久的委屈,猛地冲上心头。 她迎着王安石的目光,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却异常清晰地回敬道。 “八月十五月光稀,谁叫老夫娶少妻?” 反问!不是辩解,不是求饶,而是直指根源的诘问! 你指责鲜花为何委身棉蚕? 那你可曾想过,这朵鲜花为何会落入你这块早已干枯皲裂的“老姜”之手? 一切的源头,不正是你这位位高权重的宰相大人,不顾年岁悬殊、性情迥异,硬要将她这株鲜活的春花,移栽到你这片早已荒芜沉寂的园圃之中吗? 你给了她宰相妾室的名分,却吝啬给予一丝丈夫应有的温情。 你的心思,全在朝堂、变法,可曾有一刻真正垂怜过枕边人? 这“老夫少妻”的错配,才是所有不堪的起点! 王安石呆住了,向来沉稳面不改色的面容,第一次出现了裂痕。 姣娘的反诘,瞬间剖开了他刻意忽略的病灶。 在姣娘那双含着泪光、却异常清亮的眼眸注视下,一切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是啊,他王安石,一生以“拗相公”闻名,执着于经世济民,律己近乎苛刻,官袍旧了不舍换,饮食粗粝如寒士,视女色如无物。 续弦姣娘,或许更多是出于续嗣或照料生活的现实考量,而非情之所钟。 他将她迎入府中,却从未想过,他给予她的,只有宰相府邸的深宅大院,和一个永远伏案疾书的背影。 她的青春、她的才情、她对温情的渴望,在他宏大的家国叙事里,渺小得如同尘埃。 翌日清晨, 王安石没有上朝。 他提笔,在铺开的宣纸上,写下两个名字。 姣娘,和那个年轻家丁的名字李安。 午后, 姣娘和李安被唤来。 两人战战兢兢,面如土色,尤其是李安,几乎站立不稳。 两人都以为大祸临头,王安石却示意仆人端上一个红木托盘,上面整齐地摆放着一份文书和一封银锭。 他拿起那份文书:“此乃放妾书。” 他将文书递给姣娘,“自今日起,你不再是相府妾室,恢复自由之身。” 王安石又指向那封银锭:“这是一千贯,足够你们二人置办田产,安家落户。” 这些银钱,算是一点补偿。 拿去吧,寻个僻静处,好生过日子,莫负了这年华。 ”李安闻言,涕泪横流,连连叩头。 姣娘捧着放妾书和银钱,看着眼前这位素来威严冷峻的宰相,此刻眼中流露出的那抹复杂难言的宽容与落寞,心中百感交集。 是劫后余生的狂喜? 是对未来的茫然? 还是对这个曾是她丈夫、此刻却亲手还她自由的老人的一丝愧疚与感激? 她最终只是深深一揖,泪水无声滑落。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汴京官场。 这份胸襟,这份气度,在等级森严、夫权至上的宋代,堪称惊世骇俗。 于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赞誉,悄然流传开来。 这并非仅仅形容其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更赞颂其胸襟之宽广,能容人之过,亦能自省其非。 王安石本人,对此未置一词。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千年王安石︱段子里的政治家:中国古代笑话中的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