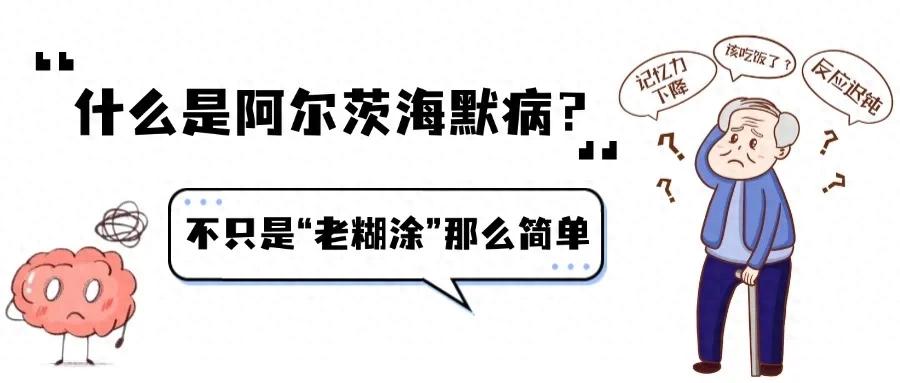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简称AD),俗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好发于老年人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就像悄无声息的“记忆小偷”,它会在不知不觉中侵蚀一个人的思维和记忆,最终让患者失去自理能力。当症状明显时,大脑的损伤往往已经不可逆转。
《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5》揭示,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患者总数已攀升至1699万,占据全球病例数的29.8%。这意味着,平均每20个中国家庭中,便有1人深受阿尔茨海默病之苦。
在过去几十年,研究者依赖二维细胞模型(2D cultures)和动物模型(尤其是转基因小鼠)来解析AD的发病机制与药物筛选。然而,这些模型存在明显局限:
1.二维细胞模型缺乏复杂的三维微环境与细胞间信号调控,无法再现人脑组织的生理特征。
2.动物模型虽能在系统水平上提供认知与病理信息,但人-鼠间的基因差异及神经生理差异,导致药物在临床试验中高失败率(> 99%)。
在这种背景下,类器官(organoid)技术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重要突破口。自Lancaster 等人于2013 年首次从人多能干细胞(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hPSCs)构建脑类器官以来(Lancaster et al., Nature 2013),该技术在三维结构、细胞异质性、发育轨迹等方面高度模拟了人类脑组织。尤其在AD研究中,脑类器官能够:
1.在体外重现Aβ 斑块与Tau 病理;
2. 建立患者特异性iPSC 模型以探究遗传易感机制(如APP、PSEN1、APOE4 突变);
3.结合高通量成像与组学分析,用于药物筛选和毒理学评估。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利用脑类器官模型揭示AD的早期病理变化。例如Raja 等人 (2016, Nature) 报道,利用患者来源的iPSC 构建的脑类器官在6 周培养后即可出现 Aβ 沉积与Tau 磷酸化,这是传统二维培养无法实现的。此外,Park等利用microglia-containing 脑类器官进一步证明,免疫-炎症反应与 Aβ 积聚之间存在动态相互作用,为理解AD中小胶质细胞的致病作用提供了模型支撑。
然而,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仍面临巨大挑战。目前,只有少数药物(如Lecanemab、Donanemab)在大规模III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延缓认知衰退的潜力,但其疗效有限、副作用显著。如何通过脑类器官实现更精确的机制解析-药物筛选-临床预测三位一体,是未来十年的关键方向。
01


脑类器官基础


脑类器官的定义与来源
脑类器官(brain organoid 或cerebral organoid)是由人多能干细胞(包括胚胎干细胞ESC 与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在三维培养条件下自组织形成的、具有脑组织特征的微型结构体。与传统二维神经细胞培养不同,类器官能够通过体外发育过程形成具有空间分层的皮质样结构,部分再现早期神经发育的关键事件,如神经干细胞增殖、神经管样结构形成、神经元迁移与层化等(Lancaster et al., Nature, 2013)。
脑类器官通常来源于三种细胞体系:
1)ESC/iPSC自组织发育体系:依靠内源信号驱动形态形成。
2)区域特异性诱导体系:通过添加特定形态因子(如Wnt、FGF、BMP、TGF-β 抑制剂)定向生成前脑、海马、丘脑、下丘脑等区域。
3)共培养/融合体系(assembloid):将不同区域类器官(如皮层+丘脑)或含不同细胞类型(如神经元+小胶质细胞)的类器官融合,以研究细胞间互作与神经环路形成。
脑类器官的构建流程
典型脑类器官的制备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1)干细胞扩增与胚体形成:ESC/iPSC 在低黏附培养中形成胚体(embryoid bodies, EBs);
2)神经诱导阶段:使用双SMAD 抑制策略(Noggin + SB431542)促进神经外胚层分化;
3)类器官生长与成熟:转入基质胶(如Matrigel)中进行三维培养,并在旋转式生物反应器中长期培养(> 3 个月),以促进氧气与营养扩散;
4)功能表征:通过免疫染色、单细胞转录组测序、电生理记录和钙成像等技术验证神经元网络活动。
这一体系可形成大小3–5 mm 的组织球体,内部包含皮质前体层(VZ、SVZ)和功能性神经元网络。研究表明,成熟的脑类器官在体外可出现同步放电和伪脑电活动,显示出早期神经环路的功能特征。
脑类器官与人脑的相似性与差异
脑类器官的关键优势在于其人源性与三维性。它们能够部分模拟人脑皮层发育的时空动态,包括:人特异的皮层放射状胶质细胞延展;长期神经发生;APOE、PSEN1等AD 相关基因表达谱的时序特征。
然而,它们仍存在显著差异:
缺乏血管系统→ 氧气与营养供给受限;缺乏免疫系统与微胶质细胞自然发育→ 难以完全再现炎症反应;发育阶段停留在胎儿期水平,与老年性疾病模型(如AD)存在“时间窗”错配。近期研究通过血管化类器官与小胶质细胞嵌入模型试图弥补这些不足(Cakir et al., Nature Methods, 2022)。
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特定建模策略
为了更贴近AD 的病理过程,研究者在脑类器官体系中引入了多种改进策略:
1)遗传编辑(CRISPR-Cas9):在人iPSC 中敲入或敲除 AD 相关基因(如APP、PSEN1/2、APOE4),以再现家族性 AD (fAD) 与散发性AD (sAD) 病理。
2)诱导“老化”模型:利用端粒缩短、ROS 累积、DNA 损伤等策略,使类器官表现出与老年脑相似的表型。
3)加入小胶质细胞与血管化组分:重建神经免疫交互,模拟神经炎症(Park et al., Cell Stem Cell, 2021)。
4)长期培养与多组学分析:结合单细胞RNA-seq 与蛋白组学揭示Aβ 积聚、Tau磷酸化、突触信号改变等动态变化。
这些改进显著提升了类器官在AD 机制解析和药物筛选中的预测性与可重复性。
脑类器官技术通过人源化三维系统,成功重建了神经发育与病理的核心要素,是连接分子机制研究与临床疾病表型的重要桥梁。
02
脑类器官在阿尔茨海默病机制解析中的应用
脑类器官(brain organoids)因具有人源、三维、发育动态可控等特性,成为理解阿尔茨海默病(AD)发病机制的理想模型。它不仅能够重建传统细胞模型无法模拟的淀粉样蛋白沉积、Tau蛋白磷酸化、神经炎症与突触退化等复杂病理过程,还可以通过患者来源iPSC 模型揭示个体化的遗传易感差异。本章将系统梳理脑类器官在AD机制研究中的关键应用与发现。
Aβ 淀粉样蛋白沉积与Tau蛋白异常磷酸化的再现
AD的两个核心病理标志——Aβ 斑块与Tau蛋白磷酸化缠结——过去难以在二维培养中同时重现。Lancaster团队的开创性研究首次提出脑类器官可在体外再现神经发育过程,但未涉及病理。直到Raja et al.,研究者利用携带APP 和PSEN1 突变的患者来源iPSC,构建出能同时产生Aβ 沉积和Tau 异常磷酸化的三维脑类器官模型。这一模型在培养6周后出现β-淀粉样蛋白聚集(Thioflavin S染色阳性),并在免疫组化中检测到p-Tau (Ser202/Thr205) 积累。
进一步研究表明,Aβ沉积可诱导Tau 异常磷酸化并触发突触蛋白(如 Synaptophysin 和PSD-95)减少(Raja et al., Nature 2016)。该模型首次验证了在三维人源环境中“ Aβ → Tau → 神经功能障碍” 的级联通路,为药物筛选提供了直接的病理基础。
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与小胶质细胞间互作机制
AD 的病理并非单一神经元损伤,而是多细胞类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传统的脑类器官主要由神经元与放射状胶质细胞构成,缺乏免疫细胞成分。为克服这一缺陷,Park et al. 通过在脑类器官形成早期阶段共培养小胶质前体细胞,成功建立了含免疫细胞的脑类器官模型。该模型揭示:小胶质细胞在Aβ 沉积早期即被激活,表现出CD68 与IBA1 阳性增强;IL-1β 与TNF-α 等促炎因子表达上调;抑制NF-κB信号可缓解 Aβ 相关神经损伤。
此外,Joshi et al. 发现,APOE4基因型的小胶质细胞类器官在 Aβ 刺激下表现出吞噬能力下降和脂质代谢紊乱,与患者脑组织转录组呈现相似趋势。这类研究证明,类器官模型不仅可以观察神经元病理,还可解析免疫与代谢层面的致病机制。
神经炎症、氧化应激与血脑屏障损伤
Cakir et al.通过在脑类器官中引入血管内皮细胞和周细胞,构建出血管化脑类器官(vOrganoid)。该模型可模拟血–脑屏障(BBB)结构,在 Aβ 暴露后出现TJP1(ZO-1)和CLDN5 下调,提示血脑屏障完整性受损。这一研究首次实现了在体外模型中动态观察AD相关血管病理。
在代谢层面,Zhao et al. 报道APP/PSEN1 突变类器官的ROS累积与线粒体膜电位下降,表明能量代谢障碍是Aβ 积聚后的早期事件。抗氧化剂N-acetyl-cysteine 能显著降低ROS水平并部分恢复神经元突触活性,进一步验证了氧化应激在AD中的核心作用。
年龄化与时间动力学机制探索
传统脑类器官的“发育阶段滞留”限制了老年疾病建模。为此,研究者开发了**“加速老化类器官”策略**。Mertens et al. 使用progerin (早衰蛋白)过表达诱导DNA损伤与表观老化,使类器官在短时间内获得类似老年脑的表型。该体系中Aβ 积聚与Tau 磷酸化显著提前出现,说明细胞老化加速了AD样病变的形成。此类模型为研究AD早期触发因素提供了重要实验平台。
系统生物学与多组学揭示的新机制
近年来,单细胞测序(scRNA-seq)、空间转录组学与蛋白组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脑类器官研究。Bhaduri et al. (Nature, 2020) 通过单细胞测序比较AD类器官与健康对照,发现AD类器官中星形胶质细胞表现出GFAP 与SERPINA3 上调、神经元表达MAPT 与APP 升高的特征,与患者脑皮质组织的转录特征高度吻合。这一结果证明脑类器官能捕捉到AD的真实分子网络变化。
小结
脑类器官为AD研究提供了一个人源化、结构化、动态发育的理想模型平台,使得研究者能够在体外重建疾病的多维病理网络。从Aβ 沉积到Tau 磷酸化,从小胶质细胞炎症到血脑屏障破坏,类器官已成功覆盖AD的多个致病环节。尤其是与患者来源iPSC 结合后,脑类器官能够揭示基因型特异性机制(如APOE4、TREM2),为精准医学与药物筛选提供实验支撑。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Lancaster MA, et al. Cerebral organoids model human brain development and microcephaly. Nature. 2013;501(7467):373–379.
2.Choi SH, et al. A three-dimensional human neural cell culture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 Nature. 2014;515(7526):274–278.
3.Raja WK, et al. Self-organizing 3D human neural tissue derived from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recapitulates Alzheimer’s disease phenotypes. Nature. 2016;531(7592):365–370.
4.Cummings J, et al. Alzheimer’s disease drug development pipeline: 2022. Alzheimers Dement. 2022;18(9):1634–1652.
5.Park J, et al. Aβ and tau pathology in patient-derived organoids reveals distinct cellular responses. Nat Med. 2022;28(6):1122–1135.
6.Kim J, et al. Patient-specific Alzheimer’s disease organoids reveal genotype-dependent drug responses. Cell Stem Cell. 2022;29(12):1891–1907.e8.
— EN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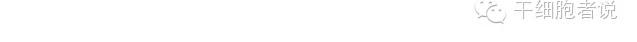
新干细胞者说
- 科普 情怀 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