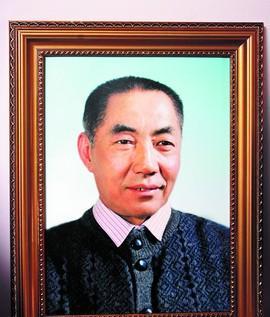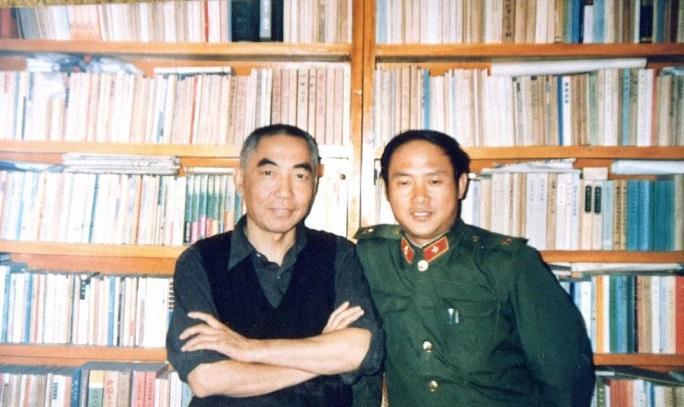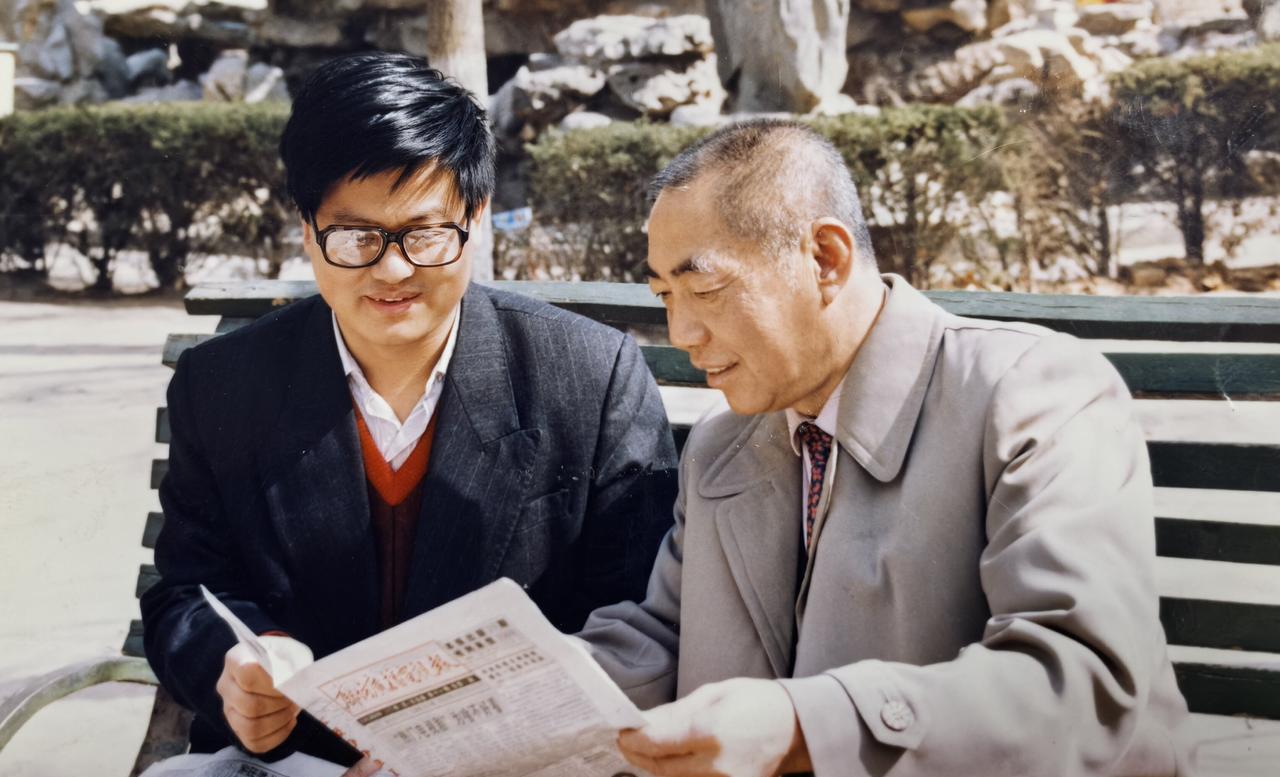改革开放后,《金光大道》的再版在文坛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莫言、艾青、叔绥人、何满子等人纷纷撰文提出批判,文章言辞激烈,多有讥讽之语。莫言说:“曾被钉在文坛耻辱柱上的《金光大道》,在人们不经意之中再度粉墨登场”;其作者“在市声喧嚣的今天翻腾旧账,吁求所谓“活下去的权利”,无非是故作惊人之呼,为《金光大道》的做宣传罢了”;在结尾又不无轻蔑地说:“什么金光大道,回光返照而已!” 而学者焦国标在文章里,毫不留情地对浩然的“代言人”身份展开了反驳。他首先把目光聚焦在浩然那些看似和农民关系紧密的话语上。浩然曾说过“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乍一听,这话仿佛将浩然和农民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好像他真的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但焦国标却敏锐地察觉到,这话根本经不起仔细推敲。 焦国标不禁发问,浩然先生自封为“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可他到底代表了农民什么呢?他又问,农民会答应让他做代表吗?会推举他做代表吗?浩然还辩解说,他写《艳阳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创作冲动和激情,没有人要求他按照某种路子写。可干了错事,难道因为出于自己的冲动和激情就可以被原谅吗?难道他就一点错都没有吗? 其实客观的讲,浩然对乡土文学还是有贡献的。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乡村生活并非静止的画卷,而是由无数鲜活的人物行动与流淌的日常细节交织而成的动态场景。他既不依赖华丽的辞藻堆砌,也不沉迷于抽象的心理剖析,而是将笔墨深深扎根于泥土般的生活肌理,让人物在锅碗瓢盆的碰撞中、在田间地头的穿梭中、在乡风民俗的浸润中自然生长。这种以行动写人、以细节显情的笔法,不仅让文字充满了烟火气,更让那个年代的乡村众生相跃然纸上,成为镌刻在文学史上的生动注脚。 《艳阳天》中萧长春与焦淑红的那段厨房互动,看似寻常的做饭场景,实则藏着对乡村男女生存状态的深刻洞察。当萧长春忙完社里的公事回到家,面对冷锅冷灶的空寂,“屋里缺一个人” 的念头如炊烟般袅袅升起,却又被 “找个合适的也挺不容易” 的现实顾虑压下去。这短短两句心理活动,道尽了乡村干部在公私之间的拉扯 —— 作为村干部,他的心系集体,肩上扛着全村人的生计;作为父亲,他又不得不笨拙地填补家庭里母性角色的空缺。这种矛盾在他给孩子做饭时被放大:“笨手笨脚,弄得里外都是烟雾”。这烟雾不仅是柴草燃烧的产物,更像是他内心慌乱与无助的外化。在那个集体主义至上的年代,男性往往被赋予 “主外” 的责任,操持家务的细腻功夫多由女性承担,萧长春的 “笨” 并非能力缺陷,而是社会分工在个体身上的投射。 焦淑红的出现,恰如一阵清风驱散了满屋烟雾,而她的行动则像一串精准的音符,奏响了乡村女性的生存智慧。作家通过萧长春的视角,将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捕捉得细致入微:开水沸腾时俯身观察水量,盖锅时用盆子加压、用抹布围边,西锅点火倒油、转瞬炒好一大碗菜。这一连串动作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仿佛经过千百次演练般自然流畅。在物资匮乏的乡村,蒸汽是热量的载体,是粮食熟透的关键,焦淑红用盆子压锅盖、用抹布围缝隙的举动,绝非多余的细节 —— 那是对每一份热能的珍惜,是在艰苦环境中炼就的持家本能。 而她同时兼顾两口锅的麻利劲儿,更显露出乡村女性在繁重劳动中炼就的高效与坚韧。彼时的乡村,女性不仅要承担田间劳作,更要操持全家饮食起居,焦淑红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千万乡村女性日常的缩影。作家没有用 “贤惠”“能干” 这类形容词,却让读者在蒸腾的热气与饭菜的香气中,真切感受到这个姑娘身上蓬勃的生命力。这种以行动塑造人物的笔法,比任何赞美都更有说服力,因为生活本身的逻辑,永远比刻意的褒扬更动人。 《浮云》中程广老伴儿做媒的情节,则像一幅工笔素描,将乡村婚恋中的人情世故与价值判断勾勒得入木三分。老太太端详宋素兰的那番观察,堪称乡村版的 “识人术”:旧衣服上的补丁、粗大的手掌,是 “能干活、能吃苦” 的明证;衣领上葫芦样的纽襻、鞋口细密的针脚,又显露出 “心灵手巧” 的特质;而 “眼不斜视”“笑不露齿”“不摇头晃脑” 的举止,则指向 “安分守己” 的品性。这些观察维度,全是从过日子的实际需求出发。 《金光大道》中年轻人调侃邓久宽的对话,则像一缕清风,吹散了主流叙事中过于浓重的政治色彩,显露出乡村生活本真的幽默与鲜活。周永振那句 “好几个月都忍了,这一会儿工夫就耐不住啦”,带着点促狭的戏谑;吕春江接腔 “大嫂子正依着门框盼着你”,更是把思念之情说得直白又热辣。而邓久宽 “怒冲冲瞪一眼” 却 “瓮声瓮气” 的反驳,看似恼怒,实则藏着几分被说中心事的羞赧。这段对话,没有一句涉及 “革命”“集体”,却在你来我往的调侃中,显露出乡村青年真实的情感状态 —— 他们既是集体中的一员,更是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