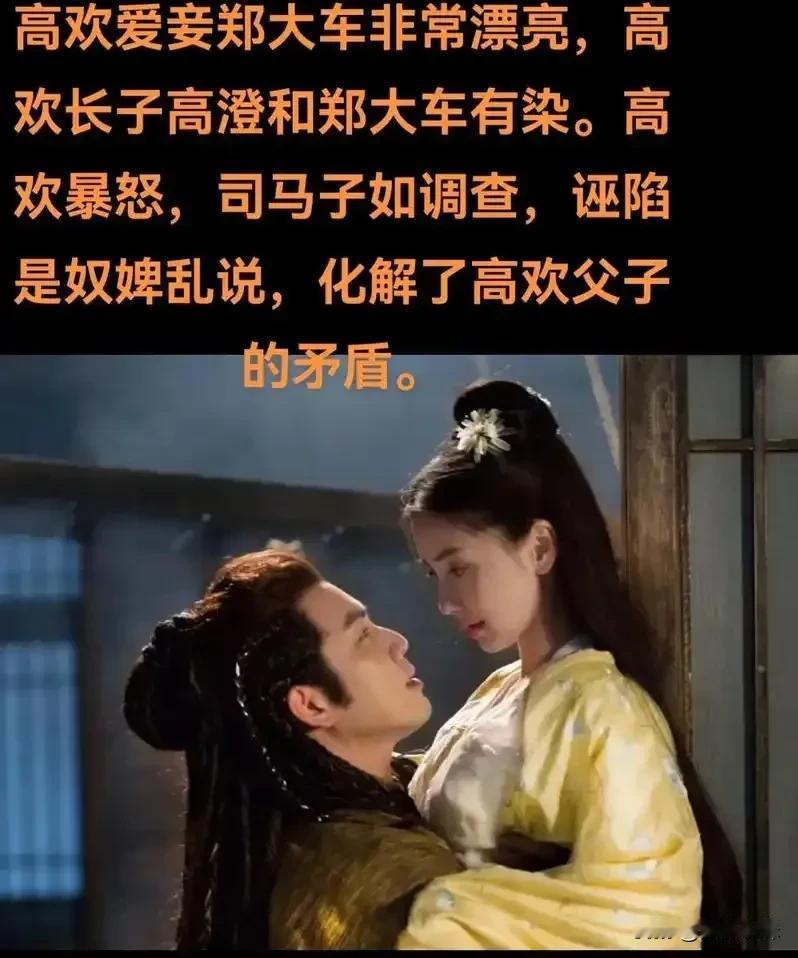535年夜里,高澄悄悄披了件外袍,脚步轻得几乎没声。他十四岁,刚被立为世子。那晚,他不是去书房,也不是巡夜。方向清楚——直奔郑大车的房间。 廊下的灯笼被风刮得晃悠,光影子在青砖地上歪歪扭扭,像极了高澄此刻的心思。他攥着外袍的袖口,布料被捏出几道褶子,手心的汗濡湿了丝线。刚过十四岁生辰的少年,身量还没完全长开,可那双眼睛里的光,早没了寻常孩童的懵懂。 郑大车的房门虚掩着,里头漏出点烛火,混着淡淡的熏香。高澄在门口站了片刻,听见里头有翻动书页的声音,轻轻叩了叩门板。 "进来。"郑大车的声音温温软软,听不出什么情绪。 他推门进去时,见郑大车正斜倚在榻上,手里捧着卷书,烛火照在她鬓角的珠花上,亮闪闪的。她抬眼瞧着他,没起身,也没惊讶,像是早料到他会来。 "世子深夜寻我,该不是忘了规矩吧?"郑大车把书卷合上,放在手边的小几上,语气里带点玩笑的意思。 高澄垂着手站在当地,腰杆挺得笔直,倒比白日里在人前更显郑重。"我睡不着,想找夫人说说话。" "哦?世子有心事?"郑大车挑了挑眉,示意他坐到对面的椅子上,"是为了府里的事,还是为了你父亲?" 这话正戳在高澄心上。三天前父亲高欢当众立他为世子,府里的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有敬畏,有试探,还有些藏在暗处的打量,像针似的扎人。他知道,这世子之位坐得稳不稳,不光看父亲的意思,更得看自己能不能扛事。 "我怕做不好。"高澄低声说,声音里带着少年人少有的坦诚,"府里的管事们,个个都是跟着父亲出生入死的,我年纪轻,他们未必肯服我。" 郑大车端起茶杯抿了口,指尖划过温热的杯壁。"你父亲十三岁就在草原上牧马,比你现在还小呢。那时候谁又能想到,他后来能成一方霸主?" 高澄猛地抬头看她。他知道父亲的过往,却从没听过有人这样轻描淡写地说出来,像在讲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年纪小不是短处,"郑大车放下茶杯,目光落在他脸上,"怕的是心里没底气,眼里没方向。你父亲立你为世子,不是因为你是长子,是因为他瞧见了你身上有股劲,像他年轻的时候。" 窗外的风更紧了,吹得窗棂呜呜响。高澄想起白日里父亲拍着他肩膀说的话:"高家的担子,早晚要落在你肩上,别怕,往前闯。"那时候他只顾着紧张,没细想父亲话里的意思,此刻被郑大车一点拨,心里忽然亮堂了些。 "夫人在府里这么久,是不是也觉得我太毛躁?"他想起前几日跟幕僚争执,差点把茶盏摔了,脸上有点发烫。 郑大车笑了,眼角的细纹弯成好看的弧度。"毛躁才是少年人该有的样子,总比死气沉沉强。但毛躁外头,得裹着层稳重。就像这灯笼,火苗再跳,外头有层纸罩着,才不会被风吹灭。" 她起身走到窗边,推开半扇窗,夜风吹进来,带着草木的清气。"你父亲当年打硬仗,帐里议事能拍着桌子骂人,转头跟敌营使者说话,又能笑得春风和煦。厉害的人,都懂得什么时候该藏,什么时候该露。" 高澄望着她的背影,忽然明白为什么父亲总说郑大车是个有见识的。她不说那些干巴巴的大道理,几句话就像把钥匙,打开了他心里堵着的那扇门。 "我晓得了。"他站起身,腰杆比刚才更直了些,"谢夫人指点。" 郑大车转过身,看着他眼里重新亮起的光,点了点头。"回去吧,好好睡一觉。明天起,府里的事,该怎么管就怎么管,错了也不怕,年轻人,经得起摔打。" 高澄轻轻应了声,转身往外走。这次脚步不再像来时那样发飘,每一步踩在地上,都透着股踏实。廊下的灯笼还在晃,但他瞧着那些晃动的光影,忽然觉得没那么乱了。 回到自己房里,高澄脱了外袍,坐在灯下想了许久。他想起郑大车说的"藏"与"露",想起父亲拍他肩膀的力道,想起府里那些等着看他笑话的眼神。窗外的天渐渐泛起鱼肚白,他吹灭烛火时,眼里已经没了半分犹豫。 有些成长,就是在这样的深夜里,被几句不经意的话点透的。十四岁的少年世子,从郑大车的房间走出来时,带走的不仅是几句指点,更是一份扛得起事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