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逃到香港的国军中将张际鹏花光积蓄后,想去台湾遭到拒绝,穷困潦倒之下,只得写信向黄埔一期同学袁守谦求助。 张际鹏出生在湖南醴陵,年少时聪明勤奋,靠着一股拼劲考进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在那个将军辈出的年代,能挤进这所军校的第一批学员,意味着一只脚踏进了权力场,当年北伐打得热火朝天,张际鹏冲锋在前,攻打武昌城时带头破门而入,赢得了上层的嘉奖,也为自己铺下了升迁的路。 从北伐到抗战,张际鹏并非最耀眼的那一批人,但始终稳扎稳打,他一路升任旅长、师长、军长,战场上不曾怯懦,也积攒下不少功绩,抗战结束后,曾被派去担任战地视察组组长,实际上是前线的“监督员”,地位虽不是顶尖,却也不容小觑,到了内战阶段,他暂时归属在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原本担任军长,后来被调任副司令官,表面提拔,实则被架空,陈明仁当时正筹划起义,对张际鹏心存疑虑,把他调离兵权核心,算是防患未然。 1949年夏天,湖南起义爆发,陈明仁在通电中列上了张际鹏的名字,想借此稳住局势,制造“广泛参与”的印象,张际鹏并未参与,却因此背上了“通共”嫌疑,情势一变,他带着家人连夜南逃,辗转到了香港,开始了截然不同的一段人生。 初到港岛,张际鹏手里还握着一些变卖祖宅所得的黄金和美金,他在九龙租了公寓,生活暂时无忧,还能与逃亡同僚保持联络,继续幻想有朝一日能重返军界,当时的张际鹏,虽然脱下军装,却仍然坚持每日研读电报、画战图、联络旧部,期望有机会“再起”,然而局势变化迅速,昔日的战友各自为营,台湾当局对任何政治背景不清者都持保留态度,张际鹏的申请如石沉大海。 黄金终究有限,尤其面对飞涨的物价和不断扩大的支出,张际鹏不懂得理财,听信他人建议投资房地产,结果遭遇诈骗,损失惨重,为了维持生计,他甚至涉足地下赌场,想靠运气翻盘,却越陷越深,赌桌上不比战场,没有排兵布阵的余地,只有输赢两个结果,他输了积蓄,也丢了尊严。 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张,张际鹏从市区搬到乡郊,从舒适的公寓搬进简陋的阁楼,妻子靠缝补衣物挣点小钱,孩子们辍学帮忙生计,有的去码头扛货,有的在街头兜售香烟,家中再也看不到昔日将军的影子,只有一屋子的疲惫和压抑,最艰难的时期,张际鹏甚至靠慈善机构发放的救济粮维持生活。 在这一切困顿之中,他想起了袁守谦,袁是黄埔同学、湖南老乡,当年还曾在抗战时期共事,如今在台湾政坛如鱼得水,是蒋氏父子的亲信,张际鹏提笔写信,把家中的困境一一道来,言语中满是哀求,他知道自己被误解,却无法解释;知道袁有影响力,却不确定能否施以援手。 袁守谦起初回信,寄来一笔钱,说当前时局不稳,暂时不宜赴台,张际鹏理解,继续等待,可等了一年又一年,回应却越来越少,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被贴上了“靠不住”的标签,在那个疑心重重的年代,一旦被视为不忠,便很难翻身。 1952年冬天,妻子因肺病去世,家中无钱医治,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情恶化,那一夜,屋外天降大雨,屋顶漏水,屋内一片湿冷,张际鹏坐在床边,手里捧着发黄的黄埔同学录,久久没有言语,那是他人生中最孤立无援的时刻,连昔日的勋章也被拿去典当,只为换几餐温饱。 转机出现在1954年底,或因袁守谦在台北政治圈的运作,或因救济机构揭露他曾在抗战中营救特工的事实,张际鹏的申请终于获得松动,1955年夏天,他带着仅存的家人登上前往台湾的船,结束了在香港长达六年的流亡生活。 抵达台湾后,张际鹏并未获得实职,他被授予“退役少将”的头衔,每月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生活虽谈不上富裕,但总算摆脱了贫困,他在台北郊区租了间小屋,靠自己做的湖南辣酱贴补家用,他把辣酱装进玻璃瓶,贴上手写标签,拿到市场售卖,偶尔还能遇到老乡,彼此寒暄几句。 在台湾的日子,他不再提起过往战功,也不再参加黄埔校友聚会,他选择低调地活着,把自己与世界的联系收敛到最窄的范围,家中陈设简单,唯一显眼的是那枚青天白日勋章,被他摆在书架角落,不再张扬。 1970年,张际鹏因病去世,讣告只有几行字,未提生前战役,不提军功,也不提艰难流亡的岁月,他的人生仿佛被浓雾遮蔽,只剩一页档案,静静地躺在某个柜子里。 张际鹏的经历并不独特,许多在内战后期失势的将领,流亡香港时都经历过从高处跌落的痛苦,他们曾在抗战中奋勇杀敌,曾在权力中风光无限,却在转瞬之间成为被牺牲的边缘人,有的选择转向海外,有的隐姓埋名,有的甚至客死异乡,连墓碑都无人问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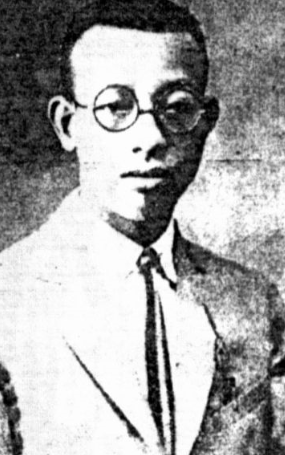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