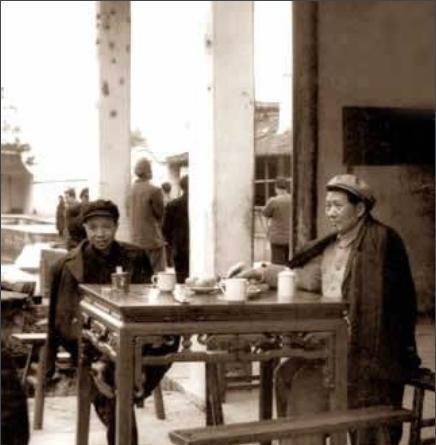71年主席得知谭启龙境遇,嘱咐周恩来:他的情况我清楚,安排工作 71年9月的一个午后,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传出一句轻声询问:“放牛娃子,你还好吗?”短暂的寂静后,回答同样简洁:“感谢主席关心,挺得住!”靠窗的毛泽东放下茶杯,笑着点点头,转向周恩来,“谭启龙的情况我清楚,安排个合适的岗位。”周恩来微微颔首,身旁秘书已在本子上记下指示。 那场工作会议本是讨论当前形势,主席却专门抽出几分钟谈起这位久未露面的老部下。许多人不解——一名因“问题”被闲置多年的地方干部,为何能让最高层如此惦记?答案要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湘赣边地说起。 1928年,永新的稻田旁,14岁的谭启龙放下牛鞭,跟着苏维埃宣传队走进贫农夜校,他第一次听到“翻身”二字。放牛娃听得入神,第二天便执意报名当“红小鬼”。没人愿意接收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可他死守门口,直到队长点头。由此,少年谭启龙正式迈入革命队伍。 井冈山的雨夜,他扛着半人高的木箱穿过丛林;瑞金的操场上,他领着少年先锋队高唱《国际歌》;湘鄂赣的山谷间,他与十几名战友躲过围剿,三年游击弹尽粮绝仍不投降……这种“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干到底”的劲头,让上级一次次选派他去最困难的地方。 1933年到中央苏区马列学院深造时,他才第一次坐下读完一本整书。毛泽东见到这个黑瘦小伙,先问家底,又叮嘱:“识字,多想,再挑重担。”一句话点醒谭启龙:革命并非只靠冲劲,还要靠学问。此后,每到战斗间隙他都揣着毛边书,看到生字就刻在枪托上,白天背诵,夜里默写。 抗日、解放、渡江,每一次大考结束,他都从前线走到行政岗位。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时期,他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装进镜框挂在床头;到山东后,他又把厉家寨的石头梯田当成课堂,硬是把旱塬改出成方连片水稻田。老农拍着他的粗布衣说:“谭书记,这人能跟土地较真,我们服。” 然而1966年开始的政治风浪打乱了一切。谭启龙被点名“有问题”,隔离审查。关押点仅数十平方米,高温闷得人喘不过气,他仍坚持写调查笔记,一页一页夹在破棉被里。看守嫌麻烦不搜,被子随他辗转几处,直到后来才在缝隙里找到密密麻麻的“山东农业水利图”。有人讥笑他傻,他摇头:“数据在,饭种得出来。” 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主席突然询问“谭启龙来了没有”,让筹备人员措手不及。两年后,毛泽东的这份惦念在1971年的工作会议上变成明确指示。几天后,中央组织部文件下达:谭启龙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曾经的“问题干部”重新站在红色地图上。 赴闽第一天,谭启龙没进机关大楼,而是直奔山区看木麻黄林。他掰着手指算账:“海岸线长,风沙急,先固沙,再谈产量。”此举惹得省里几位部门负责人面面相觑,但三年后,福建沿海多了一道苍翠防风带,木麻黄与甘蔗间作模式也被农业部推广。 1979年,他已年近花甲,却又受命调往四川。川北冬雨连绵,他顶着湿冷跑遍21个县,掏出在山东积攒的那本“水利图”,对技术员说:“山高,不是借口;水薄,也能调配。”当地干部打趣:“谭书记拿着一本旧账本闯新市场。”事实证明“旧账”管用——川北石梯田里的双季稻当年就突破亩产纪录。 1986年春,当邓小平在成都单独约见这位“老班长”时,谭启龙已递交了退居二线的报告。邓小平开门见山:“你想去哪里安度晚年?”谭启龙想了想,还是点名山东,“那里干过活,湿气小,人也熟。”邓小平笑道:“成,全力安排。”随即提笔写下六字横幅——“人间重晚晴”。旁人都清楚,小平同志极少为在世干部题字,可他为谭启龙破例。 晚年回到济南,他的行李依旧是一只灰旧帆布包,里面放着那幅题字和一本已经翻旧的“小红本”。有人请他回顾功过,他摆手:“没啥传奇,就是一直干活。”2003年秋,他在医院抢救室平静离去,省里照例开追悼会,他生前常穿的蓝布中山装被摆在灵前,胸前口袋还插着自制调查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到最后一行:“地脉不息,人可期。” 放牛娃、红小鬼、省委书记,这几个并不对等的身份后面,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实干与谨慎。回想71年那句“安排工作”,其实并非简单的人事关照,而是最高领导对一个顽强革命者价值的确认:经历风浪仍不改本色,这样的人,国家总要给他一个位置,让他继续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