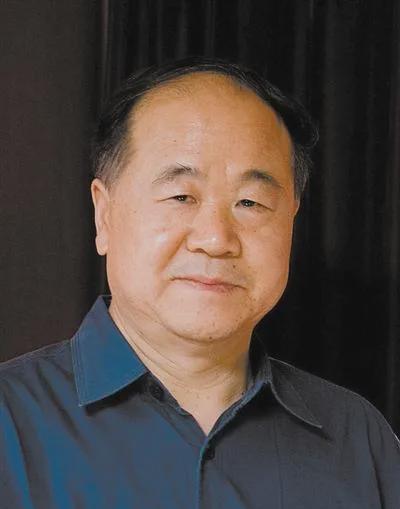学者王鼎钧:“莫言的小说揭露黑暗,谁跳起来大声反对,谁就心里有鬼!”他的这一观点,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文学评论的江湖中引发诸多回响。 莫言的创作风格向来大胆且独特,他以高密东北乡为文学版图,构建起一个个光怪陆离却又真实可感的世界。 在《檀香刑》里,对“檀香刑”这一酷刑细致入微的描写,宛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封建社会刑罚的残酷与人性的扭曲精准剖析。施刑者赵甲那冷酷且专业的模样,以及受刑者孙丙的悲惨遭遇,无不令人触目惊心。这一情节并非单纯为了渲染血腥,而是通过对这种极端残酷场景的呈现,撕开封建“文明”的虚伪面纱,让人们直面那个时代的残暴与生命的卑微。 面对莫言对黑暗毫不留情的揭露,但反对之声也确实存在。部分人认为,莫言的小说过度聚焦于社会的阴暗面,会给读者尤其是外国读者留下对中国片面且负面的印象,仿佛中国历史与社会只有无尽的苦难与丑陋。但这种观点忽略了文学的本质功能。文学并非是对现实的粉饰,而应如镜子一般,真实映照出生活的全貌,既包括阳光明媚的一面,也涵盖那些被阴影笼罩的角落。莫言通过对黑暗的书写,旨在引发人们对历史、社会和人性的深度反思。 王鼎钧先生的话语背后,蕴含着对文学创作和社会批判的深刻理解。当有人对莫言小说揭露黑暗的内容大声反对时,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内容触碰到了他们内心深处不愿面对的事实。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问题可能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而莫言的作品却将这些问题重新摆在公众面前。比如在某些历史时期,社会变革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不公,通过莫言的小说被重新审视。那些反对者或许是既得利益者,亦或是习惯了粉饰太平的人,他们害怕真实的黑暗被曝光,因为这可能威胁到他们的认知体系或利益格局。 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看,莫言的创作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的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开辟了新的路径,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大胆的主题挖掘,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学的多元性与深刻性。他对人性复杂的刻画,对历史伤痛的铭记,都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空间。而那些敢于正视莫言作品中黑暗揭露的人,能够从中汲取力量,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莫言的小说正是通过对黑暗的揭示,让人们更加珍视光明与美好,促使社会去反思、去改进。所以,王鼎钧先生的观点实则是对莫言文学创作勇气的肯定,也提醒着我们,在面对文学作品时,要有正视现实的勇气,而非盲目逃避。 在莫言的创作版图中,《酒国》与《生死疲劳》《十三步》犹如三颗璀璨却各具特色的明珠,它们在叙述分层上的差异,展现出莫言在叙事艺术上的多元探索 。 《生死疲劳》以独特的 “六道轮回” 视角展开,叙述者是经历轮回的西门闹,他先后化身为驴、牛、猪、狗、猴,最后转世为大头婴儿蓝千岁 。通过这一独特的叙述视角,小说讲述了从 1950 年到 2000 年中国农村的沧桑巨变 。与《酒国》相比,《生死疲劳》的叙述分层相对简洁明了。它围绕着西门闹的轮回经历这一主线展开,虽然在叙述过程中也融入了一些其他人物的故事和视角,但整体结构较为清晰,读者能够较为容易地跟随西门闹的经历,感受时代的变迁对个体命运的影响 。 而《十三步》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叙述层交错极度频繁且毫无规律 。小说中,现实与虚幻、梦境与真实交织在一起,人物的身份和故事在不同的叙述层面中不断转换 。例如,主人公方富贵在讲台上突然 “死去”,之后却又以不同的身份和形象出现,这种频繁的转换让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迷雾的迷宫之中,难以把握故事的脉络和走向 。相比之下,《酒国》的叙述层交错虽然也较为复杂,但仍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它通过书信和小说创作的交替,在不同的叙述层面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逐渐理清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感受到小说结构的精巧。 《酒国》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书信、小说创作等多种元素,构建起了一个虚实相生的叙事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读者既能感受到现实世界中人们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又能通过李一斗的小说,领略到一个充满荒诞色彩的酒国世界 。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既不同于《生死疲劳》的线性叙事,也不同于《十三步》的无序交错,它以一种独特的节奏和韵律,引导读者在现实与虚幻之间穿梭,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思考和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