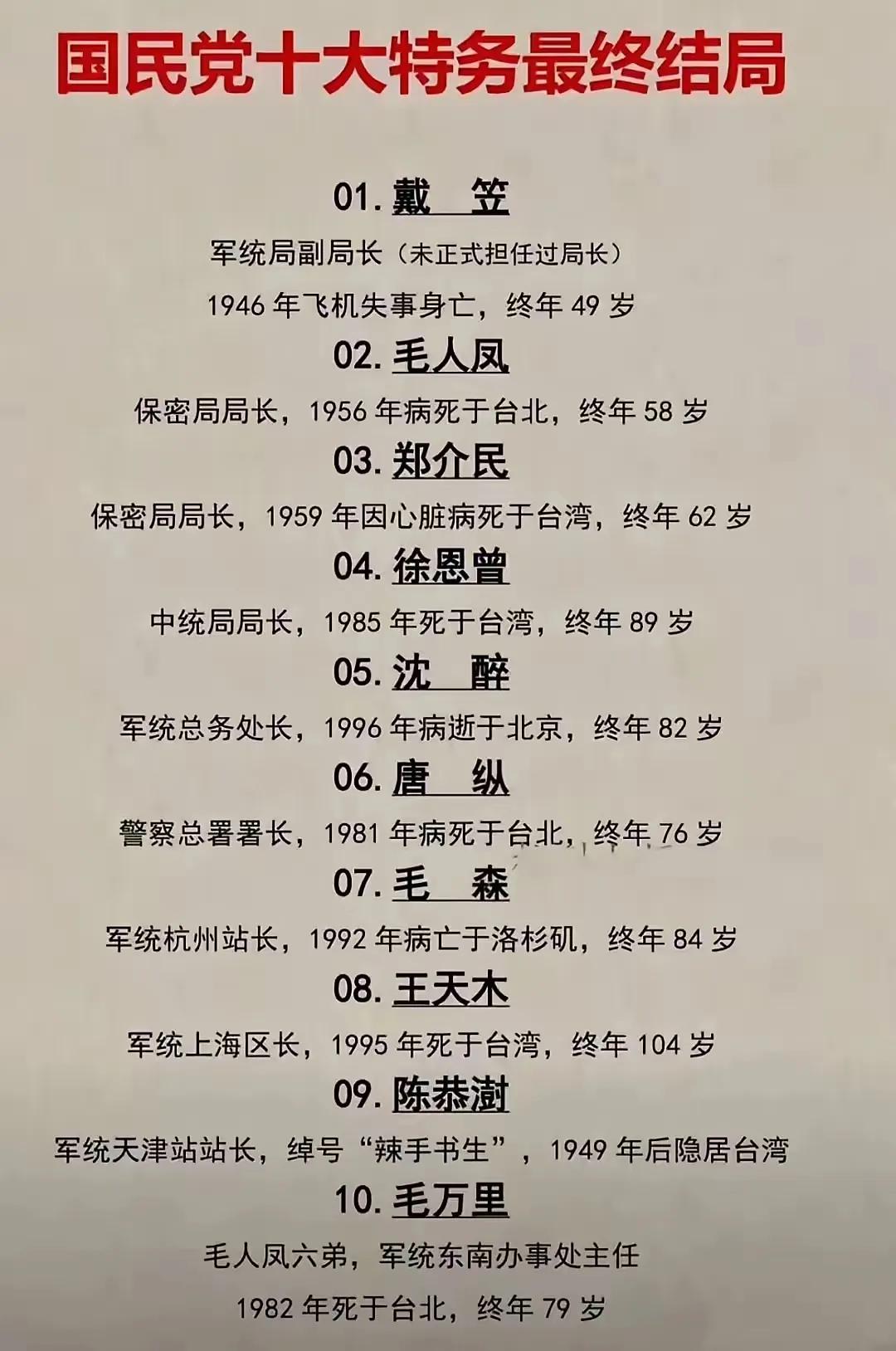钱大钧铁青着脸闯进军统湖北站,当着站长朱若愚和一干特务的面,掏出手枪当场把情报处长杨若琛一枪打死,转身扬长而去……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华清池枪声大作。当时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钱大钧,听到动静第一个反应就是抄起枪往外冲。结果,一颗流弹直接从他后肋射入,穿透了肩膀。他当场就倒在了血泊里,可以说,是实打实地替老蒋挡了一枪。 这道枪伤,成了他日后最大的政治资本。后来老蒋被抓,戴笠在审讯钱大钧时怀疑他跟张学良串通,调走了专列,断了委员长的退路。钱大钧什么也没多说,直接脱掉上衣,指着身上狰狞的伤疤反问:“我要是通敌,何必拿命去挡子弹?” 就这一句话,蒋介石心软了。 所以你看,钱大钧有底气。这底气是拿命换来的。在他看来,我替校长流过血,我为党国挡过枪,你一个军统小小的处长算什么东西? 被他打死的杨若琛,也不是个简单角色。他是军统湖北站的情报处长,戴笠的眼线。那段时间,正是武汉空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钱大钧兼任着航空委员会的主任。杨若琛接连给戴笠打小报告,说钱大钧“贻误战机”,甚至暗指他有“通共嫌疑”。 这些报告,每一条都可能要了钱大钧的命。 在那个年代,“通共”的帽子一旦扣上,谁也摘不下来。钱大钧这种在权力场里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江湖,当然明白其中的凶险。他选择了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肉体消灭。这一枪,打给杨若琛,更是打给杨若琛背后的戴笠和整个军统看的。意思很明白:别把手伸得太长,我黄埔系嫡系将领的事,轮不到你们这些特务来指手画脚! 这事捅到蒋介石那里,所有人都等着看钱大钧怎么倒霉。毕竟,当众枪杀军统命官,这是在公然挑战领袖的权威。 可老蒋的处理,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仅仅是“停职一月”,然后复职。 连刑事责任都没追究。 这就有意思了。蒋介石在想什么?其实他是在玩一种平衡术。 一方面,军统这把刀越来越快,戴笠的权力越来越大,已经开始让很多嫡系将领感到不安和反感。军队和特务系统之间的矛盾,早就摆上了台面。蒋介石需要敲打一下戴笠,告诉他别太出格,尤其不能动他的核心圈子。钱大钧这一枪,正好给了他一个由头。 另一方面,钱大钧毕竟是“护驾功臣”。如果为了一个特务处长就严惩自己的救命恩人,那以后谁还愿意真心实意地为他卖命?这笔人情账,蒋介石算得很清楚。 所以,杨若琛就这么白死了。他的死,成了蒋介石平衡派系、安抚人心的棋子。 然而,钱大钧以为自己可以永远躺在这份“护驾之功”上,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躲得过杀人的罪,却躲不过一个“贪”字。 枪杀案后不久,他坐镇的航空委员会就爆出了惊天贪腐大案。1939年重庆大轰炸,日军飞机如入无人之境。蒋介石急电钱大钧,命令空军起飞拦截。钱大钧的回复差点把老蒋气死:“无飞机可用。” “几年下来数千万美元的购机款,飞机呢?”蒋介石的质问,钱大钧无言以对。 一查到底,账目烂得一塌糊涂,几十架战机的采购款不知去向。这回,连宋美龄都保不住他了。蒋介石一纸手谕:“撤职查办,永不叙用!” 你看,这就是那个时代最吊诡的地方:忠诚和贪腐,杀人和人情,被拧成了一股乱麻。 钱大钧可以因为“忠诚”的伤疤,而免掉杀人的死罪;却也会因为贪婪,而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始终没明白,蒋介石的信任是有额度的,可以透支,但终究会花完。 其实,钱大钧并非不懂人情世故。有个故事很能说明他的精明。1933年,陈赓被捕后经多方营救出狱,在从上海去江西的火车上,竟然碰上了钱大钧。当时陈赓心里一沉,以为在劫难逃。 钱大钧却把他请到自己的包厢,好吃好喝招待,聊了聊黄埔的旧事,临了还说了句:“你有事就走吧,我不拦你。” 手下副官不解,问为何不抓。钱大钧看着窗外,淡淡地说:“你忘了,他救过校长的命。” 这指的是1925年东征时,蒋介石兵败遇险,是陈赓硬是把他从死人堆里背了出来。 钱大钧心里有本账,他知道,陈赓是蒋介石心里一个特殊的“情义债”,自己要是抓了,反而是给校长添堵。 一个能如此洞察上意、精于算计的人,最后却栽在了最简单的“贪”字上。说到底,是那个环境扭曲了他。当权力可以无视法律,当人情可以大过国法,当杀人都可以被轻轻放过时,贪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钱大钧的一生,就像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缩影。有过忠诚,有过战功,但最终却被内部的派系斗争、制度腐败和无尽的私欲所吞噬。那一枪,打死的是杨若琛,震慑的是戴笠,但真正打穿的,却是国民党政权自己早已腐朽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