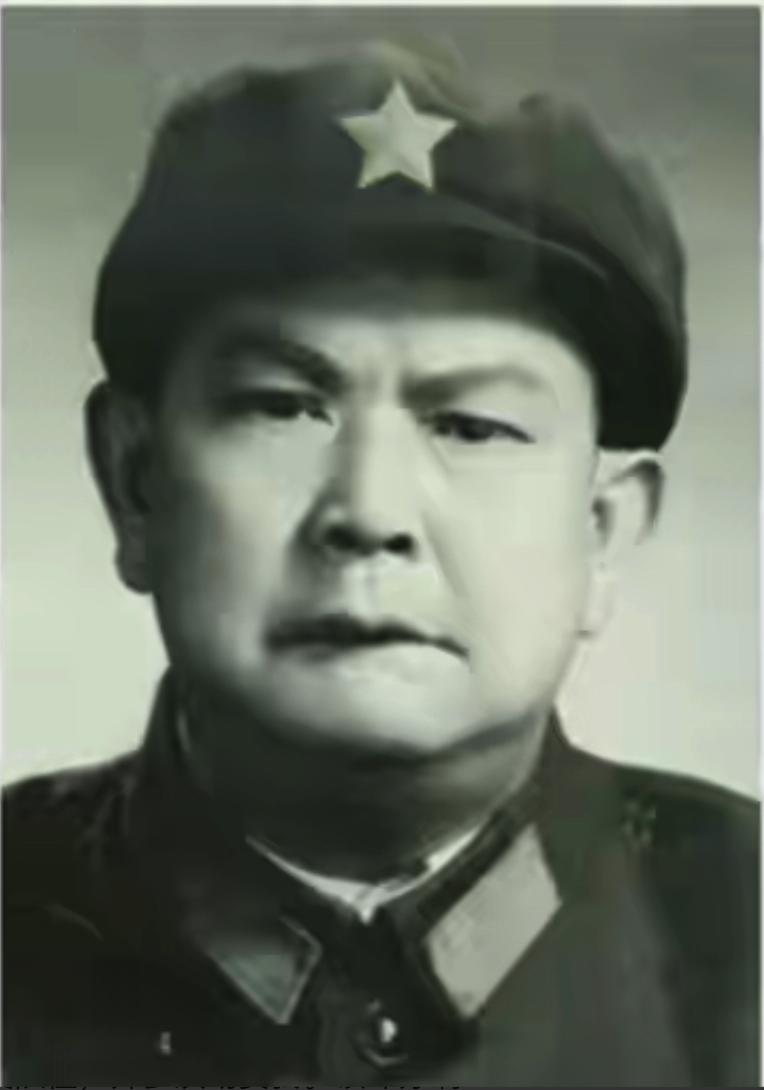1941年,新四军作战科科长找到刘奎。他说:“上级让你留下打游击。” 刘奎一愣:“就我一个人?” 科长答:“还有两个重伤员。” 1941 年 4 月,泾县河畔。新四军主力北移船队已集结。作战科科长李子高找到军部参谋刘奎时,31 岁的他刚把刺刀插进枪套。这把刺刀是他从皖南事变炮火中捡的,也是唯一武器。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 9000 余人遭国民党军围攻,仅 2000 余人突围,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等牺牲。 “部队要过江,上级让你留下打游击。” 李子高声音压低,眼神无奈。刘奎猛地抬头,攥紧枪托:“就我一个人?” 李子高别过脸:“还有两个重伤员,你得照顾好他们。” 没人比刘奎更懂命令的重量。三个月前,他刚掩埋项英、周子昆两位首长遗体。皖南事变时,他在山洞发现被害的首长和昏迷的重伤员黄诚,含泪做记号后,背着黄诚躲了三天三夜才逃出。 看着李子高的眼神,刘奎明白:皖南抗日火种不能灭。“我接。” 他转身走向安置伤员的破庙。 破庙里,黄诚伤口渗血,李建春腿伤需人扶。三人凑在干草堆前,刘奎把仅有的半块干粮掰成三份。 “就我们三个,连自保都难。” 李建春语气焦虑。 刘奎摸出牺牲战友的党员证:“得让老百姓知道,新四军没走。” 第二天天刚亮,刘奎背黄诚、扶李建春挨村走。当时皖南遭日伪军 “扫荡”,百姓日子苦。他们棉袄磨出棉絮,脚底血泡连片,靠百姓给的草药敷伤,继续讲抗日道理和新四军纪律。 五天后,他们到泾旌交界的朱家坑。村口冲来五个汉子,领头的周永华扛着锄头:“刘参谋,我们信你!跟着你干!” 三人队伍变八人,武器只有刘奎的汉阳造,其他人用锄头、柴刀。 刘奎开第一次队会,指着伪乡公所地图:“得有枪,才能保护老百姓。庙首乡公所得了新枪,守敌少,我们智取。” 队员郎建新化装成卖柴的,在庙首乡转三天摸清敌情。行动前一天,刘奎带两人埋伏,缴了伪军三支枪和军装。“换上,装像点。” 刘奎压低伪军帽檐。 深夜,刘奎带队员走到乡公所门口,岗哨刚要盘问就被控制。伪乡长正抽大烟,见 “伪军” 闯来刚发火,就被刘奎用枪抵住太阳穴。 “把枪交出来!” 刘奎声音冷。见伪乡长犹豫,他用刀刺其大腿。 “别杀我!” 伪乡长喊人交武器。 这一战缴了二十多支枪,粮食分给百姓,临走贴标语:“新四军黄山游击队在此!” “刘奎端了庙首乡公所” 的消息传遍皖南。半个月里,十八个农民、四个失散新四军战士来投奔,队伍扩到三十多人。 1941 年 7 月,泾旌太中心县委命名队伍为黄山游击队,任命刘奎为队长。当时中共中央重视皖南支点,多次指示建党组织和游击队。 队员们在朱家坑宣誓:“打死不叛党,抗战到底!” 刘奎看着大家,清楚:革命火种在老百姓的信任里,不在武器。 之后两年,刘奎带游击队在黄山灵活作战。日军 “扫荡” 修碉堡,游击队化整为零,伏击运输队、破交通线,处置汉奸恶霸。 百姓把游击队当亲人,白天放哨报信,夜里送粮送衣,妇女帮缝补衣服。 但危险常伴。敌人悬赏 2000 块大洋抓刘奎,每月 “围剿” 七八次,几里路修十几个碉堡。 1943 年冬,通信员王昆山叛变,夜里开枪打死郎进新,打伤刘奎大腿和臀部。 刘奎疼醒,硬挤出子弹,急喊:“快给胡书记报信!王昆山知道机关位置!” 警卫员舍不得走,刘奎拔枪指门口:“这是命令!保卫组织要紧!” 警卫员冲进夜色。 敌人追来,刘奎让黄裕芝先撤,自己掩护,放倒四个敌人后暴露。“抓活的!” 叛徒喊,敌人围上来。 刘奎喊:“想抓我?没门!” 跳下悬崖。敌人开枪放火,以为他死了。 可刘奎摔在柴草丛里没丧命。醒来后吞雪解渴,爬进炭宕灭火星,又躲进猴子洞。饿了吃野果,渴了喝泉水,用棉花蘸泉水洗伤口敷药膏。 二十天后,他一瘸一拐到蒋裕民家。蒋家人哭:“都说你牺牲了,我们天天给你烧纸钱!” “打不死的刘奎” 传遍皖南。1943 年底,队伍发展到 800 多人;解放战争时壮大到 2000 多人,改编为皖南沿江总队。 这期间,刘奎又负六次伤,曾被子弹打穿脖子仍活下来。 有人问:“刘队长,你不怕死吗?” 他摸伤疤笑:“我 4 岁没爹娘,党给了我家。为老百姓过好日子,死几次都值。” 这支从三个重伤员起步的队伍,成了牵制敌人的重要力量,为皖南解放立功。刘奎践行承诺:“有我刘奎在,就有皖南游击队在。” 那些吃苦流血的经历,成了皖南大地上的丰碑。它告诉后人:真正的英雄,不是天生强者,是绝境里仍坚守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