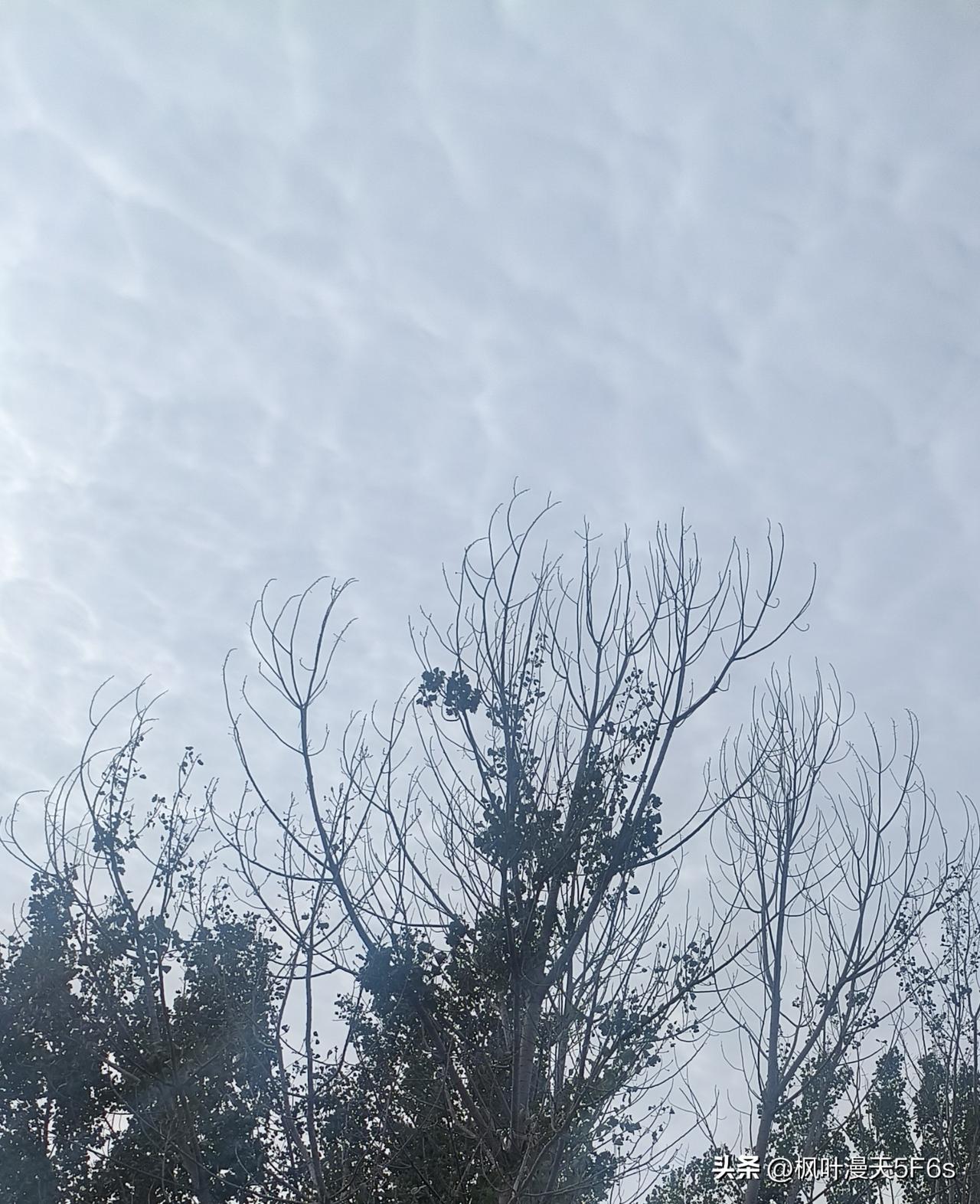最长情的归家:一只燕子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飞的是路,回的是根 老家流传着“燕子不过长江”的说法。可前年冬天,有只老燕子偏偏往南飞去了。 邻居老李头蹲在门槛上抽烟,望着空了的燕窝说:“这是要去南非呢。” 从东北到南非,足足两万五千里——这个数字让人想起另一段两万五千里的征程。 那是个飘着雪花的早晨,别的燕子早已南飞,唯独这只老燕子迟迟不肯离去。它在屋檐下盘旋了三圈,才振翅向南。 渤海湾是必经的第一站。那里的海风能把人吹得站不稳脚,燕子必须顶着狂风奋力向前,就像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每一步都在与命运抗争。 飞越渤海,便是温暖的江南。这里食物充足,气候宜人,本是休憩的好地方。可燕子只是稍作停留,如同当年红军在遵义休整,心中始终记挂着远方的征程。 最艰险的是穿越南海。茫茫大海上无处落脚,燕子只能借着高空气流滑翔,节省每一分力气。这让人想起红军翻越雪山时,老战士教新兵调整呼吸保存体力的情景。 这一路上,要躲避猛禽的袭击,要寻觅充饥的食物,要辨别前进的方向——这些困境,与当年红军躲避敌机、筹措粮食、依靠北斗星指路的经历如出一辙。 三个月后,从南非鸟类协会传来消息:那只戴着本地标识环的燕子顺利抵达了。 有人问,为何非要飞这么远?生物学上的解释是基因使然。但更让人信服的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种信念,知道家在哪里,就一定要回去。 第二年春天,老燕子真的回来了,还带回了伴侣。看着它们在屋檐下忙碌筑巢,老李头眯着眼说:“能走完长征的,最后都能安家立业。” 原来,燕子飞越的不只是千山万水,更是一条认准了目标就绝不回头的路。就像当年走完长征的人,就像如今为生活奋斗的每个人。 秋深了,燕子又南飞了。但谁都知道,来年春天它一定会回来。因为这里才是它的根,在这年复一年的往返中,完成的是生命的延续,坚守的是永恒的归途。 分享今日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