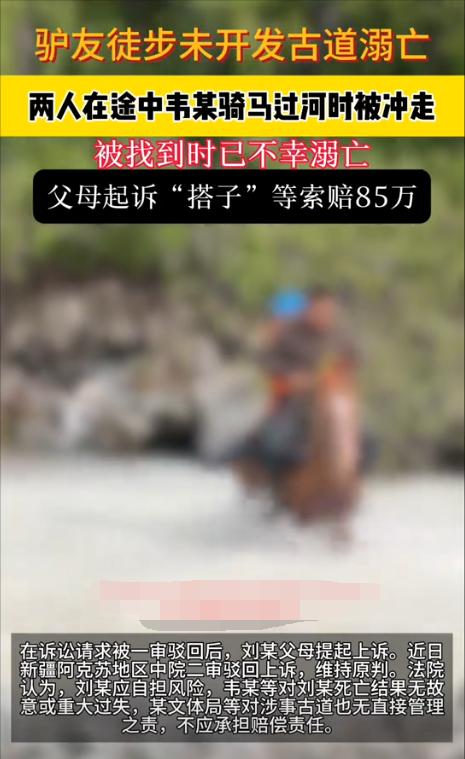新疆阿克苏,一名资深徒步者在未开发的自然风景区探险途中不幸溺亡,家属将同行驴友、古道驿站和当地文体部门告上法庭,索赔85万余元。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全部请求。 2024年8月20日,刘某乘拼车抵达新疆伊犁的一个村镇。他热爱旅行,是那种习惯“去别人没去过的地方”的人。当天,他向一位养蜂人陈某买了汽油,并顺口打听了古道的路线。次日,刘某独自上路,途经一片无名湖泊,偶遇同样独行的朱某。两人结伴同行,分享食物、路线和探险心得,暂时组成了一支临时的“驴友联盟”。 三天后,两人抵达一处古道,又遇到了独自旅行的韦某。短暂交谈后,三人决定分道前行。8月30日傍晚,刘某在古道边再次遇见韦某,两人觉得有缘,决定继续结伴。天色渐暗,他们决定趁夜过河。河水湍急、深不可测,为安全起见,刘某花费800元租了牧民的马,并请牧民带路。 晚上九点半左右,他们遇到了朱某。朱某劝他们:“这水太急,还是等天亮再走吧。”牧民也试探性下河,发现水势凶猛,建议暂缓行动。但刘某看了看周围遍布石块的河滩,说:“这地方露不了营,干脆过河算了。”牧民和韦某未再反对,三人便骑马入河。 就在河水淹至马腹的位置时,突然一股浪涌袭来,三匹马和三人瞬间被冲散。韦某侥幸被冲到岸边,拼尽全力爬了上去,却发现手机无信号。夜色漆黑、体力透支,他在树林中休息至天亮。翌日早晨七点半,韦某沿山口行进,遇到两名工作人员后立即报警。中午十一点半,警方在下游两公里外找到了刘某遗体。 刘某家属得知噩耗后痛不欲生,认为韦某未及时施救、陈某未尽导向责任、驿站和文体部门未设置安全警示,要求几方共同赔偿85万元。他们认为:“既然是一起同行的驴友,就该相互照应,不能见死不救。”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法庭对事件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了详细审查。法院认为,这一案件的核心在于:他人是否对刘某的死亡负有法定救助或安全保障义务。 首先,《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家属若想获赔,必须证明韦某、陈某等人存在过错行为,且该行为与刘某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然而,证据显示,韦某与刘某仅为临时同行关系,刘某坚持连夜过河,韦某并未主导或强迫,仅是附和同行。事发后韦某已尽最大努力自救,并于次日及时报警,其行为符合《民法典》第183条关于“合理自救义务”的规定,不存在消极怠慢。 其次,《民法典第1167条》明确,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他人承担侵权责任,除非他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徒步穿越未开发区域本身属高风险行为,刘某作为资深探险者,应充分了解并承担风险后果。韦某既无故意,也无重大过失,依法不应承担赔偿。 再看卖汽油的陈某。法院调查后确认,陈某仅售出汽油并口头说明了路线,并非专业向导,也未收取带路费用。他既未组织活动,也无法预知河水风险,因此不具备侵权主体资格。 至于古道驿站,法院指出,其功能仅限于提供登记、食宿和安全提醒,并不属于《民法典》第1198条所指的经营性公共场所。刘某的溺亡地点距离驿站数公里,驿站对未在其场所范围内发生的事故不负安全保障义务。 文体部门方面,古道属于尚未开发的自然区域,不是对公众开放的景区或经营性旅游项目。根据《侵权责任法》及《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政府部门仅对其主管范围内的公共设施承担监管职责,不承担个体自发探险的安全责任。因此,文体部门亦无需担责。 法院最终认定,刘某之死系其个人判断失误造成的意外事件。刘某明知河水湍急仍坚持夜渡,风险系其自担。《民法典第1176条》中明确,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减轻或免除他人责任。综合考量,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决:驳回刘某家属全部诉求。 从法律层面看,这一判决严谨且具代表性。案件揭示出一个普遍问题:在自由探险与安全责任之间,法律无法为所有冒险行为兜底。当成年人自愿参与高风险活动,其风险承担义务随之产生。法律可以追责“过错”,但无法否定“自由选择的后果”。 然而,案件也给社会管理和公众安全教育敲响了警钟。虽然文体部门无直接责任,但在野外活动日益流行的今天,地方政府和户外组织仍有义务加强风险提示、完善救援体系,防止类似悲剧反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