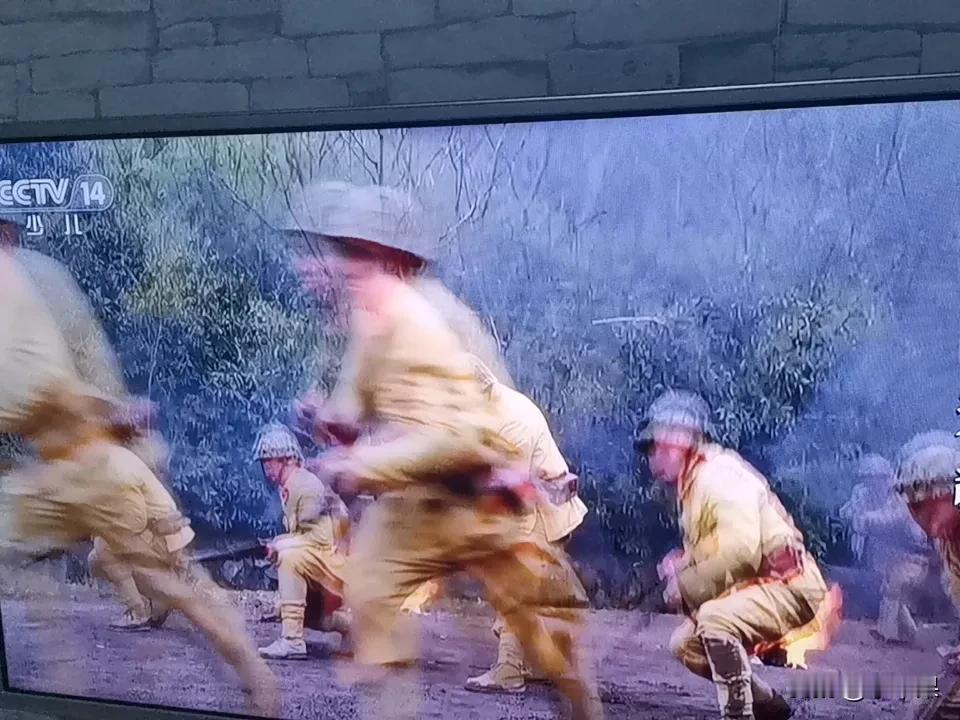铁篱笆下的火种 1942年深秋,冀中平原的芦苇荡结着白霜,剃头匠老魏蜷在破庙里磨剃刀,刀刃映出远处日军据点的探照灯。三天前,他藏在夹层的八路军伤员刚被转移,临走前塞来的半截钢笔还揣在怀里,笔帽上刻着“守土”二字。 “魏师傅,剃个头。”破庙门被推开,穿短打的青年带进股寒气,帽檐下的伤疤在火光中若隐若现。老魏认出是镇上维持会的“办事员”陈默,手不自觉攥紧了剃刀——这小子上周还帮日军清点过民房。 剃刀划过鬓角时,陈默突然按住他的手腕,低声道:“据点西头的竹篱笆,今晚亥时第三根是活桩。”老魏心头一震,想起伤员说过日军要建清乡区的消息。陈默见他迟疑,从怀里摸出块染血的粗布,上面绣着半朵腊梅:“我姐是一线红的交通员,上月牺牲在竹篱笆下。” 入夜后,老魏借着送热水的由头混进据点外围。月光下,连绵的竹篱笆像道冰冷的墙,每根桩子都插着“通匪者死”的木牌。亥时的梆子声刚响,他果然看见第三根桩子被轻轻晃动,露出仅容一人通过的缝隙。 “谁在那儿?”巡逻兵的吆喝声骤然响起。老魏情急下打翻热水桶,趁乱钻进缝隙,却撞见陈默正和两个蒙面人交接情报。“这是武连长的亲笔信,”陈默把纸条塞给他,“明天日军要搜缴周庄的粮仓,得让乡亲们提前转移。” 回程路上,老魏被日军的狼狗盯上。他攥紧怀里的钢笔,想起伤员说的“普通人也能挡枪子”,突然拐进岔路引开追兵。跑过结冰的河沟时,钢笔从怀里滑落,他伸手去捞,却看见冰面下冻着半朵腊梅——那是陈默姐姐的绣品。 第二天清晨,周庄的粮仓早已空无一人。老魏站在村口,看着远处日军气急败坏的身影,悄悄把捡回的钢笔插进泥土。后来有人说,那片土地上长出的芦苇,每年春天都带着淡淡的墨香,就像无数埋在地下的火种,在无人知晓的地方默默燃烧 。